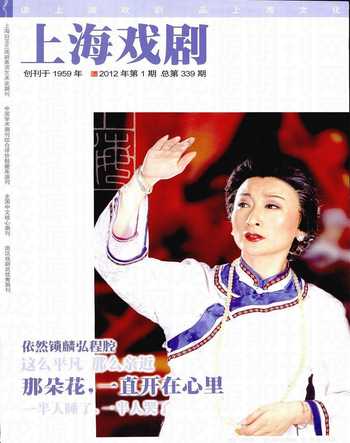筆走冷峻探千古情
聞韶
李莉自己說,人生道路有時候很奇怪,小學一年級音樂課上,她曾經受到感染在家里的門板上用粉筆寫下一句話“我將來要做個音樂家”。媽媽看到后說:“你知不知道爸爸媽媽都是工農兵,當什么家,要接好工農兵的班!”小李莉就此放棄了當“家”的年頭。多年之后,在她幾乎已經忘記這個夢想時,發現自己還是成了“家”——劇作家。
很多人都以為,李莉后來會成為編劇,一定是從小的愛好,或者從在部隊開始就搞文藝,其實不然。雖然李莉的媽媽確實是越劇迷,但這份癡迷并沒理所當然遺傳下來,早年問李莉與越劇的緣分一直少得可憐。幼年她也隨母親進過劇場,看的是經典越劇《梁祝》,當時太小,只記得“禱墓”時墳“砰”地裂開,一對蝴蝶飛出來,這個場景是她對越劇的唯一印象。15歲時李莉參軍,十年軍旅當的是通訊兵,與文藝毫不搭界,與越劇更是基本絕緣。她說,“部隊里有一位領導的夫人曾是原寧德越劇團的演員,文革武斗中她被嚇得精神失常,劇團也解散了。她丈夫就把她接到身邊。每天她會在小溪邊咿咿呀呀地唱,一開始很多人圍觀,后來也就逐漸沒人注意她了。我路過有時會好奇,想聽懂她唱的是什么,但是聽不懂,只覺得旋律凄婉纏綿”。直到文革結束后看了電影《紅樓夢》,李莉才把記憶中的旋律與電影對上號——原來她唱的是《葬花》。“部隊的生活比較剛硬,這個調子是一種浸潤,好像在對我訴說什么。這個時候對越劇的印象才明晰起來。”
李莉做編劇始于一句戲言。以連級干部的身份轉業復員回家后,李莉開始了每天八小時坐班的普通人的生活。家里有一臺9寸的黑白電視,只能收兩個臺。媽媽每天念叨著“怎么不放越劇啦”,聽得多了,李莉隨口說了句玩笑話“你這么喜歡看越劇,我寫個越劇給你看好了。”媽媽的回答是:“假使你會寫越劇,我困曚頭里也笑出來了。”李莉非常自信:“好,我就花十年功夫寫一個越劇給你看!”從此開始留心,騎著車到處找戲看,“什么好戲歹戲都看,那時候真的是自己買票的。”李莉上班的地方正好在上海戲劇學院對面。一天,她發現對面打出橫幅,上海戲劇學院招收影視劇創作函授班,學期一年,學費三十元。李莉興致勃勃地報了名,捧回一大摞教材回去啃。一年后,第一個大戲劇本《情水恨天》出爐,她獲得優秀學員獎,獎金恰好也是三十元。
和很多業余編劇愛好者一樣,李莉也曾徘徊于劇團之外。上海有位著名編劇一開始就勸告她:“上海各劇團能寫戲的編劇多如牛毛,大部分都是沉到海底,你何必進這個圈子呢。”對干這句含義豐富的話,李莉至今沒能完全理解,“可能是覺得我基礎差吧,也可能覺得戲曲編劇這個行當太難了。他說的是實情,當時每個劇團都有好幾個自己的專業編劇,愛好者更多”。《情水恨天》是為越劇寫的,最終卻并沒排成越劇,而是被改編為淮劇《烏紗夢》,由上海淮劇團梁偉平等主演。兜了一大圈,李莉被介紹給上海越劇院創作室主任薛允璜一也是她后來的老師。第一次見面,薛允璜肯定了《烏紗夢》的基礎不錯,但表示,這個戲是老生青衣戲不適合越劇,言下之意就是不接受。李莉二話沒說,回去花了一年時間,拿出了第二個劇本《魚玄機之死》。這次寫得比較艱苦,每天要趕很多路上班,完全靠業余時間,也沒有人指導。其間李莉都沒有與薛允璜聯系。再次出現時,薛允璜有點驚訝于她的執著,“可能他想,很多業余青年編劇寫了本子被拒絕就沒有音訊了,怎么又送來了?因為我承諾了母親,說要花十年時間寫越劇。如果十年出不了頭,那我就放棄了。才努力了一年就放棄,太說話不算數了。”看了這個作品后,薛允璜出手指點“這個題材對越劇不合適。如果你真想寫戲,我們給你一個題目,限時四十天。”李莉當時的想法是:“是不是懷疑本子不是本人寫的,所以要指定題目。”三十多天后,業余青年編劇交卷,根據一則新聞改編的古裝戲《送子觀音圖》——這個越劇處女作順利通過,李莉也終于拿到了進上海越劇院的通行證。進院后她的第一個作品《深宮怨》(后改名《血染深宮》)就在《劇本》月刊上發表,并獲得全國優秀劇目獎。薛允璜的眼光之準可見一斑。
越劇是個柔情似水的劇種,然而了解李莉作品的人會有這樣的印象,李莉作品中的愛情戲相當少。“記得《血染深宮》去南京參加中國戲劇節演出的時候,趙志剛對我說,大家都說你不太會寫愛情戲,我說到時候我寫一個給你看。后來就有了《夢里云間》(《千古情怨》),兩個團搶著要。可能我寫的愛情戲不是那種溫婉、祥和、喜悅的愛情。如果說大家向往的是月光下的愛情,那么我寫的是暴露在陽光下,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
李莉的作品中柔情的成分偏少,后期更是大都筆鋒犀利,散發著洞徹一切的冷峻、超然和理性,有限的情感脈絡在人物身處的時代、社會環境、權力欲望間交纏,顯得格外苦澀悲涼。這對一個身在越劇院的女編劇來說,多少有點讓人驚訝。究其根源,讓人好奇她經歷過怎樣的思索與掙扎。“每個人的際遇不一樣,接受到的東西也不一樣。同樣經歷一件事,留下痕跡深刻的,思索更多,感悟也更多。”李莉父母給她的教育比較單一、質樸,軍旅生涯更使她嚴肅律己,不肯妥協,正值年少氣盛,什么看不慣就要說,“可以說我比較‘左吧。領導常說,李莉是個毛栗子,拿在手里扎手,扔了又可惜。就像在水泥地板上長起來的,一塵不染,不懂人情世故。”軍人把服從與堅守奉為準則。她所堅守的東西,在現實中有時又是如此地矛盾。還是在文革期間,李莉手下的一個新兵頗有背景,是高干的千金,剛入伍半年多,新兵的媽媽想女兒了,要她回家探親。司令部營部開黨委會決議都通過,到李莉這個小小排長這兒竟堅決不執行,怒發沖冠:“部隊規定必須服役三年才能有探親假,干部子弟可以半年就走了,讓平民子弟怎么想?這兵還怎么帶?誰要是敢放她走,我就敢拿沖鋒槍把誰掃了。”最終沖鋒槍沒用上,新戰士也沒去探親,這個事件以想念女兒的媽媽來部隊招待所探女告終。為崗位堅守底線,直到現在都是她的原則。“堅決不讓這樣的事在我管轄的范圍內發生。從這件事可以看出來,我這人逼急了脾氣很倔的。當然這樣的性格也碰到了非常多的釘子。”多年后李莉再次得到這個戰士的消息,得知她已經過世。李莉在網上找到她的靈堂,給她獻了一束花。“現在回過頭來想這件事,有的時候她是被環境、被時事推到了風口浪尖上,推到了人人見她都要拍馬屁的地位。她的心靈深處可能并不是這樣的。這造成了后來我在寫很多歷史劇的時候,不大寫個人性格造成的悲劇。《成敗蕭何》也好、《秋色漸濃》也好、《鳳氏彝蘭》也好,都是環境造就了他們,環境把人推到了一個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