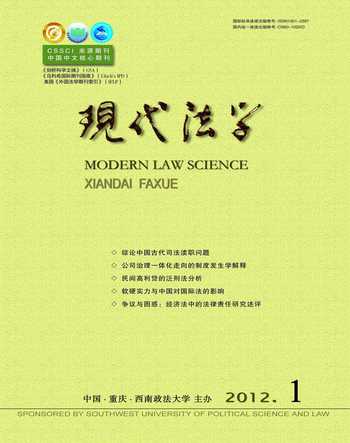勞動法中的人
摘 要:《勞動法》采用了“勞動者”的概念,但并沒有對“勞動者”的具體涵義作出解釋。學界通常依照從屬關系理論,將“勞動者”解釋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工資勞動者。但是,如果聯系立法時的語境來分析“勞動者”的權利體系,我們可以發現,《勞動法》中“勞動者”的真正原型是國有企業職工。“勞動者”原型的選擇決定了我國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機制,并且制約著勞動立法的實施效果。直到《勞動合同法》頒布,“勞動者”才開始具有農民工的某些特征。我國應當從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的要求出發,以從屬關系理論為指導,科學合理地確定“勞動者”的認定標準,并相應地對目前的勞動關系調整機制進行┩晟啤
關鍵詞:勞動者原型;勞動立法;從屬關系理論;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國企職工
中圖分類號:DF47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1.10
一、問題的提出
“勞動者”的概念是勞動法學中最具有爭議的問題之一,“不僅具有理論和政策意義,而且在勞動爭議處理中還具有重要的司法實踐意義。”[1]在法律意義上,“勞動者” 身份的取得具有私法和公法兩方面的意義。在私法意義上,“勞動者”身份的取得意味著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建立了勞動關系,其標志是雙方訂立書面或者口頭形式的勞動合同,明確約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注:我國勞動立法要求用人單位與勞動者必須簽訂書面合同,不允許采用口頭形式訂立勞動合同,這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作法不同。]在公法意義上,“勞動者”身份的取得是啟動勞動法律保護機制的鑰匙,這里的“勞動法律保護機制”包括安全衛生制度、最低工資制度、工時和休假制度、工會與集體協商制度、勞動爭議處理制度等方面。如果沒有“勞動者”的身份,就很難獲得勞動法律制度的保護和救濟。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下文簡稱《勞動法》)于1995年1月1日開始施行以來,“勞動者”開始成為一個重要的法律概念,但是受當時的社會環境和認識水平限制,該法并沒有給“勞動者”下任何定義。我國《憲法》中也多次使用“勞動者”的概念,但《憲法》并沒有區分受雇勞動者和自雇勞動者,也沒有區分公務員和產業勞動者,因此憲法意義上的“勞動者”只是一個泛義的政治概念。
在理論上,如何界定“勞動者”的內涵與外延始終是勞動法學研究中的前沿課題。我國通說認為,勞動法中的“勞動者”是指達到法定年齡、具有勞動能力,以從事某種社會勞動獲取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公民[2]。這個定義非常寬泛,基本上把所有在各類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中工作的工資勞動者都劃入到“勞動者”的范疇之中,顯然并未考慮農民工群體的特殊性。在實踐中,農民工在就業政策、社會保險、工資保護、爭議處理等方面并沒有完全享受到《勞動法》的保護,以至于有學者指出,農民工實際上只享有“準勞動者”的待遇[3]。
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首要問題就是:《勞動法》中的“勞動者”在中國語境中的真實含義是什么?它是否包括一切工資勞動者?更進一步而言,20世紀80年代以來涌入城市的農民工是否屬于《勞動法》所指的“勞動者”?
為了解答上述問題,本文采用語境解釋的方法,把《勞動法》中關于“勞動者”的各項規定作為一個整體,嘗試復原該法所描述的“勞動者”形象。通過對復原后的“勞動者”形象與現實生活中的勞動者群體進行對照分析,提出了《勞動法》中的“勞動者”原型是國有企業職工的判斷。與 “勞動者”原型相配套,《勞動法》依照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勞動關系的特點確定了我國的勞動關系調整機制,但是這種調整機制體制色彩極重,以至于《勞動法》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對國企職工“有法不依”、對農民工“有法難依”等法律適用問題。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已經對“勞動者”原型進行了明顯的修復,該法中“勞動者”的形象開始具有了農民工的某些特征。但是,由于立法機關尚未意識到“勞動者”原型的選擇問題,該法并沒有對勞動關系調整機制進行徹底改革,這可能會長期影響《勞動合同法》以及其他社會立法的實施效果。
二、 法學理論中的“勞動者”:從屬的人
我國立法中的“勞動者”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自從《勞動法》于1995年1月1日開始施行以來,“勞動者”開始成為一個重要的法律概念,但是受立法當時的社會環境和認識水平限制,該法并沒有給“勞動者”下任何定義。我國《憲法》共有7次使用“勞動者”的概念[注:我國《憲法》中共7次使用了“勞動者”一詞,分別出現在序言(統一戰線中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第8條(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勞動者)、第14條(勞動者的積極性和技術水平)、第19條(對勞動者普及教育)、第42條(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第43條(勞動者休息權利,2次)。],其含義是泛指“農民、工人、國家工作人員以及其他勞動者”。[注:我國《憲法》第19條第3款采用了這種理解,具體規定是:“國家發展各種教育設施,掃除文盲,對工人、農民、國家工作人員和其他勞動者進行政治、文化、科學、技術、業務的教育,鼓勵自學成才。”]可見,《憲法》并沒有區分受雇勞動者和自雇勞動者,也沒有區分公務員和產業勞動者,憲法意義上的“勞動者”顯然是一個泛義的概念。
對“勞動者”的科學界定更多地需要依靠法學理論的支撐。我國勞動法學的奠基人史尚寬先生提出,“勞動者”是指“基于契約上之義務在從屬的關系所為之職業上有償的勞動”的人[4]。按照這個定義,“勞動者”應當具備勞動契約、從屬關系、職業活動和有償勞動四個要素。在四個要素中,“從屬關系”揭示出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關系不是平等關系,是界定勞動者主體身份的核心要素[5]。從屬關系理論是勞動法與民法的分水嶺,也是區分勞動關系和民事關系的主要理論工具。傳統民法將勞動者視為與雇主具有平等地位的人,然而正如日本學者星野英一教授指出的,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以契約當事人的平等、自由為前提的各種契約理論因雙方當事人社會、經濟方面的不平等而顯現出了破綻,這種不平等最清楚地表現在雇傭契約里[6]。因此,作為對近代民法關于平等主體假設的一種糾正,從屬關系理論直言不諱地指出勞動關系雙方當事人是典型的不平等主體。
從屬關系理論將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從屬性主要分為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和人格從屬性三個方面。[注:國外有些學者還有階級從屬性、技術從屬性等提法,所以,從屬關系理論更多地是從不同側面揭示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的不平等地位。]所謂“經濟從屬性”是指勞動者需要依賴工資收入為生,因而在經濟上對用人單位具有從屬性。然而經濟從屬性的含義比較抽象,很難具體量化,因此,法院通常不把經濟從屬性作為認定“勞動者”地位的主要依據。[注:
法國和德國勞動法中通常對經濟從屬性理論持懷疑態度。(參見:鄭愛青. 法國勞動合同法概要[M]. 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24-26;杜茨.勞動法[M].張國文,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8.)]所謂“組織從屬性”是指勞動者通常會被勞動使用者編入到其內部組織架構之中,作為該組織的一名成員參與生產經營。雖然組織從屬性在三個從屬性標準中最容易識別,在實踐中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然而,組織從屬性又是最容易被改變的。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普遍存在著雇主通過勞務派遣等形式將勞動關系轉變為民事關系的現象。為此,法院一般也不完全根據組織從屬性的有無來認定勞動者的身份,而是要從多個方面進行綜合裁量。所謂“人格從屬性”是指勞動者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從事勞動,而是將自己置于用人單位的指揮、管理和監督之下,從而導致人格上對用人單位的從屬性。日本通說認為,勞動力與一般商品的不同之處在于,勞動力與勞動者人格不可分離,勞動者出賣勞動力時,雇主同時會支配其人格,即“人格上的從屬性系勞動者自行決定之自由權的一種壓抑”[7]。無論是在大陸法國家還是英美國家,人格從屬性都是司法機關認定勞動者身份的主要標準。[注:人格從屬性在英美國家被稱為“控制標準”(control test)。(參見:李坤剛. 論勞動關系中雇主之界定——以英國勞動法為視角[J]. 云南大學學報:法學版,2007, (3): 192-196.)]我國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曾于2005年出臺《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其中一項標準就是“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該標準比較明顯地體現了人格從屬性的要求。
毋庸諱言,“從屬性”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不同勞動者在從屬性方面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現實中的從屬性有強弱、深淺、廣狹之分,界線并非絕對清楚。[注:這主要是日本學者下井隆史教授的觀點,參見:劉志鵬. 勞動法理論與判決研究[M]. 臺北: 元照出版社,2000: 12. ]因此,在很多案件中,僅僅根據從屬性標準來判斷勞動者的身份仍然是相當困難的。不僅如此,由于我國現行勞動法理論受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學說的影響較大,往往只是從經濟、人格和組織三個方面解釋勞動者對用人單位的從屬性,其目的主要在于論證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不是平等關系,從而排除民法的適用。[注:臺灣學者劉志鵬認為,所謂勞動契約有從屬關系,乃系立法者因立法政策之需要而可以予以強調、認知,并借此為勞工保護法之制定架橋鋪路而已!劉氏觀點雖然有點偏頗,卻比較準確地說明了從屬關系理論對勞動立法的基礎作用。(參見:劉志鵬. 勞動法理論與判決研究[M]. 臺北: 元照出版社,2000: 22.)]然而,這樣的從屬關系理論并未窮盡我國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不平等的根源,我國勞動者除了經濟從屬性、組織從屬性和人格從屬性之外,還具有明顯的“體制從屬性”。具體而言,由于長期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我國勞動人事制度具有明顯的“體制性分割”特征,基本劃分為體制內勞動力市場和體制外勞動力市場兩大體系。體制內和體制外的勞動者形成了“一系列事實上的不平等”,具體表現在工資、福利、民主管理等多個方面[8]。體制從屬性造成了體制內勞動者與體制外勞動者享有不平等的權利,有經濟學者非常深刻地指出了這種差異:
“從國有企業與存量合同工的關系來看基本是平等的,職代會、工會在確保涉及企業與職工關系的有關決策的民主性、透明性等方面有極大的影響,職工的保險福利相對有保障,……而國有企業與臨時工、農民工的關系,以及非國有企業與員工的關系,則基本上是一種雇用與被雇用、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民主性、透明性、公正性及保險福利等有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往往得不到體現、更沒有保障。”[8]
因此,勞動法中的從屬關系理論在實踐中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解釋所有勞動者問題,需要根據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及各國的具體國情加以完善。如果不考慮中國勞動力市場體制性分割的特點,只是簡單地運用從屬關系理論來判斷勞動者的地位,就容易造成勞動立法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的問題,最終影響到法律的實施效果。
三、我國勞動立法中的“勞動者”:從國有企業職工走向農民工
任何法律一經制定,就已經成為歷史,法官只能在“現在”的環境中去解釋那些在“過去”的語境中制定的法律。有鑒于此,解釋法律不能只從文本出發,還必須聯系立法當時的經濟與社會背景,否則就無法發現那些隱藏在法律條文背后的真正含義。在英美法國家,“當法官或律師試圖發現立法意旨時,除了訴諸法律文本自身外,他們通常總是訴諸大量的立法資料或其他學者的解釋,例如立法的辯論記錄,立法者個人的日記通信,立法前后的社會環境和重大事件,以及其他學者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所有這些材料都用來證明某種意圖是立法的真正的、原初的意圖。”[9]由于中國正處于快速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期,很多勞動立法最初制定時的社會場景在現在可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倘若僅僅拘泥于字面意思,就很難避免誤讀誤判的問題。因此,在中國社會變遷這個大背景下,緊扣立法當時的語境來解釋勞動立法就顯得特別重要。
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和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都使用了“勞動者”的概念,但都沒有給“勞動者”下定義,而是采取界定“用人單位”的方法來明確“勞動者”的范圍。如《勞動法》第2條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企業、個體經濟組織(以下統稱用人單位)和與之形成勞動關系的勞動者,適用本法。國家機關、事業組織、社會團體和與之建立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依照本法執行。”依照該規定的字面含義, “勞動者”就是所有與企業或者個體經濟組織形成了勞動關系的勞動者,以及所有與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建立了勞動合同關系的勞動者。
然而,通過界定用人單位來界定“勞動者”是一種間接的方法,這種間接定義方法決定了我國勞動立法中的“勞動者”概念既不科學也不精確,在實踐中會造成很多問題。例如,很多企業使用了大量的勞務派遣工人,被派遣工人在法律上并不是這些企業的“勞動者”。[注:
我國《勞動合同法》第58條規定:“勞務派遣單位是本法所稱用人單位,應當履行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義務。”]再如,有的企業使用了很多技校學生“頂崗實習”,這些實習學生在法律上也不是該企業的“勞動者”。另外,很多地方都曾經發生過公司總經理申請勞動爭議仲裁,并要求公司支付高額加班費、獎金或者經濟補償等待遇的案件。事實上,總經理之類的高級管理人員在勞動法中通常被視為“雇主代理人”,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不具有從屬性特征,自然也就不應該適用《勞動法》。可見,具體認定哪些人是“勞動者”,僅僅靠劃定“用人單位”的范圍仍是不夠的,還必須具體分析這些人員與企業之間的法律關系,尤其是要查明其與企業之間是否存在從屬關系,才能最終決定這些人是否具有“勞動者”的法律地位。
回顧歷史,我國制定《勞動法》主要是為了適應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需要,確認并且推廣國有企業全員勞動合同制改革的成果,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體制立法的特點。如果把《勞動法》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就可以發現,只要一個人具有“勞動者”的身份,他就有權享有就業促進、勞動合同、社會保險、民主管理等勞動權利。然而,在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這種全能型的“勞動者”只可能是體制內的勞動者。
第一, 依照《勞動法》,“勞動者”享有就業的權利,各級政府應當為勞動者提供公共就業服務。但是在實踐中,就業政策長期以來并不支持農民進城務工,只有城鎮職工才享有在城市就業的權利,農村勞動力就業“總的精神是離土不離鄉,就地消化,向城市流動要做到有序化”。[注:這里引用的是原勞動部部長李伯勇轉述李鵬總理、朱镕基副總理就農村勞動力就業問題的指示精神。(參見:李伯勇. 認真學習貫徹勞動法,推動勞動事業全面發展[J]. 中國勞動, 1994, (10): 6.)]在2003年國務院發出《關于做好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管理和服務工作的通知》(國辦發[2003]1號)之前,各地政府主要是為本地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提供就業服務,農民工不僅享受不到工作地政府提供的就業服務,甚至還經常被當作“盲流”而被驅逐。直到2007年制定的《就業促進法》出臺,農民工在失業保險、稅收優惠、就業指導等方面仍未能取得與城鎮失業人員同等的權利[10]。鑒于就業權是“勞動者”能夠享受《勞動法》保護的前提條件,在就業權缺失或者不完整的情況下,農民工不可能完全享有 “勞動者”的地位和待遇。在就業權利方面,“勞動者”只具有城鎮職工的特征。
第二,依照《勞動法》,“勞動者”有權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并且有權參加集體協商,與用人單位訂立集體合同。從立法的發展路線來看,《勞動法》關于勞動合同的規定主要來自于1986年國務院頒布的《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11]。在《勞動法》立法討論過程中,多數人主張“在《勞動法》中確認和發展勞動制度改革成果,把勞動合同作為確定勞動關系的一種基本形式而普遍地推行。”[12]勞動合同制改革的重點是城鎮公有制企業,其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職工。直到《勞動法》實施10年之后,簽訂勞動合同的農民工人數只占農民工總數的28.7%[13]。大多數農民工連書面勞動合同都沒有,更不可能有機會與企業簽訂集體合同。
第三,依照《勞動法》,“勞動者”應當享有休息休假權和勞動報酬權。事實上,這些權利并未能真正惠及農民工。根據《勞動法》的規定,勞動者每天工作不超過8小時,每周不超過44小時,后來國務院進一步將每周工時縮短為40小時。然而據國家統計局2004年所作的調查顯示,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時,平均每個月加班超過80小時,遠遠超出了《勞動法》每個月加班不得超過36小時的最高限制。另外,拖欠農民工工資是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據有關方面估計,2004年上報的拖欠農民工工資總額為336億元(至2004年底償付比例為98.4%)[13]。可見,在休息休假權和勞動報酬權方面,農民工顯然不是《勞動法》所描繪的“勞動者”。
第四,根據《勞動法》,“勞動者”享有參加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等五項社會保險的權利。在制度設計方面,《勞動法》把社會保險關系與勞動關系掛鉤,即只要是“勞動者”就有權參加各項社會保險。但是在法律實施過程中,全國大多數省市都沒有把農民工作為社會保險制度中的“勞動者”,甚至還為農民工建立了一套有別于城鎮職工的保險制度。如北京市在2001年為農民工建立了一套專門的養老保險體系,其特點是繳費基數低,待遇采取一次性發放的方式。[注: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2001年8月發布的《北京市農民工養老保險暫行辦法》。]上海市則為農民工建立了“綜合險”制度,包括老年補貼、工傷保險和醫療保險,采取了商業化運營的管理模式。[注:上海市人民政府2002年4月頒布的《上海市外來從業人員綜合保險暫行辦法》。]全國人大常委會2005年的工作報告也指出,在社會保險方面,大多數進城務工人員難以按現行制度參保[14]。可見,從參加社會保險的角度來看,很多地方事實上把“勞動者”理解為“城鎮職工”,農民工被排除在“勞動者”的范疇之外,這種理解非常準確地反映了《勞動法》在1994年起草時的真實語境。
第五,“勞動者”享有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勞動法》第10章規定了“調解-仲裁-訴訟”的爭議處理程序,其中,企業勞動爭議調解委員會由企業工會負責組織,工會代表擔任主任。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由地方工會與勞動行政部門、企業代表共同組成,不經過仲裁,勞動者不能向法院起訴。這樣就建立起一套所謂的“一調一裁兩審”勞動爭議處理程序。然而,這樣的處理程序過于繁瑣,發生勞動爭議的農民工出于生計所迫,很難堅持到二審程序。更重要的是,在2003年之前,各地工會根本就不接受農民工入會。[注:直到2003年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報告,農民工加入工會問題才被首次寫入其中。(參見:李雪平. 國際人權法上的遷徙自由和遷徙工人的權利保護——以中國農民工為例[J]. 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 2004, (3): 35. )]因此,農民工在申請爭議處理時長期存在著沒有工會代表其利益的問題。再加上申請仲裁的時效只有短短60天,仲裁機構要求農民工預交案件受理費和辦案費,造成了農民工難以利用《勞動法》所提供的救濟渠道的尷尬局面。
綜上可知,雖然《勞動法》采用了抽象的“勞動者”概念,但是立法者在制定《勞動法》的過程中所關注的“勞動者”主要是當時正處在改革攻堅階段的國有企業職工。該法制定時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就是減員增效,而當時的國有企業職工對勞動合同制持懷疑態度,擔心簽了合同之后會失去體制上的保障。為了消除國企職工對勞動合同制的擔心和顧慮,《勞動法》為實行勞動合同制后的“勞動者”提供了一個堪稱完美的權利體系,囊括了就業權利、社會保險權利、勞動合同權利、參加工會與集體協商的權利、工資保障權利、休息休假權利、民主管理權利以及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幾乎全盤復制了當時國有企業勞動關系的調整機制。這些權利體系及其所依附的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對農民工而言是一個封閉的體制,他們很難成為這個體制中的“勞動者”。由此可見,《勞動法》中的“勞動者”并不是一個泛義的概念,其立法原型主要是原體制內的國有企業職工。
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原型進行了重要修復,使“勞動者”開始具有農民工的某些特征。首先,該法強化了書面勞動合同制度,強調用人單位必須與勞動者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否則就要向勞動者支付二倍的工資。[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10條、第82條。]由于現實中大多數沒有簽訂合同的勞動者是農民工,因此,書面形式要求更多是出于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需要。其次,該法加強了對勞務派遣、非全日制勞動等非典型勞動關系的法律規范。[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5章第2節和第3節。]由于很多用人單位采用勞務派遣等非典型用工形式使用農民工,因此,加強法律規制的目的顯然在于保護農民工。第三,在社會保險權利方面,該法不僅規定社會保險是勞動合同的必備條款,同時還特別要求“國家要建立健全勞動者社會保險關系跨地區轉移接續制度”。[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17條、第49條。]雖然城鎮職工也可能存在著社會保險關系轉移接續等問題,但是流動性更強的農民工顯然是這些新規定的最大受惠者。第四,該法還回應普遍存在的農民工工資被拖欠問題,規定用人單位應當及時足額地向勞動者支付勞動報酬,否則勞動者可以向法院申請支付令,或者單方解除合同,并要求用人單位支付經濟補償。[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第30條、第38條第1款第2項。]由此可見,《勞動合同法》中的“勞動者”形象正在逐步向農民工轉變,這一轉變是我國勞動立法對經濟與社會轉型的積極回應,表明“農民工已經成為我國產業大軍的一支重要力量”。[注:《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2006年1月18日發布。]
然而,由于對“勞動者”原型的選擇缺乏主動性和自覺性,《勞動合同法》幾乎全盤繼承了《勞動法》確立的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將各項社會權利與“勞動者”身份捆綁在一起,比如“勞動者”有民主參與制定企業內部規章制度的權利,有參加社會保險的權利,有參加集體談判的權利,有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權利等。由于這樣的勞動關系調整機制源于國有企業,對農民工而言,至今仍然缺乏各方面的配套措施,因此,農民工很難享受到法律所賦予的各項權利。《勞動合同法》在頒布后之所以受到企業界的強烈抵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勞動者”原型選擇與勞動關系調整機制不匹配造成的。“勞動者”原型的錯誤定位使勞動者的法定權利無法轉化成勞動者的福利,導致勞動立法從出臺之日就已經注定得不到完全地貫徹實施。
四、“勞動者”原型的選擇對勞動立法實施效果的影響
《勞動法》自1995年1月1日開始施行以來,其實施效果一直差強人意。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赴各地對《勞動法》的實施情況進行檢查,發現《勞動法》在貫徹實施方面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問題。例如,勞動合同簽訂率低,超時加班現象比較普遍,欠繳社會保險費現象嚴重,等等,這些問題在有些地方還相當嚴重[14]。
對于《勞動法》未能有效地貫徹實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勞動法》本身存在著許多缺漏和先天不足,在許多方面只作了原則性、綱領性規定,難以實際操作。因此,主要的解決辦法是盡快修訂完善《勞動法》[15]。第二種觀點認為,《勞動法》及其配套法規所確立的勞動標準過高,因此造成了實施過程中執法不嚴的現象,為此,勞動立法應當適當降低勞動標準,實行“低標準、廣覆蓋、嚴執法”[16]。第三種觀點認為,《勞動法》實施不力是因為法律責任太輕,企業違法成本太低,法律缺乏威懾力,因此解決辦法在于加重處罰力度。[注:郭軍認為:“(《勞動法》的)法律責任制度總體上講不成功, 處罰的力度和手段都嚴重不足, 這也是導致《勞動法》執法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亟待加強。……《勞動法》實施中的問題不是《勞動法》本身的制度缺陷導致的, 而是配套立法滯后的問題, 是執法不到位的問題。”(參見:郭軍. 勞動法執行大于修改[J]. 中國勞動, 2005, (2): 18. )]第四種觀點則認為,《勞動法》實施不力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拼命招商引資,并把放松勞動執法作為優化投資軟環境的一個方面。因此,這種觀點認為,要解決《勞動法》執法不力的問題,關鍵在于地方政府改變過去的政績觀,樹立科學的發展觀[17]。
上面幾種觀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事實上,《勞動法》之所以未能很好地貫徹實施,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立法過于原則,缺乏可操作性;也不在于勞動標準過高造成的執法不嚴;更不在于法律責任太輕,企業違法成本太低;甚至不能歸咎于地方政府的執法不力。客觀地說,我國《勞動法》以及其他勞動立法之所以沒有得到很好地實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該法把國有企業職工作為“勞動者”的原型,并由此確立了勞動關系調整的法律機制。但是這樣的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并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造成了嚴重的有法不依和有法難依的問題。具體可以從國有企業職工和農民工兩個方面進行說明:
首先,《勞動法》頒布后大規模開展的國有企業改制并沒有嚴格遵守《勞動法》,存在著嚴重的“有法不依”問題。國家制定《勞動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普遍推行勞動合同制,打破國有企業中長期實行的固定工制度。《勞動法》頒布后,國有企業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與新錄用勞動者訂立固定期限的勞動合同,可以根據法律規定的條件和程序解雇職工。[注: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陳清泰1995年在“《勞動法》實施縱深行”座談會上發言指出:“(國有企業)這些改革試點工作都面臨著一個重要課題需要回答,就是如何通過分離企業社會職能,分流企業富余人員,減輕企業負擔。……貫徹《勞動法》是搞好‘分離、分流、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根本性措施。” (參見:陳清泰. 《勞動法》是企業制度改革的重要法律依據[J]. 中國勞動科學, 1995, (9): 9. )]然而,這仍未能滿足國有企業盡快裁減冗員的需要,1995年之后,國務院又逐步允許國有企業有條件地讓職工下崗,實行“減員增效”。僅僅在1998-2001年期間,國有企業就累計有2 550萬名職工下崗。[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白皮書》,2002年4月29日發布。]隨后,又有大量國企職工在改制過程中被企業以“買斷工齡”或者提前退休的方式解雇。《勞動法》本來已經為國有企業分流富余人員設計了“經濟性裁員”等法律程序,然而,無論是國企職工下崗還是買斷工齡,都沒有嚴格適用《勞動法》規定的程序和補償標準。[注:
依照國務院1998年6月9日出臺的《關于切實做好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業工作的通知》,下崗職工“3年期滿仍未再就業的,應與企業解除勞動關系,按規定享受失業救濟或社會救濟”,實際上并未依照《勞動法》處理國企職工下崗問題。]《勞動法》不僅無法向下崗職工提供法律救濟,甚至還要容忍國有企業超越勞動合同解除制度之外,以“減員增效”和“買斷工齡”等名義與大量職工解除合同,《勞動法》因此喪失了應有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其次,《勞動法》對農民工則如同“水中月,鏡中花”,存在著嚴重的“有法難依”的致命問題。如前所述,《勞動法》以國有企業職工作為“勞動者”原型設計了一整套勞動關系調整機制,不僅包括勞動合同制度,還包括工會制度、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就業促進制度、職業培訓制度、社會保險制度、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制度、勞動監察制度、爭議處理制度,等等。這種調整機制的根本特征是所有權利和待遇都與勞動關系掛鉤,只要是“勞動者”,就可以享有所有的權利。然而,這種勞動關系調整機制實際上是建立在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的基礎之上,城市中的各項公共服務都以本地戶籍為前提,由于“農民工”不具有本地戶籍,因此也就難以進入到這種體制化的勞動關系調整機制之中。直到2003年之后,勞務輸入地的公共就業服務、工會服務等各項制度才逐步對農民工開放,至今農民工在社會保險等方面仍然難以真正享受到“勞動者”的待遇。所以,農民工雖然在形式上屬于《勞動法》中的“勞動者”,但由于缺乏關鍵的配套制度,他們在很長時期內都未能享受到“勞動者”的各項權利。
因此,我國勞動立法的實施障礙并不能簡單地歸因于地方政府的態度,因為并非各地政府都在勞動標準方面向下競爭;也不能簡單地歸因于勞動立法規定得過于原則和抽象,因為即使很具體的規定往往也執行不下去;甚至不能歸因于我國的工會體制,因為我國的勞動法是建立在國家統制主義的基礎之上,維護勞動者權益的責任主要在政府,而不在工會。勞動立法之所以實施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立法本身對“勞動者”原型的選擇不當,并且由此造成了勞動關系調整機制的錯誤定位。一些勞動法學者和實務工作者也曾經指出過這個問題[注:
例如,董保華教授曾指出,《勞動法》制定于20 世紀90 年代,當時的勞動者主要是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少量民營企業的勞動者。那時的企業是較為正規的企業,員工也是較為正式的員工。10多年來,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隨著農民進城務工、國有企業員工下崗,勞動者出現了分層,當時《勞動法》所保護的對象已經成為這種分層中較高層次的勞動者。如果不對這種狀況加以調整,《勞動法》就會出現某些貴族化傾向。(參見:董保華. 錦上添花抑或雪中送炭——析《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草案) 》的基本定位[J].法商研究, 2006, (3): 49. )],
但并沒人系統地加以論述。如果未來的勞動立法仍不能糾正“勞動者”原型存在的問題,再多的立法恐怕也只會重蹈《勞動法》的舊轍。
五、結論
長期以來,勞動法實務部門和理論界之間關于勞動者的定義問題存在著很大的分歧。一方面,實務部門往往以《勞動法》第2條作為依據,即只要雙方存在著一方提供勞動,另外一方支付報酬的關系,并且用工主體符合第2條所規定的“用人單位”的范圍,就會直接將雙方之間的法律關系認定為勞動關系。然而,這樣對“勞動者”的理解過于教條和機械,完全沒有考慮勞動者應當具有從屬性,因而常常把總經理、人事經理等“雇主代理人”也認定為勞動者,甚至要求企業“依法”向此類人員支付巨額加班費、獎金或者經濟補償。另一方面,理論界則往往強調勞動者應當具有從屬性特征,甚至套用政策語言將勞動者說成是“弱勢群體”,但是大多數學者實際上并未發現我國勞動立法中的“勞動者”并非理論意義上的從屬勞動者,而更多地是指體制內的勞動者,因此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究其根本,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國勞動立法對“勞動者”原型選擇不當造成的。
由于“勞動者”原型的選擇不當,我國勞動關系的調整機制天生就帶有體制色彩過強、覆蓋面過窄、權利體系大而全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曾嚴重地妨礙《勞動法》的貫徹實施,而且將來還可能會降低《勞動合同法》等新法的實施效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立法中的“勞動者”應當是處于從屬地位的抽象的人,而不應該是具體的某一類社會群體。直言之,無論是國有企業職工還是農民工,都不適合作為立法中“勞動者”的原型,否則就很容易混淆政策和法律的界限。目前,國有企業大規模的減員增效改革已經基本結束,農民工問題也得到了各級政府的高度關注,對“勞動者”原型的重新定位正面臨著一個絕佳的歷史契機。我國立法機關應當抓住這個難得的機遇,以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者的從屬性特征為出發點,科學合理地重塑“勞動者”的法律形象,并相應地完善現有的勞動關系調整機制。ML
お
參考文獻:
[1]常凱.勞動權論——當代中國勞動關系的法律調整研究[M].北京: 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2004: 121.
[2]郭捷,劉俊,楊森.勞動法學[M].修訂版.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57.
[3]岳經綸.農民工的社會保護:勞動政策的視角[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6):14-16.
[4]史尚寬.勞動法原論[M].上海:世界書局,1934:7.
[5]呂琳.論“勞動者”主體界定之標準[J].法商研究,2005,(3): 33.
[6]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M].王闖, 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66.
[7]黃越欽.勞動法新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94.
[8]李萍, 劉燦.論中國勞動力市場的體制性分割[J].經濟學家, 1999, (6): 18-22.
[9]蘇力.解釋的難題:對幾種法律文本解釋方法的追問[J].中國社會科學, 1997, (4): 23.
[10]丁大晴.農民平等就業權在《就業促進法》中的缺陷與完善[J].北方法學, 2010, (3): 5.
[11]王全興.《勞動法》完善的方式選擇[J].中國勞動, 2005, (2): 19.
[12]胡可明.勞動法起草過程中的若干難點問題[J].中國勞動, 1994, (11): 12.
[13]勞動保障部課題組.勞動保障部課題組關于農民工情況的研究報告之一——當前農民工流動就業數量、結構與特點[N].中國勞動保障報,2005-07-28(7).
[14]何魯麗.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勞動法》實施情況的報告[EB/OL].(2005-12-29)[2010-12-20].http://www.gov.cn/jrzg/2005-12/29/content_140649.htm.
[15]關懷.適應市場經濟要求,應當盡快修訂《勞動法》[G]//葉靜漪, 周長征.社會正義的十年探索:中國與國外勞動法制改革比較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8-12.
[16]董保華.中國勞動基準法的目標選擇[J].法學, 2007, (1): 52-60.
[17]爾民.勞工權益誰來保護[N].中國經濟周刊, 2004, (29): 62.
Person in the Labor Act: Effects of Choice of Prototype of Laborer upon Labor Acts Implementation
ZHOU Chang瞶heng
(Law School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Labor Act, while adopting the concept of laborer, failed to clearly define it. Academics usually with the doctrine of subordinated relationship interpreted it as all wage workers including migrant ones from rural areas. However, if viewing the framework of laborer rights in the context where the Act was made, one may find that the prototype of laborer was no one but the worker in the state瞣wned enterprise. Choice of the prototype of laborer determines the legal mechanism regulating the industrial relation and has direct effects up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 Not until the adoption of the Labor Contract Act did laborer have some features of migrant workers. As such, we should redefine “laborer” to make it in consistence with the theory of subordinated relationship so as to satisfy the demand of market economy. The current legal regim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should also be modified accordingly.
Key Words:prototype of laborer; labor legislation; theory of subordinated relationship; mechanism to regulate industrial relationship; workers in state瞣wned enterpri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