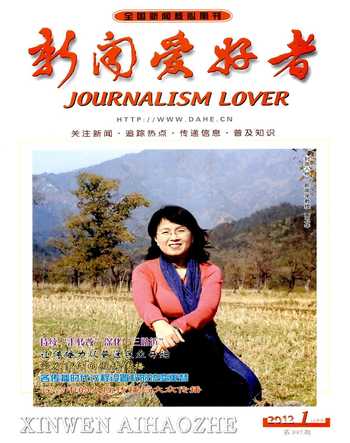大眾傳媒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
龍麗雙
【摘要】隨著社會的發展,大眾傳媒已經越來越廣泛、深刻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少數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少數民族文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沖擊。毋庸置疑,少數民族文化是少數民族群眾心靈的家園,是需要一代代傳承與發揚下去的。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大眾傳媒在沖擊少數民族文化的同時,可以通過一些途徑實現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但也不能過于放大這種傳承與發揚。只有認識到這些,才能夠真正、有效地實現大眾傳媒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
【關鍵詞】大眾傳媒;少數民族文化;傳承與發揚
隨著社會的發展,大眾傳媒對人們的生活觀念、人生體驗等諸多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而這種影響隨著大眾傳媒在少數民族地區的迅速發展日益明顯。大眾傳媒帶來的各種新的觀念和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少數民族的傳統風俗、習慣和思想等,甚至使一些少數民族文化瀕臨消亡。少數民族文化是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積淀的智慧結晶,是少數民族群眾心靈的家園。其文化中的優秀部分是少數民族自身得以發展的精神食糧,是需要得到傳承與發揚的。大眾傳媒對少數民族文化產生巨大沖擊的同時,在傳播過程中通過各種形式的信息將前人所創造的文化傳遞給后代可以實現文化的延續,也為傳承和發揚少數民族文化提供了契機和可能。
大眾傳媒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的現實性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建立在繼承和創新的基礎之上的,只有將前人的經驗、智慧、知識進行記錄、積累、保存并傳給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完善、發展和創造。而大眾傳媒在傳播的過程中,通過各種形式的信息將前人所創造的文化傳遞給后代可以實現文化的延續、傳承與發揚。
張瑞倩在《電視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修補”——以青海“長江源村”藏族生態移民為例》中考察了青海—藏族生態移民村村民的社會生活變遷及電視媒介接觸經驗發現,雖然大眾媒介加速了移民的現代化進程,沖擊了藏族的民族文化,但是她認為廣播電視尤其是電視可以對少數民族文化起到修補的作用。如電視可以通過反映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節目來重現和強化少數民族文化。曾經在唐古拉山鎮存在但又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弱化、改良甚至是消失的許多傳統的藏族節日儀式通過電視節目重現了這些節日在西藏、云南、四川的盛況,從而彌補了青海—藏族生態移民村村民對本民族文化由于種種原因而淡忘甚至消失的民俗知識的空缺。臺灣三立電視臺曾經制作的一部名叫《獨龍族一切安排好啦》的片子也一定程度上發揮了電視節目對獨龍族傳統文化的修復、傳承的作用。“節目中介紹了獨龍族一些傳統的生活方式,如爬樹游戲、江邊釣魚、編織獨龍毯、采取獨龍汁(一種天然的染色品)、放養獨龍牛,等等,他們看得非常認真。因為他們發現節目陳述的一些據說是獨龍族傳統的習俗和游戲的內容他們也沒有聽說過,已經在他們現在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一位村民看完電視后說:‘我們的生活習俗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不看這個節目,我還不知道我們祖先有那些游戲,我真佩服我們祖先有那么了不起的創新和征服自然的能力。”[1]因此,大眾傳媒特別是廣播電視可以通過各種信息、節目加強少數民族的民族辨識以修復民族文化,進而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
大眾傳媒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的途徑
傳播方式上靈活多樣。大眾傳媒可以采用少數民族群眾樂于接受的方式來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我國許多少數民族群眾都能歌善舞,唱歌跳舞是少數民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如世世代代的苗族人通過歌舞解除疲乏,也通過歌舞在游方場上尋找到知心愛人,使苗族族群代代繁衍、生生不息。而木鼓、蘆笙更是已經與苗族、侗族血脈相連。大眾傳媒在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時,可以采用歌舞彈唱、山歌情歌、民族歌劇戲劇、音樂歌舞或風情藝術片等方式來展示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同時,在傳媒技術不斷更新發展的背景下,大眾傳媒應充分利用各種傳媒技術并發揮不同媒介的特點,多層面多角度地展示少數民族文化以達到傳承與發揚的目的。如針對互聯網具有的信息量大、覆蓋范圍廣、交互性強的特點建立各種介紹少數民族文化的專題網站、網上論壇等以擴大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再比如影視手段具有的聲情并茂的傳播特點特別適合于我國許多只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2006年浙江景寧縣廣播電視臺推出了一檔有極強民族針對性且完全使用畬語播音的《畬語新聞》。“該欄目以畬語語言播報,同步配漢語字幕對一周要聞進行回顧,是華東地區電視媒體中唯一用民族語言播報的新聞欄目,也成為浙江省廣播電視發展史上第一次用少數民族語言播出的廣播電視節目。”[2]畬族在唐朝時就在福建、廣東、江西交界地區繁衍生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畬族文化。“畬族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畬族傳統文化的積累和傳承不能像漢族那樣通過文字進行,而主要是通過口頭語言傳播和手頭技藝傳播來進行。本民族的歷史源流、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等精神文化的發展也主要是通過家庭學歌、家族活動、民間習俗和宗教活動過程中以口耳相傳的歌謠、故事、諺語等代代相傳而實現。”[3]這檔畬語新聞節目將畬族人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民族節日與民族習俗、民族語言、民族文學藝術及民族文化特色等方面的新聞進行組織報道,與其他節目類型和其他文化方式一起發揮傳承畬族民族文化的作用。
在傳播的內容和形式上凸顯少數民族文化特色。“內容為王”是傳媒業的鐵律。這對大眾傳媒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也同樣適用。大眾傳媒只有制作富含鮮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作品才能實現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如《劉三姐》、《阿詩瑪》、《五朵金花》等影片以其鮮明的、各具特色的少數民族特色獲得一代又一代人的認可,而這些影片也為傳承與發揚彝族、白族的民族文化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影片《爾瑪的婚禮》中,導演運用紀實手法大量展示了羌族的服飾、語言、舞蹈、羌笛、民歌、飲食和婚俗等民族文化元素,從而保存和展現了有2000多年歷史、被譽為“東方古堡”的桃坪羌寨和神秘的釋比文化等古羌非物質文化遺產。同時,在表現形式上,大眾傳媒也應凸顯少數民族文化特色。
在傳播主體上提高少數民族傳媒人的素養并發揮其能動性。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當然需要政府和全社會各個階層民眾的共同參與,也需要全社會各種力量的加入。但是大眾傳媒在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的時候,傳媒人的能動性與責任感尤為重要。少數民族傳媒人由于對本民族文化的了解與認識以及對本民族文化瀕臨消解的危機意識更為深刻,因此更能夠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實現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但是由于我國少數民族多分布在西部偏遠的地區和省份,從事大眾傳播行業的人素質普遍較低。如前文提及的浙江景寧縣的《畬語新聞》雖然是當地畬族群眾較歡迎的一檔本民族特色的新聞節目,但是該節目仍然存在著新聞節目播出頻率不高、新聞時效性較弱、新聞題材單一陳舊、報道的深度和廣度不夠等問題。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較多,其中比較突出的是缺乏精通畬族語言的采編人員。該節目甚至一直沒有專職畬語播音員,而只能邀請當地教師兼職播報。雖然經過幾年的磨合,這位兼職播音員已被當地畬族群眾接受,他的語音語調也被當地畬族年輕人競相模仿,但是這種兼職的工作方式仍然影響了該節目的發展,也影響了畬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因此大眾傳媒在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時必須要把人的因素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大眾傳媒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的注意事項
大眾傳媒在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時要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內涵。近年來,隨著民族風尚的流行,越來越多的都市人將目光聚焦到了充滿神秘情調的少數民族文化上。在這個過程中,大眾傳媒成為展示少數民族文化風采的重要窗口,增強了各民族之間尤其是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但是當少數民族文化展露在廣播電視的視野之下時,少數民族文化卻常常淪為被消解和被想象的異文化,逐漸失真并開始遠離其融入在少數民族生活中真正的文化內核。比如彝族火把節就常常成為傳媒鏡頭展現的焦點。“火把節作為一場彝民族的傳播盛宴,是傳播和展示民族文化的大舞臺,該民族的衣食住行、社會關系、傳統藝術、民間信仰等得到集中的展現,民族文化深層結構即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倫理道德觀念、行為模式、審美情趣等得到突出的表現,它無疑使參與者受到潛移默化的民族文化精神的沐浴,增強自己民族的認同感、責任心。”[4]其中,彝族民間的“選美”活動最具看點。彝族選美要求非常嚴格,選美的彝族姑娘要盛裝打扮,手拿黃傘,在火把場外唱歌、跳舞盡展才藝。而評委們都是村寨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而選美的標準除了姑娘的身材容貌和穿著打扮外,更要看她們平時對待父母是否孝順,還有她們平時的道德品行和勤勞聲譽。但是為了滿足觀眾的獵奇心理和提高節目的收視率,編導們過度強調了姑娘們的美貌而忽略了彝族火把節選美的真正內核。這些經由廣播電視編輯們精心選擇的畫面所展現出來的彝族火把節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火把節的文化內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節目的真實性。甚至為了滿足拍攝的需要,編導還經常采用擺拍的方式。潘蛟教授2004年在《人文講壇》中談到的火把節見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村子在當地看來較為富裕。村民們在忙著收拾剛收割回來的煙葉,村中看不見任何火把節前的喜悅和躁動。經過打聽,才得知該村在幾天前就已過‘火把節了,而且過節的方式基本上是家庭式的,沒有舉行諸如斗牛、選美這樣的大型社會活動。此景有點讓人失望,顧問建議干脆來做‘擺拍。”[5]彝族火把節歷史悠久,通過火把聚合了各種社會關系,最終達到天、地、人的和諧統一。但在這里,少數民族文化變成了滿足現代都市人群視覺、聽覺的感官盛宴。因此,大眾傳媒只有在真正地理解并尊重少數民族文化內涵以后才可能真正做到對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
大眾傳媒在傳承與發揚少數民族文化時還應有所選擇。傳統文化并不等于優秀文化,也不等于文明。每個民族在進步的過程中都需要舍得丟棄掉自己落后的東西,切忌在強調傳統特色的同時形成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如一些民族存在著原始的平等觀念、婚姻上的近親習慣、“坐家”習俗等,它們的確是傳統的東西,但卻代表著愚昧和落后,是應該被淘汰的。對于這些文化內容,我們所采取的態度不應是保留,而是摒棄。最后,大眾傳媒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也是有局限的。張瑞倩在《電視對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修補”——以青海“長江源村”藏族生態移民為例》一文中也承認,這種文化修補的對象往往只是儀式性的信條和文化形式,而不是價值觀、生活方式等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修補后的結果也不是傳統文化的還原,經過修補的文化中難免會摻雜一些原本不屬于這個文化體系的內容。同時,傳媒人在面對少數民族文化的時候,原有的知識結構以及個人的主觀認識也會影響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為此,我們不能過分放大大眾傳媒對少數民族文化傳承上的作用。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是一個意義重大而又耗時耗力的工程,需要全社會各個階層共同努力。
參考文獻:
[1]吳飛.少數民族社區居民的電視體驗報告[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7(2).
[2]盧理洪,周玉蘭.少數民族文化傳承中民族語言新聞節目的開拓與創新——以景寧廣播電視臺《畬語新聞》為例[J].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09(3).
[3]劉冬.閩東畬族傳統文化特征[J].寧德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2).
[4]王萍.大眾傳媒視野中的少數民族節日與生存——以彝族火把節為例[J].貴州民族研究,2005(6).
[5]潘蛟.火把節紀事:當地人觀點?[J].人文講壇,2004(3).
(作者單位:貴州民族學院傳媒學院)
編校:鄭 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