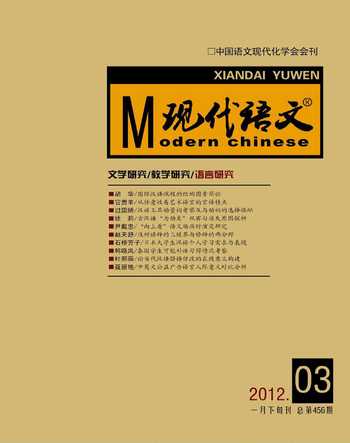從任意性看藝術語言的言語特點
摘 要:本文主要著眼于任意性原則,以相對任意性和絕對任意性的結合為切入點,總結出藝術語言的四個言語特點:藝術語言是反映真情實感的、包含隱性意義的、超越現實世界的、表現美學神思的語言。
關鍵詞:任意性真情實感隱形意義超越現實美學神思
索緒爾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中論述能指與所指關系的時候,提到語言符號的性質之一是任意性。他認為,一個完整的語言符號包括能指與所指,而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任意的,即語言符號是任意的。這里提到的任意性,我們可以從時空的角度對其進行更細致的切分,即相對任意性與絕對任意性的合二為一。相對任意性是指語言符號在某種特定的時空環境中保持性質狀態的穩定性,它強調大同小異;而絕對任意性是指語言符號不論時空環境的狀況不同或相同,其性質狀態等都在持續變化,它強調異中無同。按照辯證法的觀點,后者是片面的,它只看到事物變化的一面,卻忽視不變的一面。當然,前面提到的任意性還可以做另類的理解。相對任意性注重不變性,而不變性是指同一語言符號在不同時空環境中始終存在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我們現在提倡的科學語言就是注重穩定性的絕佳例子。絕對任意性注重可變性,而可變性是指語言符號在任何時空環境中都在發展變化,比如我們現在提倡的藝術語言就是變異性的典型代表。從某種程度上說,相對任意性的不變性內核是共時的觀點,絕對任意性的可變性則是歷時的觀點,而學界對共時歷時結合的呼聲是一浪高過一浪。其實,我們應該承認,要準確地把握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就必須權衡相對任意性與絕對任意性,求二者之同存二者之異,找到最佳的平衡點,以便使二者互通有無、精誠合作,共同為語言符號使用者服務。
就目前國內學界而言,研究藝術語言的學者不乏其人。當中,研究范圍最廣、學術成果最大的首推駱小所教授。他撰寫了《藝術語言和藝術語言學》等論文,并出版了《藝術語言學》《語言美學論稿》《藝術語言再探索》《藝術語言——普通語言的超越》等專著。其中,《藝術語言——普通語言的超越》一書中對藝術語言的言語特點進行了概括,藝術語言是自然的、具象的、靈活多變的、張揚個性的、富含感情的,它強調情感超越、感知世界與審美發現。毫不夸張地說,駱小所教授對藝術語言的剖析是全面且深刻的,對藝術語言的研究是細致且前沿的,這為學界探索藝術語言做了大量先導性工作。但是,學術活動是向前發展的永不停息的過程,學術思想也是多元的、辯駁的且不斷更新換代的。基于此,本文擬以任意性為立足點,以相對任意性與絕對任意性的結合為切入點,探討藝術語言的言語特點問題,錯謬之處敬請批評指正。
從相對任意性與絕對任意性的結合看,藝術語言是反映真情實感的語言。這里的“真情實感”應做這樣的解釋:“真情”指真實的情況,它指描述主體借助語言對客觀事件、事物等進行的真實反映;“實感”指實在的情感,它指描述主體借助語言把對客體的所思所想轉化為情感反映。前者具備普通語言的功能,后者具備淺層修辭的功能,當普通語言與淺層修辭放棄彼此間的對立,親密無間地共同服務于表達者時,藝術語言便應運而生了。更進一步說,相對任意性反映的語言符號的穩定性映射到語言上就表現為對普通語言的基本功能的借重,即客觀真實地再現事物或事情的原初面貌,這與“真情”恰恰相互吻合了;而絕對任意性反映的語言符號的變異性映射到語言上就表現為對普通語言基本功能的突破,即描述客觀事物之外的傳情達意,這與“實感”正好互相映照了。古人在賞析文學作品時常用“文似看山不喜平”來凸顯文章的優秀,語言表達出來的“天理人情”大概可以稱得上“不平之處”吧!例如:
(1)黑夜
像一群又一群
蒙面人
悄悄走近
然后走開
我失去了夢
口袋里只剩下最小的分幣
“我被劫了”
我對太陽說
太陽去追趕黑夜
又被另一群黑夜
追趕
——顧城《案件》
(2)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辜負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負了我的思量。
我為我心愛的人兒,
燃到了這般模樣!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該知道我的前身?
你該不嫌我黑奴魯莽?
要我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般的心腸。
——郭沫若《爐中煤》
例(1)是作者憑空杜撰出來的一個案件:黑夜是強盜,打劫了我,而我向太陽告狀,太陽去追趕黑夜,途中又被另外的黑暗追趕。作者所要表現的只是“日升月落”“日落月升”的自然現象,他卻不直接描寫,而是賦予無生命的太陽、黑夜以生命感知,使描寫主題躍然紙上,給讀者留下生動深刻的印象。例(2)中,作者以“爐中煤”自喻,借“年青的女郎”比喻祖國,賦予客觀存在的“爐中煤的燃燒”以個人情感,而表達甘愿為祖國奉獻生命的崇高愛國情懷。例(1)和例(2)都是作者充分調動藝術化想象,借助藝術語言,把個人情感寓于描寫客觀事物和表現個人思想之中,以達到“真情”“實感”的預期效果。
一般而言,普通語言因推崇理性邏輯而提倡“語言技巧說”,即把語言看作描寫客觀事物的工具;藝術語言則不同,它推崇情感邏輯,往往認可“語言無技巧論”,即藝術語言的表達是一種自然天成的藝術境界,受話人與其達到最高的審美契合,完全看不出藝術語言創造所使用技巧的痕跡。[1]藝術語言是內容與形式完美的統一的最高審美狀態,是在藝術語言傳情達意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藝術語言主張“文無定法”而“師心法”,正如清代畫家石濤在《畫語錄》中說的:“至人無法,非無法也,無法而法,乃為至法。”
從相對任意性看,藝術語言是包含隱性意義的語言。語言符號(包括藝術語言)雖然可以無限地進行組合,以表達近乎無限的意義,但某些語言符號的固定組合卻有著相對穩定的意義,對于藝術語言來說,言外之意的表達是主要的,字面意思的表達是次要的。根據王希杰先生的修辭“潛-顯”理論分析得出,藝術語言主要表達的是一種隱性信息,即發話人所傳遞的暗含在理性信息之中的實際信息。這些具有隱性意義的言語,一方面可以增大話語信息量,使話語言簡意賅;另一方面有助于把握交際對象的意圖和心理,尤其在一些特定的場合,可以順利地達到交際目的。
從修辭學上講,這些包含隱性意義的語言可分為四種類型:包含預設信息的語言、包含留白信息的語言、包含辭格隱含信息的語言、包含語境信息的語言。這些語言表達信息的特殊性,決定了它們不是通過簡單的言語編碼可以實現的,而必須借重于聯想這個傳遞中介,分別用語義聯想、語境聯想和語用聯想等聯想方式實現意義的內隱,從而達到言語編碼者的主觀意圖。這些包含隱性意義的言語表達,在當代小說創作中被稱為屏蔽。屏蔽是當代小說在表現特定情境中的人物心態、人物關系或促使情節發展的一種手法,它指對話一方有意或強制將話語屏蔽,未經信息通道傳送給交際對象的一種潛在話語現象。當然,使用這種話語表達方式要把握住“度”,不然很容易產生言語表達過程中的信息錯位、減值、增值、冗余、改值等語病。包含隱性意義的語言體現了言語表達者獨具匠心的運思,也必將考驗言語理解者與表達者在文思上的契合程度。例如:
(3)“你的火爐跟我媽的火爐一模一樣。”姑娘答:“是嗎?”小伙子又說:“你覺得在我家的爐子上,你也能烘出同樣的碎肉餡餅嗎?”姑娘歡悅地回答:“我可以去試一試呀!”(林薇人《空口道》)
例(3)看似只是描述了小伙子和姑娘之間一段再平常不過的家常對話,實際上作者要表現的卻是小伙子向姑娘求婚的過程。對話中雖然沒有直接使用與求婚相關的字眼,卻創造性地借“在我家的爐子上烘餅”代指求婚,借“試著在你家的爐子上烘餅”代指姑娘同意小伙子的求婚,既生動又含蓄地表現了求婚的整個經過。不得不說,這種曲徑通幽式的表達,展現了作者嫻熟的言語表達技巧與語言運用能力。
從絕對任意性看,藝術語言是超越現實世界的語言。絕對任意性告訴我們,語言符號的表達有很多種方法,不同的方法能取得不同的表達效果。藝術語言不同于普通語言就在于它抓住了語言表達的多樣性,在語言上完成了對現實世界的超越。這種超越主要是對理性邏輯和語言規范的超越,具體表現為對感官、色彩、情感、理性和語言規范等的超越。
超越感官的藝術語言表現為對視覺、聽覺、嗅覺、觸覺和復雜感覺等的超越,在修辭上表現為通感、移覺等辭格的使用。比如“綠色的希望”“很臭屁的話”“山接斜陽天接水”[2]等就是如此。超越色彩的藝術語言表現在色彩的實體、色彩的情感和色彩的哲理等三個方面,在修辭上表現為借代、諱飾等辭格的使用。比如“綠色家園”“藍色憂傷”“白匪”等就是這種情況。超越情感的藝術語言表現為感官刺激的情感、對立的情感和變異的情感等三種類型,在修辭上表現為夸張、空文等辭格的使用。比如“旌旗蔽日”“紅燭自憐無好計,夜寒空替人垂淚”[3] “窺探艙里,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可惡!然而……四叔說”[4]等就是這樣的情況。超越理性的藝術語言表現為意象的交錯拼接、懸想、空想等三個方面,在修辭上表現為示現、夸張等辭格的使用。比如蓬子的《蘋果》中“夕陽沉在山下,如一條老狗僵眠著”等就是這類描寫。超越語言規范的藝術語言表現為對語音、詞匯、句法、標點格式等的超越,在修辭上表現為擬人、倒置等辭格的使用。比如“綠楊煙外曉寒輕,紅杏枝頭春意鬧”[5]“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6]等就是這類手法的使用。總之,藝術語言對現實世界的超越是作者使用各種語言表達方法,對所見、所聞、所思、所想等的生動表現,體現了藝術語言與作者心靈在時空上的虛擬而真實的對接。
從絕對任意性看,藝術語言是表現美學神思的語言。語言符號的任意組合帶給言語理解者很多內容,有基本信息、語境信息、美學信息。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必然包括這三種信息,其中,美學信息是不易察覺的,它經過言語表達者的特殊編碼,以隱晦的方式出現,需要言語理解者借助于全面的知識儲備以及高超的理解能力,去捕捉話語編碼形式傳遞出來的美學信息。它是信息傳遞過程中除實際信息外的補充信息,是某些話語編碼形式所固有的美質,是同語境相互作用而產生的美學意味。例如:
(4)一朵野花在荒原里開了又落了,
不想到這小生命,向著太陽發笑,
上帝給他的聰明他知道,
他的歡喜,他的詩,在向前輕搖。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開了又落了,
他看見春天,看不見自己的渺小,
聽慣風的溫柔,聽不慣風的怒號,
就連他自己的夢也容易忘掉。
——陳夢家《一朵野花》
例(4)既可以看作是詩人以野花自比,也可以看作是詩人對具有野花特質的一類人的贊美。從詩中,我們可以總結出野花的特性:不以己小而自卑,不以境惡而害怕。隨季節變換容顏,不變的是對萬物的虔誠般溫柔。這首詩的意象并不新奇,形式也不新穎,卻用強有力的藝術感染力描述了野草的獨特之處,在同言語環境的聯系中給我們以美的享受。
誠然,本文對藝術語言的言語特點的探討并沒有做到盡善盡美。一方面,本文只是著眼于任意性,簡要梳理了其脈絡,大致區分出筆者認為較重要的四個特點。實際上,除此之外肯定還有其它特點,但因篇幅有限,暫不作討論。另一方面,學界一直提倡“百花齊放”,即對同一問題就其形式、內容、特點等都可以作不同程度的分析,或以點概面,或層層深入,以張揚個性思考,最終達到學術探討在深度和廣度上的不同擴展。筆者深感因知識儲備及悟性等方面不足帶來的學術探索之艱辛,但仍敢以粒米之力,拋學術鄙陋之磚,引學界高明之玉,祈盼相關的學術研究能百尺竿頭。最后,筆者借用駱小所教授的一段文字來結束本文:“藝術語言的創造活動,是一個涉及社會、心理各方面和各種因素的整體系統活動。發話主體的內在的主體情感在創造藝術語言時,不僅有感性與理性的對立統一、認識與情感的對立統一,而且有意識與潛意識的對立統一,表層心理結構與深層心理結構的對立統一。所以,我們說藝術語言的創造不是純主觀的,也不是純客觀的,而是主觀與客觀地統一。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對藝術語言的言內之意和言外之意加以理解和把握。我們才可以找到通往發話主體心理深處的道路。”
注釋:
[1]駱小所《藝術語言——普通語言的超越》第15頁。
[2]范仲淹《蘇幕遮》。
[3]晏幾道《蝶戀花》。
[4]魯迅《祝福》。
[5]宋祁《玉樓春》。
[6]《秋興八首》。
參考文獻:
[1]駱小所.藝術語言學[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2]駱小所.語言美學論稿[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
[3]駱小所.藝術語言再探索[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
[4]駱小所.藝術語言——普通語言的超越[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
社,2011.
[5]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9.
[6]顧城.顧城詩全編[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
[7]郭沫若.郭沫若——新詩[M].北京:北京電子出版物出版中心,
2001.
[8]傅德岷.唐詩宋詞鑒賞辭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
社,2008.
[9]駱小所.藝術語言和藝術語言學[J].楚雄師范學院學報,2000,
(4).
(官貴羊昆明 云南師范大學文學院6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