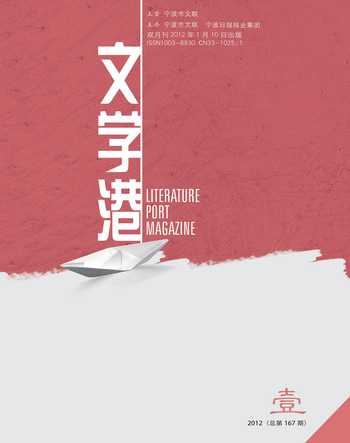心中珍藏的這盞燈照亮了我的敘述
謝志強 朱平兆
本期特別關注特推出朱平兆的長篇小說《一佳燈火》。原稿十二萬字,幾經修改,成了讀者面前的小長篇了。我把它界定為長篇傳記小說。因為,這部小說有現實的原型。同名同姓的人物陳亮確實要求朱平兆寫一部傳記。算是小人物的傳記吧?當然,朱平兆加大“虛構”的份額,由此表達對陳亮這一生命之燈的懷念。面對死亡,每一盞燈都那么溫暖那么明亮。陳亮這盞燈執著地亮著。因為,我們正在閱讀這本書。陳亮在故事里活著。
主持人謝志強
謝志強:我先談閱讀直感吧。陳亮的故事,是一個中國式的圓,從出生地出發,回歸的則是故鄉。總體上感到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有力量。當然,這前后不可分割,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只不過將前者的散狀凝聚,又推向高潮。平兆,你能夠把握住情感的流動,感動讀者,引起共鳴。
閱讀的直接反應,有三處細部。一是黃蓮懷孕時的喜悅,由兒子、丈夫去摸肚子里的“妹妹”來表達:二是主人公與大女兒的約談,所謂的“交代”,是中國式的表達:三是夫妻關于雙穴墓的交流,已是開放型的倫理觀。
這三處的感動,有著溫暖的底子。小說是寫關系,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就這部小說而言,我給個主題詞:親情。中國式的親情。上邊提到的三個細節,正是貼著“親情”的敘述。閱讀的反應如此。那么,你在創作的過程中,你意識到了哪幾處情感的穴位呢?因為,創作總是由閱讀的效果來檢驗。
朱平兆:能感動讀者,引起共鳴,這是作家最大的欣慰。要說寫作過程中的感動之處。除了您談到的三處,還有很多。陳亮發現疾病后,黃蓮說你不能走,我不讓你走,我不會讓你走的:陳亮拉著我的手要我寫以他為原型的小說:陳亮死亡時,黃蓮說你放心去吧,我會給你帶一些書和稿子,做你喜歡的事,等等。有好幾處,寫作過程中我被陳亮感動得唏里嘩啦的。
您把感動之處說成是情感的穴位,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小說是通過敘述方式架構起來的,通過人物線索和具體細節,獲得了血肉。長篇小說是一個完整的心靈世界了,這像一個完整的人。人有十二經脈,全身遍布了大大小小的穴位。長篇小說的穴位長在哪兒呢?我想應該在結構、線索和細節敘述的間隙中。穴位有大有小。大如丹田命門。讀者容易發現并感動:小如風池合谷。只有慢讀的細心的才能發現并感動。作家是期待讀者在那些穴位停一下的。讓這種感動沿著經脈做個巡回。
穴位不是作家刻意挖的,它與作品一起生長。渾然天成是理想的形態。
謝志強:偉大的喬布斯是個改變世界走向的人,但在死亡面前,他與你這部小說里的人物陳亮都處在平等的位置,都是人。記得喬布斯說死亡是生命最大的發明。在死亡面前,許多我們認為“重要”的事兒都不那么重要了,陳亮“發現”了親情的重要性,你這部疑似傳記小說(為普通人立傳)的主人公陳亮,有創業史,有情愛史,有疾病史,這部小說其實是寫陳亮對病的反應。故事由這種反應構成,他的反應,牽扯出各種人際關系的反應,而他是反應的漩渦中心。生意、情愛,都并入疾病這條主線上了。生與死、愛與恨、真與假、財與情,這一系列矛盾,都集合、糾結一起,人生,命運,商場,情場,考驗著陳亮的選擇,他的形象在這種關系的漩渦中表現,展示。你寫出了寧波普通商人的生意經,但小說著力點不在生意經上。文學創作也是發現,你是如何進行這次文學的發現的呢?
朱平兆:喬布斯死了,蘋果會不會爛?喬布斯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偉大的人物通常被人們符號化。所以喬布斯死的時候我會有這樣的反應。偉人要走到人們的心中,需要把架子放下。帶上他們那顆熱的心及內心的喜怒哀樂。陳亮是我心中朋友。是個小人物。小人物要走出去。需要自己抬起來。陳亮發現了“親情”的重要性。維護“親情”的一系列行動。使得本來普通的陳亮有那么一點崇高了。
文學創作是一種發現。《一佳燈火》的創作,我是先發現燈,后發現陳亮的。幾年前近距離目睹了幾位親人的死亡,包括父親、朋友、親戚。我注意到他們或要求給他們做總結。或把仇恨放下了,或費盡心機地為子女安排一番。靈堂里都設了一盞燈,悲痛之余我感覺到一股溫暖,溫暖流遍了全身。于是我想,人在死亡時有一個全新的開始。這是生命的最后綻放。生命之燈雖然微弱,但很珍貴,它似黑夜里遠方若隱若現的光亮。就這樣。我的心中珍藏著這盞燈。這盞燈溫暖著我。也給了我敘述的欲望。
后來陳亮走近了我。陳亮這樣的人生經歷在現實具有普遍性。陳亮面對生與死、愛與恨、真與假、財與情的矛盾的時候,自然會在人生,命運,商場,情場中糾結。陳亮是個燈具商人。我不可避諱寫了普通商人的生意經。但小說著力點并不在生意經上。先發現“燈”后發現陳亮,這是其中的原因吧。
謝志強:長篇小說講究個結構感。顯然,它與短篇小說各異,短篇小說講究個趣味性,即有味道。我把結構感換個說法,擺架子。長篇小說得有架子,那就是結構感。通常,我們說官架子,其實官大了,有意無意地會擺架子(不是貶意),那架子引出了尊嚴。可是,小孩如果擺架子,那就可愛了,就像短篇小說,根本擺不起架子,還來不及擺,就該收攤了(結尾),否則就有形式主義之嫌。
《一佳燈火》的架子,是由“我”(受委托的傳記執筆者)擺出來。陳亮故事的順序展開與“我”搜集陳亮的故事同步進行,而“我”是選擇故事表達方式、結構方式的介入者,主線是三個女人三個孩子與一個男人的關系。敘述的詳略取決于“我”這個見證人,敘述者。你(我把“我”視為現實的你吧)為什么選擇了這個較為妥帖的結構、敘事方式?
這個方式還達到了一個目的,即使主人公以另一種方式活著。陳亮的第一位妻子和大女兒,起初都恨他,這種恨的表達是:“他在我的心里早死了”,“我爸早就死了”。死其實有兩種形式,一是靈魂之死,沒人記得才算真正的死:二是肉體之死,他確實被癌奪去了生命。“我”的敘述,陳亮活著,活得開闊、豁達,這個意義上,他活著,靈魂活著。你把主人公放在生與死的臨界線上來表現,他對現實放下了。
朱平兆:把文學創作看簡單了,就是發現和表現的問題。前面我們談了發現。結構是表現層面上的事情了。是一種技巧。
《一佳燈火》是我嘗試的第一部長篇,如何擺好架子,曾經困惑過我。第一次動筆寫的時候,寫了兩萬字,覺得并不適合《一佳燈火》的敘述,放下了,一放好幾年。這放著的幾年中。陳亮一直在跟我對話。一直在與我聊。這個聊,不是實體的陳亮,是心靈的陳亮。有一次陳亮和我聊到了寫以他為原型的小說。我怦然心動。感覺找到了敘述那盞燈或者說陳亮故事的表達方式。就以“我”(受委托的傳記執筆者)擺出《一佳燈火》的架子,開始講述陳亮的故事。擺好這個架子以后,寫作就順利了。我的寫作是業余的,寫《一佳燈火》用的只能是周末,初稿寫了大半年。即使這樣,寫作中也沒有發生過續不下去的困難。
所以,回過頭想,我選擇“我”(受委托的傳記執筆者)擺架子是妥帖的。
死有兩種形式,我完全同意。那么,活著的形態不只兩種了,活著的肉體,活著的靈魂,除此以外還有有靈魂的肉體。暫不顧陳亮是虛構的還是曾經過去的一個實體,陳亮的靈魂在我心中是活著的。寫以陳亮為原型的小說是陳亮要求的,由此可以說,從“我”(受委托的傳記執筆者)擺架子不是我的選擇。是陳亮自己的選擇。在這里我還得感謝我這位心中的朋友。
謝志強:小說要塑造人物。寫長篇小說,作家要經受群體鮮明的考驗。你知道其中的奧秘,就是為每個人物配備一二個細節。例如,陳亮第二位妻子的嗑瓜子,鄉村親戚的說話響亮,阿強的墨鏡,第一位妻子的倔。記住了細節就容易記住人物,哪怕是個次要的角色。主人公陳亮,你配置了癢的細節,數處出現,但我覺得不夠有力,不夠結實,這個癢的細節還沒彌散到他的處境,還可往情感深處去潛入。否則,僅是個表面化的細節,與人物隔著,像隔靴搔癢那樣。你在構思中,如何設計人物的細節,即預先設計還是創作中閃現?
朱平兆:我個人理解,塑造人物是最見作家功底之處。人物的細節寫好的,虛構的人物就是真實的。反之,真實的人物就變虛假了。人物應該符合人物內存在的變化規律,符合他的生存環境,個性特征。這其中有奧秘,我還沒有完全禪悟。在寫作實踐中,我覺得配角,或者說出場少的人物容易寫,給他們配置一二符合他們性格的細節,就立起來了。如陳亮第二位妻子的嗑瓜子,鄉村親戚的說話響亮,阿強的墨鏡,第一位妻子的倔。因為出場不多,可以特征性。主人公就不一樣了,他反復地出場。在故事的漩渦中心。稍有不慎就會違背人物的感情變化邏輯,成為非自然人。我自感寫作的功底還不夠,還需不斷地學習和練習。
您提到陳亮的癢。就本意上說,癢不是為了寫陳亮的個性配置的,而是作為故事局部性的推動力。我覺得故事的發展單純交給時間是不夠的,除了幾條線索外,還需要多個內在的推動力,這樣故事發展起來更加自然些。陳亮的癢是安排推動陳亮與家鄉、與生意關系的局部性動力。當然。寫作的結果并不一定能實現作家的初始愿望。
在我的寫作中,人物細節預先設計和創作中閃現都有。自我感覺閃現更多一些。人物的性格設計好了,人物在故事內部各種動力的推動下。遇到事件或進入不同環境中。按各自性格反應表達應對,反而能增強人物的真實性。
謝志強:我對長篇小說的期待,除了人物的命運,結構的穩健,還有一個重要元素,就是,最好有個形而上意味的東西。
記得有人問海明威《老人與海》的象征。海明威答:那里邊沒有象征,只有一個老人和一條大魚。其實,《老人與海》有象征意味,那就是形而上意味的東西。但是,創作過程中,海明威當然不刻意去表現什么象征什么寓意,他僅僅是貼近老人與大魚的搏斗寫,寫著寫著寫出了“形而上”,——讀者品味出了。
這就引出了創作問題,作家怎么把細節寫好,寫得無意中有了容量、內涵,于是有了象征、寓意。《一佳燈火》里,有個明與暗的關系,只是你的筆力沒掘進去。暗就是死亡的陰影,而明,是一佳燈火的燈。我閱讀中就想,是不是將“燈”(亮)這個物質層面的意象,彌漫開去敘述,建立在扎實、結實的敘述基礎之上,讓“燈”的意象凝聚、照亮你的人物。關鍵是“我”的心中有沒有那盞“燈”去升華素材?
你在創作時,發現過“燈”的意象嗎?陳亮是燈具的經營者,生意的燈、故鄉的燈、生命的燈,我是不是想過頭了?
朱平兆:形而上意味的東西是作品走向偉大的重要因素,您跟我談這個問題,顯然高看了我,我非常感激。
在《一佳燈火》寫作過程中,想到過溶入點象征或者寓意,還企圖把“燈”作為照亮陳亮和黃蓮愛情的道具。從您閱讀的結果看。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這是我的筆力所不能及。
此前,我總稱自己為文學愛好者或者業余作者。對“作家”這個稱謂,一直心懷敬畏。今天談話中我自稱了作家,這其中有下決心的過程。這個決心就是今后的生命中我要讓文學占據更大的份額,也就是說,寫了《一佳燈火》以后,還想寫第二部、第三部作品。那時候,我會將形而上意味的東西加以更加認真的思索。
不想成為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成就偉大作品的作家也成不了好作家。有個形而上意味的東西不是想寫就能寫出來的,不但關乎作家的功底。并且還是可遇不可求的。想成為將軍的士兵絕大多數成不了將軍,但想成為將軍的士兵多數會是好士兵,還多了一些快樂。作家也一樣。有成就偉大作品想法的寫作也多了一些快樂,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