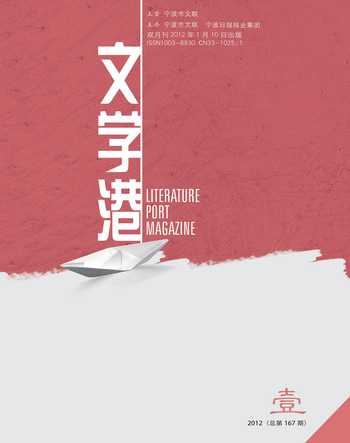安全保護證
趙柏田
這部小說。是2007年秋天我蟄居北京安內大街分司廳胡同的一段時間開始動筆的。那些日子,北京的天空一掃煙霾,藍得異常明凈。從胡同出來,隔著安內大街就是國子監街,不遠處就是鼓樓大街、雍和宮和有名的“鬼街”。這些我寫累了經常散步的去處。也是這個時隔一百余年的故事中人物的活動場景。日光之下。它們漸次變得像電影布景一樣虛幻。
在這之前幾年,我已飽受這個故事折磨。每年幾次短暫的出行,我都會帶著小說主人公的兩大卷日記踏上旅途。在浙江鄞縣東錢湖的一個悶熱的下午。我都已經看見了這個故事的輪廓。我寫下了一些片斷,一些對話,獨白,主人公的性的囈語。但我還是忍住了沒動筆。我覺得我還沒有準備好。隨后一年夏天在廬山牯嶺,看了老別墅群中賽珍珠的故居,那個晚上我夢見了自己在寫這部小說,夢中,我寫得非常順暢,那些寫下的句子似乎全記得。醒來,它們卻像受驚的鳥兒都飛走了。冥冥之中。好像有一股力量要我跑到北京來開筆寫這個故事。秋天的北京。薄如蟬翼的空氣。安靜的小胡同,我不是一直夢想著這樣來開始一部小說的寫作嗎?
首先吸引我的,自然是這個叫羅伯特,赫德的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青年在中國的傳奇經歷。我在進行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東部口岸城市研究時。發現在現代性降臨前夜的中國政壇。時時出沒著這個人的身影:光光的腦門,穿著雙排扣大衣,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從后來找到的他的兩大卷日記,同時代人的記述。和費正清先生的研究。這個人一生的輪廓漸漸清晰起來:他是在1854年19歲那年。抱著去東方傳播上帝福音的念頭從北愛爾蘭鄉村來到中國,擔任寧波領事館的一名見習翻譯。以此為起點。這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踏入了神秘、詭異的清廷仕途,一步步登上了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高位。他主宰控制晚清帝國經濟命脈的海關近半個世紀,經歷了波譎云詭的中國近代史上的各個重要階段,從太平天國運動、派遣第一個駐外使團、洋務運動直至世紀之交的義和團運動,他都深深介入并影響了晚清中國政務……
在通讀他的兩大卷在華日記時,我走入了這個人隱秘的內心世界的一角。盡管他身居帝國高位后,為人日益謹慎和圓通,為愛惜自家羽毛,對早年日記中的荒誕不經的經歷多有涂飾,但順著沒有清除干凈的蛛絲馬跡,我還是發現,他在我現在生活的這座城市居留的三年間,曾愛上一個叫阿瑤的船家女兒,也正是出于對這個女人的愛和悔意,延續了他半個多世紀對中國的復雜情感。我還發現,他們一起共同生活了七年,從寧波,到廣州,再到上海,并生下了三個孩子。這個煙花般絢爛的半殖民地情愛故事不久就結束了,當他在1866年——當時他已登上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要位——率領近代中國第一個海外觀光使團(即史家習稱的“斌椿使團”)前往歐洲時,他把這三個孩子送回英國,而自己則迎娶了一個門對戶當的英國小鎮醫生的女兒,并在短暫的度假后帶到北京充任他的總司夫人……
隨后出現在公眾眼里的羅伯特,赫德(也是史籍所記載的)。已完全是一位整日勞形案牘的官吏的形像。他把自己完全地獻給了他在中國的事業。獻給了海關,把海關建設成了正日益走向衰敗的帝國的最具現代化的一個部門。至于私生活方面,他時而還會在社交場上與一些妙齡女郎應酬交際。頗有紳士風度地獻殷勤,或真或假地說一些表白愛慕的話,但他再也不會像19世紀50年代中期在寧波城里那樣對她們充滿性的幻想和愛的激情。他的激情,已經在阿瑤這個女人身上耗盡了。只有在與他的倫敦代理人討論那些被他放逐的孩子的教育問題的信中,他還是會抑制不住地流露對這個女人的思念與愧疚,稱她是“人們能想像得出的最可愛、最有理智的人”,而自己則是個不折不扣的“傻瓜”。這個消失了的女人。留給他三個未成年的兒女,也帶給了他無盡的傷痛與愧意。
沒有一個人知道,阿瑤后來怎么樣了。據赫德向他的兒女們解釋,她在1865年去世了。由于資料的缺乏,我無法否定赫德的這一說法。她或許是死了,比如死于生最后一個兒子阿瑟時的難產或其他疾病。但對這沒有先兆的死,我總心存疑惑。一個那么健碩的來自鄉野的姑娘,怎么說死就死了?會不會是新婚在即的赫德把她像一只舊雨靴一樣遺棄了?聯想到這個人勃發的政治野心、他的帶有濃重維多利亞時代烙印的價值觀念和行事方式。這是最合乎邏輯的解釋。離開赫德后的這個女人。她或許在廣州嫁人了。或許回了寧波老家。她的情夫在以后的歲月里把日記中她的痕跡幾乎全剔除干凈了。沒有一個人再提起她。就好像她本來就不存在。她就像一粒灰塵消失在了流轉的大氣中。大時代里的女人命運。如同風中轉蓬流轉無定。也乏人關心,這個女人后來充滿種種可能性的遭際卻突然向我呈現出一處讓人性之光透射進來罅隙:歷史的盡頭是小說,史家止步之處,莫不是小說家騰挪身手的新起點?
鉤沉一個多世紀前的書信、電報、日記、奏稿和宮庭秘檔,這個叫赫德的孤獨者的形象也在漸漸走出扁平變得立體豐滿:他就像一個走鋼絲者游走在東西方兩個大國間,兩邊都是深淵,一腳踏空就會萬劫不復。是以他的人生成了一種“騎墻”式的人生,不斷地去調和,去彌合,去裝裱(這做派有點像他經常的合作伙伴李鴻章)。在青年時代的日記里,他給我的初始印像是謹慎的、柔弱的、多情的,情欲是理解他早年生活的關鍵詞,但后來他競變成了一個大獨裁者!在他的海關王國。在他的家庭的王國里,他都是說一不二的王。以至于一場場疲憊的父子戰爭后,他哀嘆自己是個失敗的父親。表面上他喜歡熱鬧的生活,內心卻常感孤獨。一個細節是,到了晚年,給朋友的孩子們精心準備生日禮物競成了這個孤獨的老人最好的消遣。
長達數年的實證研究和史事考察中,想為這個深刻影響近代中國進程的孤獨的外來者重寫今生的念頭越來越強烈:他跋涉在帝國官場的夢想與野心,他瞬息燃滅的情欲之焰和身處東西方沖突不為人知的苦惱,他對于古老中國向現代性轉型的歷史進程所起的作用……這一切蠱惑著我,又讓我重不堪言。在讀了維克多,謝閣蘭的一本關于北京城的幻想性小說《萊內,勒斯》后,我在這個句子下面畫上了醒目的波紋線:“兩獸相向,嘴對著嘴,爭奪著一枚朝代不可辨認的錢幣,左邊是一條顫抖的龍,顫動著翼、鱗和爪。右邊是一只軀體頎長、靈活的虎,它弓著腰,顯出強烈的肉欲……”我認為,應該讓東西方的情愛悲劇與倫理悲劇中隱含的文化沖突呈現在小說中。但文化沖突、文明碰撞這些寵大的關懷如何落入到一個小說中去?或者換個說法,小說有義務承載這些嗎?對此,米蘭,昆德拉早就有過一個著名的論斷——小說的道德就在于去發現惟有小說才能發現的。
于是出現了小說開場處的那艘船,一艘海上航行的船。故事的講述者阿瑟,在三歲那年,和他的哥哥、姐姐一起被父親送回英國去。同船航行的,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海外觀光使團的官員們:一個老派的官員,幾個同文館的年輕學生,幾個各有懷抱的海關洋員,一個笑料百出的奇妙
的組合。大歷史與個人命運就以這樣一種近乎天然的方式統一在了小說第一頁上的那艘船上。這個使團的歷史意義如何暫不去說它,對三個孩子來說,這是一條放逐之路,因為從此以后這些孩子都將成為沒有身份的人。他們甚至不能說出他們是誰。他們的生身之父,已只是一個影子,在法律意義上只是他們的監護人。這種感受在故事的敘述人阿瑟的身上尤甚。作為父親投身到大歷史中去的代價和犧牲,他們不得不先驗地承載被拋棄的命運,這在他幼小的心靈深處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他一直覺得自己是被釘住舌頭的人,不能說出自己是誰,從哪里來,這像鼴鼠一樣的生活,在人生初年使他對影子父親的仇恨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甚至使他對宗教也發生了懷疑。我這樣設置故事是試圖說明,父親的缺席是如何塑造了孩子們的生活道路。這個不存在的父親,如果他不那么不擇手段追求權力和榮耀。不那么絕情。三個孩子的生活之路就會完全不同。
正因為父愛的不在場,阿瑟長大后要去尋找那個逝去的影子,尋找自己被丟失的身份。在與姐姐安娜的不倫之戀后,他來到了中國。一個中英混血兒。他在19世紀90年代來到東方,會遇到什么人,什么事。這些又是怎樣影響他的內心的?想想這些就夠激動人心了。故事行進到這里,我似乎看到一個引入入勝的好故事正在像花朵一樣開放。
當故事流動起來,它的豐富性讓我這個作者也感到了吃驚。在與海邊曬鹽工的女兒小芹的戀愛以悲劇告終后。阿瑟走入了生命的絕境。在約書亞牧師的引領下。他“在黑暗中努力一躍”。終于受洗成了一個牧師。約書亞神父讓他感受到了強烈的父愛。他們一起去山西傳教,在一次官府發動的對傳教士的屠殺中,神父殉教了。阿瑟則從太原逃回到了北京。也就在這個時候。包括赫德在內的所有在京外國人已經在使館區陷入了義和團和清軍的包圍,即將遭受沒頂之災。正是在戰亂逃難的間隙中,阿瑟開始講述他和父親的故事。經歷了那么多苦難,他已經原諒了父親當年的作為。這時的他已沒有了仇恨,沒有了悲情,他是以純凈的赤子之心來講述他和父親的一切。而在小說的最后一章我們也會看到,那個強項了一輩子的孤獨的老人,在炮火震耳的使館區一邊寫下他對中國局勢的思考,一邊給他的兒子寫一封可能永遠也無法投寄的信:親愛的阿瑟,我不是個稱職的父親。我從來都不是個好父親。我現在正式乞求你的原諒。乞求安娜和死去的赫伯特原諒。親愛的阿瑟,原諒我。原諒我。原諒我。這個“壞父親”在死亡的陰影籠罩下發現。身為傳教士的兒子實現了自己來到中國最初的夢想。他是另一個方向上的自我。父子兩代人終于在命運小徑上交叉并重疊了。
仇父一審父。和最終到來的相互諒解和掛念,是進入這部小說的一條線。這里濃墨重彩書寫的是他們各自在中國的情愛故事。和父子兩代人的情感戰爭。感官危險的愉悅。或隱忍或狂暴的愛,這給小說末世迷狂的底色之外打上了一圈溫暖的光暈,也使小說完成了從文化差異與沖突的探討到父子關系和愛的真諦的探討這一有著輕逸的美學風格的轉身。另一條線索。從小說開篇寫到的斌椿使團出訪歐洲。到馬嘉理事件。再到義和團運動。如幕后的伴奏般漸次寵大。越來越喧嘩,直至湮滅了故事中所有的人。小說最后一幕。1900年,北京陷落后聯軍士兵們在頤和園里的狂歡,對小說主人公赫德而言,意味他在中國半個世紀的事業的全面潰敗,也是中國走向現代性的失敗的序曲。書名《帝國遺夢》(或《暮色降臨》)意即在此。
小說在這里顯得如同一個兩聲部的合奏,單章的一個聲部是兒子眼中的父親形像和家族往事,他在遺棄和放逐中長大。一次次走到死亡的邊緣。在世俗和仇恨中努力一躍,在一條傳播福音的荊棘路中讓自己的靈魂得以了安歇。另一個雙章的聲部,以十九世紀中葉“自強運動”為肇始,寫近代中國的一個個驚濤駭浪裹挾著人物跌跌撞撞往前走。幾代人鑿壁借光。總算迎來了現代性的一絲曙光,但一切努力隨著庚子年的北京陷落宣告破滅,帝國還將在隨之降臨的暮色中趔趄前行。這種結構方式,使我在寫作這個小說時覺得自己就如同在彈奏一架鋼琴,當我感到用第一人稱敘述過于疲乏,就轉到第三人稱上去。這使得我在兩個聲部都能保持飽滿的張力。
就像以前香港媒體評述我的寫作風格是“黃仁宇與史景遷的合體”,這部小說同樣是一個“不純”的文本,一個“合體”——一個小說和歷史的合體。多年來,我一直喜歡年鑒學派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所派定的那種“技工”的角色,這使得我在這個小說的寫作中時時提醒自己,對歷史細部的刻劃要如工筆般精細,對人性和愛欲的開掘要像挖土機一般執著。
把我把目光投向這個小說發生年代的人和事時,有關他們的各種觀點、書籍、圖像信息會一點一點滲入我的生活,它們成為了一個長時段里的我日常生活。因此寫作這本書也是對自我的一次改變。在史料的采擷和運用上,我在這個小說上是“先顯后隱”的——扎實的、細致的研究之后,就試圖學著去忘記,而只讓細節呈現。這或許就是這個小說的方法論吧。《乘槎筆記》,《航海述奇》,《中國海關密檔》,一百多年前的書信,日記,電函,《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按理說這些基石足可以托起一座大廈了。但我還是需要足夠多的細節。我不希望這部小說只是書寫了一個傳奇,它更應該是一闕在生活細節中流淌的史詩。最初的文稿就像有好多個缺口的一面四處漏風的墻,我只有老老實實用細節去填滿它。有時,我會為找到一個好細節,整日里都保持著飽滿的工作激情。可信的細節!閃閃發光的細節!對小說我有一個樸素的觀點,幾百上千個有意思的細節。就可以勾連成一部小說。我相信如果有上帝,它也一定居住在細節中。
可以告慰逝去的時光的,是我終于寫出了一部與預想相去不遠的小說。在眾聲喧嘩的當下小說圖譜中。它顯現了一個新的向度,一個對歷史進行現代性書寫的向度。即在對史實的忠實上,它有著專業史家的筆法嚴謹,在對歷史中的人性與愛欲的呈現上,它又與我喜歡的尤瑟納爾、多克特羅氣息相通。
如此,它才可以成為我穿過時光的安全保護證。
責編曉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