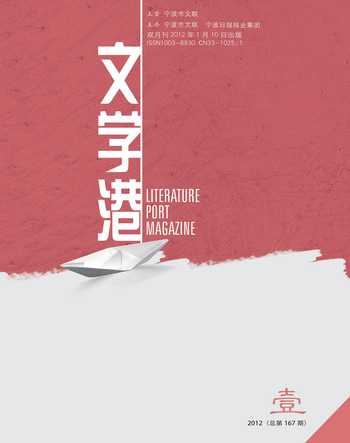諸神在島(外二篇)
賴賽飛
島被人在遙遠的海上惦念。理應比其他地方得到更多的祝福。
走進浙江漁業第一村所在的東門島,在2.8平方公里之內周旋,與漁民、漁船、漁網及魚蝦不期而遇,還與神廟不期而遇。最多的時候。島上曾有14座廟庵,計算下來的平均密度是每0.2平方公里就有一位神祗守護。
多神多福吧。當人們的祝福并不能表達心意的萬分之一,只有托付給萬物之靈。因此,東門就成了個諸神保佑的島,得到最多祝福的島。
各路神仙,屈指數來有通行的觀音、土地、城隍、關帝、藥王、山神,還有沿海特有的海神廟甚至是為鄉土先賢而立的廟宇。從這個意義上說,東門島上的神各有來歷,不僅始于繼承、借鑒,還源于自發的造神運動。
地方小,人家船多東西多,互相就湊得很攏,整個島很飽滿充實。
島中心密度特別高的~簇是東門老街,原居民聚居地。小小的三合、四合院貼身挨著,日間門長開,走進去有舊的石板地,舊的板壁,洗得很干凈。房子不大,卻有點曲徑通幽的味道,不寬的門洞,窄的通道,兩側堆了劈柴之類的什物,因為堆得整齊,反顯出拾掇者很勤快。再進一點,老的井,尺來高的四方口,旁邊擱球狀的青色塑膠吊桶,水淋淋的,眼尖的人還能看出其實是被剖開的大浮子。小的方方前院,還有更小的不規則后院,用石塊砌出些高低臺子。臺子上擱滿了草花,它們隨便種在泡沫盒子里、粗陶小缸里以及其他隨手用上的容器里。再大些的直接砌出花壇,四周別出心裁地飾以白色泡沫塑料小浮子,種上并不高大的梔子、海棠。人家之間留出的老街主道不足兩米,支巷就只有一米。白天青壯都作業去了,老人留守,近清明。遇見的老婆婆人手一卷經文或黃煤紙折元寶牒。口中不忘念念有詞。
由于正房都隱在著意營造的深處。很多人家廚房尤其餐廳都設在明處,中午時分。家家門口或窗戶透出氤氳香氣。令你想到在城里人家,為何聞到的就只有油煙味。在這樣的路上,緊挨眾人活色生香的日子行走,不孤單。溫暖,同時只有生活的純粹動靜,也安寧得很。
跟~港之隔的石浦老街一樣,東門老街也這樣將生活區經營得明顯有區別于作業區,凡空蕩、飄零、粗糙、嘈雜,濃烈的海腥味與狂暴的風浪。所有與漁業相關的元素都盡力摒棄隔絕,然后得到了與此相反的縝密整飭、精致優雅乃至寧靜溫馨。但還不夠,在東門島,高密度的神廟以及分布上與民居相依的特質讓人體會到島上人對于平安幸福的極致追求,那么直接、勇敢。與此同時,這種景象讓人隱約觸及海上生活的內里,一定有無數次的擊打、摧毀讓他們備受驚嚇與絕望,形成島上帶有明顯痛覺的歷史與記憶。出海,一次又一次,一代又一代,他們曾經的委曲、不堪重負和茫然恐懼,都在向神前的深深一拜里。
每年的開漁節都有這樣莊重的祭海場景。
公祭的場面浩大,一向放在寬廣的皇城沙灘,這幾年改為原生態的民祭,就落腳在東門島。這一日,沿港馬路上綿延人潮,一直通向島的制高點。島小,祭臺更小,觀禮者都靠邊站,圍著主祭群體——當地漁夫與漁嫂,看他們服飾明麗,神情肅穆,祭拜如儀。
紅氈、彩旗、大鼓、海碗,米酒與五谷……雖然是民祭。但組織有方。還是面向大眾供人觀瞻的。
真正有私密性的是私祭。主婦家趕個早,穿過小巷來到媽祖或海神廟,獻上用心籌備的供品,將自己的心思向諸神低低托付。這是岸上,在水上,船老大亦有體己的儀式,是為祭拜船龍爺。地點是神圣而高昂的船首。香燭供品一概齊備,外人多不得見。猜想祝詞總不外乎一愿大海豐饒如初魚蝦滿艙,二愿船家順風順水出入平安。
身處彈丸之地。固然有地域上的限制。但未始不是本能的指引,屋與屋、心與心,民居與神殿相依偎的東門島,一直抱成一團,棒打不散,水潑不進。可能如此。與大陸連接的銅瓦門大橋開通了多年,擔心這個島會走樣、會被同化至今顯得多余。
跟石浦老街不一樣的是,東門老街更緊湊更家常。不是專門的旅游區,行在其中的外人很容易被本地人區別開來,加以關注。他們不受打擾的目光里沒有淡定與漠視。依然保留了源自純樸熱情的重視、鼓勵,似在誘惑人開口,并準備隨時回應。
初上島。明顯感覺到因為人神毗鄰而居,兩者不自覺地相望相守著。島首銅瓦門門頭立著的是平水廟。任誰一進島就能看見。供奉的居然是大禹,他善始善終,治水一路從河流治到海里。
島尾立著東門廟。神號為天門都督。來歷縹緲,責任卻也明確。護佑從東門門頭經過的舟人。門頭水道有暗礁群,水流激蕩,漩渦密布,非當地人不能過。更近海處還有魚師廟,里面的海神實為聽魚聲找魚群指揮下網的魚師,被漁民想當然地列為海神。建廟祀之。經常用大魚骨作棟梁。
直接處在島上人家中間的有東津廟,主奉海神菩薩。屬于泛稱。島上最大的海神廟是天后宮(天妃宮)。到達天后宮要穿過東門老街,深入漁村的內部。天后宮祭祀媽祖。東門人稱媽祖為天后(天妃),根據東門人的說法,媽祖姓林,名默,福建莆田縣人。隨父兄來東門打魚為生,但她能預言人禍福,樂于助人,每于狂風暴雨之夜。站上高峰高舉火把為船只指引航向。
蒼茫大海。狂風惡浪里的一只船。船上的一群強壯男子,企求和感激媽祖娘娘的挽救——這個曾經的人間女子。總覺得。這是一種對家和家人的渴望。
媽祖的來歷清楚,但根子畢竟不在本地。東門島最知根知底的神廟是王將軍廟(王公廟),在泗洲路38號。王將軍本是元代東門巡檢司巡檢王剛甫,象山人。為官剛正,有勇有謀,多有義舉,深受百姓擁戴,這都是肯定的。然而先被罷官,晚年受誣入京師,竟卒于獄中,年六十八。此地人懷念他,也曾作歌慕之,歌之不足就為他建廟塑像,一致封他為將軍,尊稱王公。
在此,將一個人神化,敬為神,沒有遇見多大障礙。
記得我參加高考的時候,母親特地向石浦陽明山莊里的七老爺許愿。希望他保佑我考中。當時想,這位老爺是何方神圣,兄弟倒挺多,排行到了老七。后來忽然記起要我跟著去還愿,這已經過去好幾年了,親眼所見的時候方知七老爺原是戚老爺,抗倭名將戚繼光。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生前擔當國是的英雄,身后就這樣被民眾繼續寄于重望,甚至涉及到我的學習問題。
民間記錄歷史的方式,一向有虛有實。口口相傳,那是虛,傳之不足,干脆建碑立廟,那是實打實。文化的積累偏偏沒有在紙面上。因此傳說是一種浪漫和理想。以自由飛翔的方式。建筑卻是以沉甸甸的存在方式,一磚一瓦。都是記憶,也是愿望。
按紙面上的記載來看,人和神之間必然有很高的門坎。顯出嚴苛的等級制。很多修煉者往往費時久長卻容易功虧一簣。這里的人卻隨時搬掉門坎。將現實中的好人順利送入神殿。
島民生存之道,以海為生。船充當了移動的陸地。與海隔著幾分薄的船板。這個厚度就是陸世界與水世界的距離,也是生與死的距離,所以凡界與神界的距離大致如此,有自身開辟的秘密通道作為捷徑。有民心的抬舉作為臺階。隨時完
成穿越與上升,人、物莫不如是。至今,漁夫們的網無意中從海底拉上大魚的頭骨或肋骨,還會收在船上。上岸時送到魚師廟里受香火之供,一根躺在海底的魚骨就這樣成了神物。小小的土地廟里。有時不湊手。香被插在切開的蘿卜或大頭菜上,蘿卜們上升為香座,同樣不成問題。
神在這里扮演的是一個慈悲長者,因為出身人間,所以最知疾苦,因為最終拔離塵世,所以顯得大智慧,大手段。許眾生凡有休咎隨時求教。也許,所有神的前身都是人,只是他們的高度普通人難以企及。只是海邊人難以完全抗拒命運中的災難。所以這座島被神廟覆蓋。被無數的神聯手護佑,被接下來無數自覺的禁忌所禁錮。就像長命鎖似的,一重重鎖住海上人的身家性命。
頻繁的祭祀活動會一直延續,直到休漁。因為出海過程中,有收獲頗豐的人,記得大張旗鼓地來謝神,也有不順利的,再來暗暗討神的示下,俗云嘸結煞問菩薩。以此推斷,島上神廟密布的另一原因:地方小,成功者、行善者修橋鋪路的作為有限,造神廟就成為一個重要出口。
客觀地說,平常日腳——這里的人將太陽稱做日頭,將自身的生活叫日腳——廟里并非香火鼎盛,也非寥落不堪,它處在一個常態里,就像廟宇處在人居中間。與左鄰右居只隔著一堵墻。與前后人家也只隔著一條小路,正處在尋常生活之中。
過大目涂
大目洋之岸有個大目涂。小時候天天聽廣播,女播音員用地道的方言播報新聞及氣象。海邊的氣象播報離不開海里的事。挨個漁場過來,大目洋、貓頭洋、漁山、大陳漁場,北到東北風……長于纏綿的象山上鄉腔,那個大字開口度很大,目字急促且重,洋字稍短而輕,后面緊跟的是貓頭洋,貓頭二字皆曼聲吐出,平滑如水,至洋字小尾聲兒一挑,說不出的宛轉。
每次想起來,她的聲音和傳達的內容,都像城南舊事,遲暮的美里,仿佛深埋著靜默深井,大滴琥珀,以及類似于地溫。我從聲音里聽出的關于她的容顏也從此停留:端莊,白皙,發齊過耳,小方領白襯衣。也許涼風起時加上一件水灰色兩用衣,
回憶很遠,現實很近,氣象預報中的大目洋,我今天正走在它的縱深。
驅車行進在不久前的大目涂——大目洋最靠近陸地的部分。中間已矗立起一條高高的攔海大堤,3000多米長,壩頂凈寬7米,作雙車道綽綽有余,壩頂高程8米,可比兩層樓,圈出了10余平方公里,折合成更通俗易懂的計量單位是一萬五千畝之廣。
進入數字化時代日久,再糊涂的人也會對一些數字表示出敬意。尤其許多習慣于蝸居的人。湊近那些數字,就不止是敬意而是敬畏了。
這蒼茫的一片,非海、非涂、亦非地,可它曾是海、是涂,將來就是地、是城池。
眼下,它很適合嘹望、非想、發呆,一片由泥水、水草與水禽構成的奢華荒蕪。
單論荒蕪,有的是沙漠、戈壁灘,不過那是單純的荒蕪,乏人問津的。眼前的這一片,處在詩意江南。富饒的沿海地區。嗜土如命的城池邊沿。再沒眼力的也能從荒蕪中看出金子般的價值。
早在普通人依稀看見自己非分之想的時候,管理者在此看見了宏偉的施政理想,商賈看見了資本盛宴。
然而,看得真真切切并火速付諸行動的首先是大米草。從一棵、一叢,用不到幾年的工夫,它就將一萬五千畝先占為已有。縱橫的水道一下子變得狹窄并閃閃發亮起來。
接著白鷺來了、綠頭野鴨也來了……
春夏,長得汪洋恣肆的大米草完全融合為一片綠海,每一棵,半人多高,從頭綠到腳,綠得健康陽光。人無言以對。南來的海風輕易翻過堤壩,氣息溫潤,線條流暢,然而作派強勢,推涌著長草向著北面陸際一輪輪滾過去。成群的白鷺自鮮美的草甸深處飛起。低空盤旋的時候,白鷺的翅膀并不完全打開。在半折半合之間,腳也不曾用力往后延伸。站在近處,就能看出它們是拎著自己兩扇優雅的翅膀,赤垂著一雙零丁的長腳,在草尖上空翩然。雪白的,在青春動感的綠色大背景上。似一群輕盈潔凈的靈魂乘風而起,充滿欣悅。
比起白鷺。綠頭野鴨飛翔的愿望低得多,總是在殘存的咸水蕩里埋頭找海鮮吃,看它們不知疲倦地往前或往下夠。有時入水太深,不體面地撅起屁股。甚而兩腳丫翻天。
秋去冬來,大米草總要全數枯黃,太密集,倒是支支直立。將荒蕪的印象疊加成荒涼,幸而還有白鷺從草叢中偶爾飛起,一只,悄然。世事變幻,身下的背景已換成了衰草連天。映襯著它就像一支蒼白孤獨的靈魂在傍徨無定。
綠頭野鴨一如既往地游戈著找食,腳似乎凍得紅了些。水蕩里有人遺下的蜈蚣網。一節一節延伸,旁有進口前無出口。里面多少捕到了魚蝦,一只野鴨順著不知哪只進口追進去了。只知往前,不知后退。一直鉆到了封死的網底。網有一小半浮在水面,空間有限。這只野鴨掙扎著,毫無出路,積蓄力氣,再掙扎,再而竭,竟安靜了下來。
我用能找到的東西去夠網,差得很遠。險些將自己陷進去。一而再之后,也安靜下來,開始像上帝那樣看著它,看出它此時應該做和唯一能做的就是后退。
對該鴨表達了足夠的著急無奈之后,將它留在了網里。凍死、餓死或淹死,命運在等待著它。當我像個未曾救美的偽英雄轉身離去,之前自認大智慧而生出的無盡憐憫變成了難以言喻的沮喪,仿佛今日野鴨子遇見網,我遇見野鴨子,都是個悲劇。
風,這次自北而南,從陸地刮向海面。與春夏海風的怡蕩相比,冬季的陸風兇猛、凜冽,呼嘯著穿過血肉之軀,并在四周枯草之間掃蕩出一片凄厲的瑟瑟。
我顫抖著繼續走向深處。拜某個投資商所賜,荒蕪深處居然填出了幾條通道,出奇的寬廣,并且隨心所欲。據我觀察,有好長時間沒動靜了,究其原因,可能是投資商當時考慮不夠充分。
想想吧。這里原本是海龍王的地盤,不似土地爺好糊弄,要在此建立人類理想中的亭臺樓閣,需要往里面喂多少土石方呀。所謂海量,自然胃口很大。他沒準老道失算,后繼乏力了。機器聲隆隆。飛沙走石一場。遺下了這么個大場面。就像一個與荒蕪特別配套的中央舞臺。供有需要的人狂奔、大吼、飛旋,等等。
離春節沒有幾天了,這會是我虎年最后一次來。這之前和之后,過大目涂,再過大目涂,四季的海風吹過。晴天的陽光和雨天的雨來過。荒蕪將被繁華一點點蠶食。證明的無非是:如今易逝的不再是繁華。而是荒蕪。看上去有價值的荒蕪尤其易逝。既然如此,失落跟著轉向,找尋也才剛剛開始。
總是這樣。比如懷著自由的目的,自愿把自己放進城市這個高壓艙里。用不著多久,海水退卻之處浮現出一座嶄新城池。滄海桑田,這個詞注定會在這兒貶值,失去起碼的縱深感和負重感。但也未始沒有好處。幾輩子的事情,只能在傳說中領教的一切。現在都發生在可預期內。就像自然孕育的神秘過程,如今大白于天下,敬請圍觀。
圍涂工程起自2004年,2007年大堤合龍。合龍當日,海水作過一定程度的掙扎,自然迅速降伏,當時也沒引起多少轟動。這個半島當年交到先人手里,只相當于一副骨架,除了海,就是山。到如今骨肉勻停,曲線玲瓏,都是先人手
澤。那些高高低低、長長短短的堤壩,見多了,就平常了。當它是自然存在。只是以一般的海塘歷史來看,從海涂淤積達到一定高程,圍塘,而后養塘,再到種植耐鹽堿植物。然后成為平整肥美的水田、菜地,最后成為宜居之地人丁興起雞犬相聞,自有一段漫長的熟化歷程。
而現在。算算大約只需十年時間。
還是不能接受既成事實:一片海在我的注視下消失,一片荒蕪由從前的海底噴薄而出。再往下注視。在可預期內。繼海涂上的原住民不知所終后,白鷺將翩然飛走,綠頭野鴨追隨其后。最后。不會飛的大米草將在鼎盛時期全數壓入萬劫不復的深淵。這一點似乎沒什么好可惜。它是外來侵入生物,本在可誅之列。緊接著,萬物之首的我們隆重進駐,將比大米草更來得欣欣向榮。
瞻前顧后。從大目洋開始。留在童年記憶中的,確乎遙遠,然后是大目涂,有點土氣的名字。名字底下無數不起眼的土著,現在有必要特別一提,它們是:彈涂魚、紅鉗蟹、蛤蜊、蟶子、香螺、螺螄、青蟹、望潮、鰻魚苗……現在,它稱作大目灣,后面還有新城二字作后綴,聽上去比大目涂時尚多了。
這一片的西側。還有較早的大目涂一期,都算攏來。總共有18平方公里。不過。大目洋有1800平方公里。絕大部分海域屬于象山。象山陸域是1100多平方公里,如果將象山拎起來頭朝下摁進大目洋,也不夠填它的。因此,這點面積算不了什么。何況人們向來對平地有一種癡迷,天官賜福,這里真是天造地設,將山頭削平填進海里,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樣的簡單易行。
這些,彈涂魚們、綠頭野鴨們甚至大米草們顯然是不懂的。
就像未來被高度壓縮,打包快遞到面前,那片曠世難遇的荒蕪,留予人嘹望和穿越的時間越來越短了。
鶴之浦
回到鶴浦。感覺是回到了船的故里。
鶴浦一直有拆船場,專拆木船的,或專拆鐵殼船。它們往往毗鄰眾多的造船廠,這樣的安排看不出天意。卻頗有人世間的意味深長。仿佛是命運造就的一種另類洄游。有著更為復雜艱危的歷程,值得人追溯。
跟牛馬一樣,勞役了一輩子,船終被棄置,固然是落寞,同時有逍遙。可惜不見得都能牛解軛,馬放南山,更多的船最后是被拆解的。
后龍頭海灘邊的那個拆船場存在了五六年,如果一個月拆二條來算,也該拆掉上百只船了。
迄今為止,這個船場拆的全是老木船。
沒有專門船塢。但可趁大水潮。將船一舉拖上岸邊下手。先清理掉油與機器,掃除艙面上的所有,最后輪到拆解船木。
這使我有機會在此看見船的一生:從外看到里,一直看到了骨子里,從新看到舊,而且是當初樹剖開成板看起,一直看到還拆為板。
最舊的船,是它的船體被分解后曝在岸上。像曬鲞一樣,一塊一塊的舊起來。邊邊角角都不放過。那種完全徹底的舊法,讓每塊船板起細密的裂縫。油漆早不見蹤跡,船板還原為木的本色,自然中的黯淡,重新掩蓋了它的國色天香。船釘起走后,留下深的傷痕,略呈方形,顏色較他處濃重,幾近黑色。有些船木被故意留在露天接受日曬雨淋風吹,肉裂,漸失,留下樹骨、樹筋、樹結,依然鐵板一塊。這些走了幾十年的老木船所用的大多是來自南亞、東南亞的硬木料,有些船板一米多寬居然是獨出的,每根巨大的龍骨,見圓見方,厚重得好像沒人能抬得起。玉肋次之,更長。
站在舊船板堆積的木山中,想象遙遠的原始森林。參天蔽日的大樹,沉重陌生的伐木謠響起,它們倒下、集體走出,越過重洋,經過幾十年的時光漂流。最終來到這個所在。是一生尋找的歸宿地。只是旅程遠未結束,這些經海水浸泡更加艱固的木料可能出其不意地現身在他鄉,有的龍骨之類的大料會被原樣豎在旅游區或者新區作為有寓意的標志,承載寓意的還有老舊的舵盤、鐵錨,不可思議地登上大雅之堂。小些木料用作室外露臺甲板。更多的用作家具。
大概沒有多少人會是因為實用才選擇老船木家具,它們絕對的笨重、桀驁不馴,看上去像鋼鐵一樣的硬。可它分明是天然可親的木啊。經過精細打磨,先天的紋理,后天形成的傷痕累累,清晰地疊映之下,仿佛是種種經歷的重現,卻又刻畫得若無其事。當年的美麗、成就、創傷、殘缺。無非是一種經歷罷了。所有征服者都已過眼云煙,獨有它征服了歲月與大海走到現在。
制造老船木家具是艱難的,它太硬,固守著自身的形制。改造者只能順勢而為。多付一些打磨功夫。讓它的堅強不屈顯示動人的光澤。坐在這樣的老家具旁邊,大概能感覺出入生磨難的輕浮。就像我此刻坐在老船木堆里,將萬千感慨投射到它們身上。順著無處不在的裂痕深入肌里。它們的堅強與沉著讓我感到自身的確不堪一擊。
有春風桃李花開日,就有秋雨梧桐葉落時。當這邊老船以緩慢沉重的節奏一塊塊拆開,不遠處的新船正大塊拼接快速成型。
拆船場拆去了一個舊時代,新船廠正創造新時代。走在夾縫里,思考左右逢源與左右為難的含義,像進入了一條漫長的單行道。
新船的工場顯得整潔規則。船在這里被當地人換了種名頭。稱為大輪,從事運輸業者就叫撐大輪的。單從字面想象,如同看見一個人使一支竹篙在太平洋里劃著一只幾萬噸級的鋼鐵大家伙,脫口而出的現代童話,典型的超現實主義。
在現代化程度相當高的東紅船業,我看見在造的有一只為5萬多噸級,這可能是石浦港能走得出去的最大噸位。寬30多米。長190多米。凈深17米多,算上駕駛臺40來米高,要用去鋼板近萬噸。
第一次去的時候。這只船遠未成形。它的各個部位被分成110多段在各個車間加工:磨洗、切割、造形、焊接、噴漆。巨大的行車,背負著重物,像個手腳麻利的跑堂在車間之間來來去去,它的表面是平板一塊,首鼠兩端,前后各有一個駕駛臺藏在下面。看上去渺小。跑起來絕對的無人駕駛現象,滑稽得很。彎下腰,才能看見駕駛人精靈似的若隱若現。
以自動化為主。船場空曠寂靜,只有鋪在地面上的厚厚鋼板。身邊聳立的鋼構件,暫時還真看不出船的樣子。這是個鋼鐵主宰的世界。硬朗的初春海風,船件動輒大開大闔的剛性線條。未被油漆完全封閉的鐵腥味,船廠涌出來的青壯男性員工。手工明顯退卻,幾近消失,船周邊的鋼架構成十字網。只有少數焊工釘在高處如蛛。完成轉彎抹角的拼接,固執地將強光與灼熱向世界昭告,但已寥若晨星。少數人才能把握的場合,作為外來入侵者游走在如此質地堅硬規模巨大規則嚴明的世界。威懾感和排斥感很強,不容接近。人情味淡薄到若有若無,自主意識收縮之下,強烈感知的只有自身這一點子肉體的柔軟和溫熱的血液,唯一能與之抗衡并有機會凌駕其上的,大概只有強大的想法。
我看到了各種新船。新到一塵不染。接觸它的人都戴著手套,新到不落地,被擱在氣墊上,其實我還從它的每塊鋼板看起,看到被氣焊割開的嶄新的邊緣,露出鋼鐵的內里,純凈的青色,看見兩塊鋼板被拼接在一起,之間留下一條平整的焊縫,深入雙方的肌體,也是純凈的銀青色。看見了船體構件中出現的大大小小空洞,那是為鋪設電、
氣、水各類管路預留下來的,像一組秘密通道。看見裸船,還未被裝飾的形態,下到它的深處,完全掉人鋼鐵的內部。被它復雜的地理徹底迷惑。又被它強悍的氣味數次擊倒。在此之前。終于看清它秘不示人的內部結構。充滿解剖學意義。
平地高樓起萬丈,暫時沒有海容納它,陸上的船們顯得特別氣勢恢弘。最后一次去看它直接爬上了船頂,這是目前海岸的制高點,從這里能平視或俯視左鄰右舍,它們都是大輪。有部分仍是本廠的,更多屬于其他船廠,一只一只頭南尾北排過去,密集的,老老實實,像巨人酣睡,把所有圍著打轉的人都形容成了蟻族。
沿鶴浦鎮所在地的這段海岸線排列著五六家大型船廠。集聚了幾十臺巨大的龍門吊,橘紅色、寶藍色,門寬五六十米,高四五十米,遠遠的就能望見它們高昂的頭顱。如果都是經陸路進來的。估計會讓沿路的交警吃驚苦惱很多次。我常把它們看作出世的風景。在晨曦中。在夕陽西下的時候,它們的頂端能照到最早的陽光和留下最后一抹。雖然短暫,可是像新希望一樣動人。正午也是好的,能照亮全身,強烈的光芒與耀眼的色彩,頂天立地的長方形,似一冊冊煌煌巨著。
除卻自然風情,如果人文鶴浦還能讓我留戀,大概就是作為船里——船的故鄉。整個鶴浦像一個巨大的露天船舶博覽館。只從功能上分,從小到大,有供觀賞的船模、輔助用的小舢板、捕撈用的漁船、還有客運船、貨運船。鶴浦也像一部攤開的船業發展史,里面記錄了從傳統手工、半機械化、現代化拼裝的造船方式,呈現了初裝、半成品、已臻完美的狀態,反過來也是:待拆、拆成了半邊豬頭、四分五裂各歸其位。而且。活生生的。一切都在進行時。
那些嶄新鮮亮的,或者飽經風霜的,大至如同龐然大物,小至精致把玩的手工藝品,都掩蓋不了背后船人的辛勞、智慧,個人奮斗與集體協作的完美結合。一只船的出生與歸宿,從頭至尾承載無數人的命運,鶴之浦,鶴的故鄉,這個擁有美麗優雅名字的地方,輕舞飛揚的面紗之下。是作為南田島黃金一角。大多數時候。它像海面上一只小小的漩渦,充滿了投機、機遇、博弈、冒險的巨大助推力。表面堆滿了喧囂的泡沫。但我始終相信船,船是認真的,很結實,不是海面上風吹出來的泡沫。不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因此不管是造它,還是使用它,甚至拆解它,無論是用生長了許多年的木。還是干錘百煉的鋼。都真實可靠。它們源源不斷地自這個地方被孕育出來,幾番經風歷浪,又回歸,見證了一個地方生生不息的內在——沒有船。就沒有鶴浦,就像沒有了魚。就沒有了石浦港。
同時,船業的頑強存在與持續壯大,一直在表明有很多人的身家性命在海面上行走。大海,繼續接納并養育著我們,沒有比這個消息更讓人心安。
5月中旬。大水潮,一只老木船從外海被帶到拆船場等待解體,動力還在,艙面破爛,奄奄一息如頭擱淺的鯨。它的寬度是6米多。長30多米,就當時的船來說,可算大型,但把它豎直了量還不及大輪身板的寬度。從它身上,會拆出數目不清的油料、廢銅爛鐵,約幾十方老木料,那是舊時代的全部質量和價值,船的傳奇經歷與每道傷痕未計算在內。
當場主領著數名拆解工登場,手持鋸子、鎯頭圍著它打量,活像叢林中冒出來的古代勇士圍著一頭大型獵物互換會意的眼神,觀者如我不免黯然告辭。
前后不過幾天,不遠處有艘新鋼質運輸大輪下水,當鞭炮響起,香檳酒飛濺,兩旁用于固定的粗大鋼繩頂端彈鉤被敲擊而彈開,自重成千上萬噸的它從氣墊上輕盈滑落到海里,不過幾分鐘的工夫。沖出一堵高高水墻。剎那間令人窒息——新時代的氣勢越來越波瀾壯闊。這段時間內,隱在附近港汊里邊的小木船場叮叮咚咚敲出了兩只舢板,躲在堤壩邊老屋里做船模的老人還未賣出半支船模——或許他根本意不在此。其他船廠建造的運輸船、漁船、小型游艇暫存不計。
這個時代,這個旋渦狀的小鎮。船走船歸船生船消的我的故里,注定讓人忙于記錄。
責編曉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