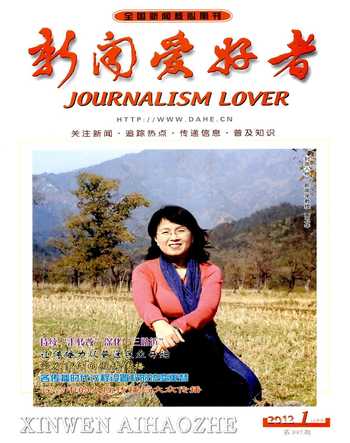十年來中國影視藝術傳播的文化指向
李琳
【摘要】新世紀新十年,中國影視藝術不斷發展,呈現出了新的文化指向:政治意識形態導向與大眾娛樂調和,個性化創造與文化工業結合,本土文化凸顯。闡釋新的精神內涵和價值指向,對調整當代中國影視的生產機制及面對世界的敘事方式,促進當代文化的發展都有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新十年;文化工業;本土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世紀化轉折,人們的社會文化心理和審美風尚都有了巨大變革,平均、單一、模式化的文化觀念開始走向多元,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共存。新世紀以來,以影視傳媒為載體的文化藝術在繼續擴大這一文化轉變的同時,更多地呈現出一些新的指向。
政治意識形態化導向與大眾娛樂的調和
縱觀中國電影的百年發展,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中央政府強化對影視文化的調控,政治意識形態化導向一直是貫穿始終的中心。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治意識形態化的最直接體現就是“主旋律”影視創作現象,各種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題材熱方興未艾,出現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為創作題材的影視作品,這些作品在特定的時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以共產黨優秀干部為題材的《焦裕祿》、《孔繁森》等;以革命歷史題材、特別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為創作主旨的《大決戰》、《百色起義》等;以反映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光輝業績為主題的《開國大典》等。在中國影視文化的構成中,意識形態標準對影視創作的引導性和影視評選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電影的指令性行為與藝術性行為間缺乏融合,這使得多數“主旋律”影片在藝術上、市場上甚至意識形態教育上都沒有收到想象中的傳播效果。
政治意識形態導向與大眾娛樂是影視藝術要面對的兩個內在矛盾,如何使影視作品既能實現其審美教育的功能,又能充分滿足大眾娛樂的感性審美需求,是當代文化現實給影視藝術提出的一個嚴峻的課題。在經過對曾經的文化現實深刻反思之后,中國近十年來影視藝術在思想導向和大眾娛樂之間尋找到了一個“結合點”,通過“主旋律”影片的平民化和市場化探索與“娛樂片”的理性思索風格,來實現意識形態導向與大眾娛樂的和解。這種力量,對這一時期影視創作的題材選擇、敘事方式、價值觀念的表達以及影視語言創作都產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響,從而形成了特殊的時代風格。
《集結號》(2007年)作為一部主旋律影片,改變了英雄在觀眾心目中的形象,與中國電影中主流戰爭敘事那種人性的缺席拉開了距離,讓人印象深刻地記住了甚至是觸摸到了民族解放過程的殘酷和不朽。它融合了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思想,影片中有血有肉的軍人被呈現在殘酷、瘋狂的戰爭中,人被歷史所淹沒,被歷史必然性所摧毀,就像一粒塵埃,幾乎可以被忽略、可以被以歷史和集體的名義取代。谷子地倔強地尋找著自己的兄弟們并為他們正名。強調個體感受及人性的概念,為每個人而努力,這不正是我們對戰爭最好的反思嗎?個人永遠是戰場上的犧牲品,戰爭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每一個個人。同時,該片用最先進的技術手段真實地再現了戰爭史實,在中國戰爭題材的影視創作中開辟了新的道路。
電影《建國大業》(2009年)是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的影片,它在形式上擺脫了傳統電影歷史模式對這一類型片的宣傳,說教的功能大為改觀。影片側重表現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發生的一系列故事,從抗日戰爭勝利的重慶會談到最后新中國成立的開國大典,中間4年多時間中的共產黨、國民黨以及各個民主黨派之間的種種變化和糾葛都得到了一一展現,突出了當時多黨合作以及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同時影片將國共兩黨主要人物的喜怒哀樂都給予了描寫,凸顯了人性化,突出表現生活化的領袖,著力把領袖還原成一個個普通人。在表現形式上,170多位國內以及國際一線明星傾情加盟,使觀眾在應接不暇的眾星表演中重溫了那段經典歷史。
《云水謠》(2006年)則在普通人物的身上表現著一種傳統的道德情操和倫理準則,在贊美美好愛情的同時,讓我們對那段不可磨滅的歷史背景更多了些體會,可以說是主流意識形態電影的一種創新,取得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成為年度最優秀的國產電影。
《唐山大地震》(2010年)是馮小剛繼《集結號》之后拍攝的另一部主旋律電影,故事突破了原有主旋律電影的束縛,沒有將敘述重點放在人們對災難的拯救上,而是通過一家人的遭遇演繹了災難對普通人的傷害,可以看到導演糅合主流意識形態與商業價值,努力縫合兩者本質性沖突的追求。
近十年這類影片的敘事策略不是簡單地圖解政治、圖解生活,而是尋找一種對大眾審美情感產生巨大召喚的敘事模式。主旋律電影商業化、商業電影主流化之間碰撞、交叉和融合形成的主流商業電影,或許就是能滿足當代中國觀眾的觀賞期待和觀賞快感的類型。
個性化創造與文化工業的結合
在新世紀的電影創作中,作為一種文化產業生產方式,統一的集體“寓言式”的創作不復存在,我們通過對新世紀電影創作繁榮的局面考察后發現,個性化的真實與商業性的本性得到了很好的結合。這類影片一方面善于在敘事手法、表現手段上進行商業化包裝,另一方面又關注現實人生并給予溫情關照,使商業化包裝和文化品位得到一定的平衡,從而贏得了市場和觀眾。
2006年,投資不到300萬元的小成本電影《瘋狂的石頭》票房高達3000萬元,幾乎使中國觀眾“瘋狂”,這部影片把中國當前社會現實的困境放到一個喜劇情景中去,力圖通過盡量多的場面、事件、話語、人物來展示,成了中國電影的代表作和類型標本。寧浩很聰明地將草根文化貫徹到底,并以幽默為幌子巧妙調侃了時下社會的弊端,無論是下崗問題,還是綜合執法,抑或是行騙招數,都被他以極為睿智的手法調侃和批判,討債、下崗工人(即將倒閉的工廠)、拖欠醫藥費、買彩票、玩短信彩鈴等生活場景隨處可見。2006年是中國電影產業的一個標志性轉折,《瘋狂的石頭》一鳴驚人,《大道如天》等影片票房突破千萬元,此外,《天狗》票房680萬元、《雞犬不寧》票房550萬元。
這種“操作性”影片都在暗示著一種趨勢,不再將那些教化的勸世寓言和道德神話作為最終目的,也沒有被好萊塢似的商業模式完全同化,而是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體驗、描述和表達普通人所真正遭遇的普通的生活。如陸川《尋槍》(2002年)、馬曉穎《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2002年)和《我們倆》(2005年)、姜文《讓子彈飛》(2010年)等,這些導演縱橫在商業化的大潮中,充分體現自我的真實的個性,竭力堅持關懷普通人的文化立場和觀點,以實現自己的藝術理想。這些影片沒有挑戰現存倫理和世俗道德觀,卻非常切合主流觀念,受到了觀眾的喜愛。平民化的視角、類型化的策略、市場化的觀念、不拘一格的電影語言、豐富的想象力,一種新的電影觀念、一種新的電影思路、一種新的電影標準,這些變化影響了一批帶有新觀念的年輕導演,新世紀在為他們提供激情和信念的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展現才華的環境、輿論和機會。
在文化多樣化和多元化的局面中凸顯本土文化
21世紀影視傳播的明顯走向是多樣化、多元化。文化的傳播多樣,電影、電視、網絡打破彼此界限,電影和電視在技術上相互借鑒,網絡介入電影、電視傳播,可以說,高科技的運用在為影視藝術拓寬新的境界的同時,也在拓展著現代社會人們對藝術、對美學的全新認識,其本質是人的視野和文化角度在擴大,數字技術和寬帶網絡的發展和運用更新了人們的思維形式,引發了人們對人自身的重新認識。文化的指向更加多元,單一的文化指向不復存在,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更顯現本土文化的重要。
對于中國電影來說,其藝術感染力、文化傳播力乃至核心競爭力,最顯而易見的優勢,是中國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國家的、幾千年相對獨立的文明發展歷程,有著滲透到當代生活的各個層面的文化傳統。中國主流電影都體現出中國電影的文化傳統和現實主義傳統,體現出當下本土觀眾的欣賞需求和審美趣味。在全球化背景下,電影的文化價值最終都體現在本土觀眾的需求以及對現實生活的表達上。《讓子彈飛》(2010年)中洋溢著導演姜文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和抑制不住的激情,受到了觀眾的歡迎,其影片內容上的諷刺性也只有中國觀眾才能領略其中個味。同時我們在影片中看到了導演對電影傳統和經典尤其是西方電影的兼收并蓄,影片干凈利落、凌厲的剪輯風格、動與靜的對比、懸疑氣氛的營造,都能清晰地看出西方電影對姜文的影響。比如開場的劫車場面,分明是約翰·福特西部片高潮的翻版;再如影片高密度的打岔式的對話,又和昆汀·塔倫蒂諾有趣地相似;黃四郎派人冒充麻匪強奸民女、張牧之審問手下弟兄一場,似乎又是《落水狗》的再現。
在中國電影中,馮小剛的電影將本土的文化資源與類型片的商業策略結合,創造了一種具有中國本土化的商業電影模式,一直成為國產影片的票房中堅。當代中國電影如果能夠創造性地利用中國的傳統文化資源,包括題材的資源和價值觀、審美觀的資源,就可以開創國際化的電影市場。新十年電影對中國現實的人文關注尤為可貴,這些電影關注普通大眾人物,對當代現實做最真實的反映,如路學長《卡拉是條狗》、安戰軍《看車人的七月》和《美麗的家》、王小帥《二弟》,電視劇《鄉村愛情》、《蝸居》、《家,N次方》等。本土化、產業化的發展實踐及其需要,永遠是中國主流電影創作的出發點和目的地,是好萊塢電影不可能替代的中國電影的文化優勢。
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在數字化的推動下,在多元化的生存格局下,調整當代中國影視的生產機制及面對世界的敘事方式,闡釋新的精神內涵和價值指向,才能構筑適應當代文化發展和最接近人的本真狀態的當代價值坐標體系。
(本文為河北省教育廳2011年度科研項目:90年代以后中國影視傳媒的文化轉向及對新世紀高校影視教育的思考,項目編號:SZ2011311)
參考文獻:
[1]張楊.好電影就具有商業性[J].電影藝術,2000(2).
[2]楊曉林.回歸主流與游戲狂歡:中國新生代電影的轉型[J].理論與創作,2009(5).
[3]饒曙光.國際化、本土化與主流電影發展[J].文藝報,2010(5).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