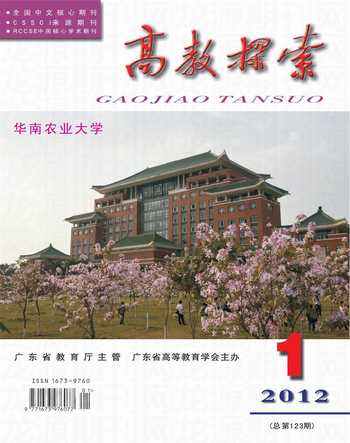尋求合法性:我國大學趨同化機制解析
李斌琴
摘 要:我國的“985”、“211”工程重點大學政策在引領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促進高等教育質量提高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對大學趨同化起到了導向作用。組織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的合法性機制可以對此作出一個合理解釋。尋求合法性是大學趨同化的動力機制。強意義上的合法性機制往往通過排名、等級定位影響大學的行為,弱意義上的合法性機制通過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方式來影響大學的行為。而這其中,合法性機制的強迫機制、模仿機制、規范機制共同對大學的趨同化起導向作用,在現實當中具體表現為:重點大學政策所帶來的“媳婦”(高校)對“婆婆”(政府)依賴與順從的馬太效應、高校爭當“一流”、爭變“研究型”的盲目求大求全、一般院校招生被“忽視”、畢業生就業受“歧視”的尷尬。
關鍵詞:合法性機制;趨同化;重點大學政策;新制度主義
一、問題的提出
上世紀90年代,知識經濟在世界范圍內興起,為提高自身國家競爭能力,各國對增強科技創新能力、提高科研人才水平格外重視。為此,許多國家推出了以趕超一流大學為目標的重點大學政策,以培養高、精、尖創新人才。在此背景下,我國也先后推出了以“創建一流大學”為目標的“211工程”、“985工程”重點大學政策。其中,“211工程”的目標定位于“使大多數學校達到國內領先水平”,“985工程”則定位于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在推出“211工程”、“985工程”后不久,1999年我國開始拉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序幕,使我國的高等教育得到了迅速發展,各級各類高等學校大增。根據教育部2010年12月30日公布的數據,我國現有普通高等學校2305所,成人高等學校384所,其他高等教育機構812所。其中,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090所(含322所獨立學院),專科院校1215所(高職占1071所)。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進程中,“211”、“985”工程重點大學政策在引領我國高等教育發展、推動高等教育質量提高,促進“211”、“985”院校的學科建設取得顯著成效、師資隊伍結構優化、人才培養質量與科研裝備水平及科研能力提高、辦學條件改善的同時,也在無形中引導全國各類高校紛紛向“211”、“985”院校看齊,即不論是高職院校,地方院校,還是單科性院校,千軍萬馬都在“專升本—拿碩士點—拿博士點—競爭‘211—競爭‘985—最終成為‘清華、‘北大式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這一條獨木橋上行走,出現“千校一面”的趨同現象。
二、尋求合法性:大學趨同化的緣起
為什么當下我國的大學會不約而同、“集體”爭相向“211”、“985”院校看齊?對于此類“組織的趨同性問題”,組織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理論的合法性機制(legitimacy)可以提供一種解釋。
什么是合法性機制?周雪光教授作出如下解釋:合法性機制是指,當社會的法律制度、社會規范、文化觀念或某種特定的組織形式成為“廣為接受”(for-granted)的社會事實之后,就成為規范人的行為的觀念力量,能夠誘使或迫使組織采納與這種共享觀念相符的組織結構和制度。[1]簡而言之,合法性機制就是組織為了在特定的制度環境中生存和發展,必須滿足社會共享觀念的要求,做符合社會期待的事情。它一方面約束組織的行為,另一方面又可以幫助組織提高社會地位,得到社會承認,從而促進組織的資源交往,提高組織的生存能力。
合法性機制如何影響大學的行為?組織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理論認為,合法性機制對組織的作用存在于兩個層次:強意義上的合法性機制及弱意義上的合法性機制。[2]強意義上的合法性機制是指社會的共享觀念具有強大的約束力,導致組織無法自主選擇其結構與行為,不得不采用外界環境認可的合法性機制。道格拉斯(MaryDouglas,1986)認為它通過賦予人們某種身份,并將其自然分類,使人們習慣于按身份去思維和行事;塑造了社會群體的記憶和遺忘,引導人們的思維和行動;塑造了對事物進行分類的標準,影響人們的思維和行為等。通過這三種“自然化”的機制,塑造人們的思維方式。例如,人們在心里會自然而然地對大學劃分三六九等,排在前面的重點大學是“好大學”,排在后面的就是“二流”、“三流”大學、“不好”的大學。在這種情況下,合法性機制是通過對大學的排名、等級定位來影響大學的行為。然而,并非所有的共享觀念都能塑造人的思維方式,只有那些已經被人們神圣化了、自然化了的基本理念,才會被人們認為是“天經地義”的道理而毋庸置疑地加以接受。相對于強意義上的合法機制而言,弱意義上的合法機制是通過一定的獎懲激勵機制來影響組織的行為或選擇,而非一種自然而然的思維邏輯。新制度主義學派重要創始人邁耶(Meyer)和羅恩(Rowan)認為雖然強意義上的共享觀念確實是存在的,但將其用于研究組織的趨同性問題,往往只能停留在思辨和定性的層面上。因此,邁耶和羅恩之后,新制度主義學派學者開始在弱意義上的合法性機制的框架內研究組織趨同性問題,認為,大多數的共享觀念并未達到塑造人的思維方式、影響人們行為的程度,人們的行為之所以仍受這些共享觀念的影響,并非失去了選擇的能力,而是出于想要獲取資源的利益驅動。也就是說,合法性機制是通過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方式來影響大學的行為。
那么,合法性機制又是如何引導大學趨同化的呢?對此,迪瑪奇奧和鮑威爾(Dimaggio & Powell,1983)認為有三種機制。其一是強迫(coercive)的機制。在一個組織領域中,當大家都把某種組織形式、規章制度或某種做法視為理所當然時,將迫使同領域的組織依此仿效,否則,將受到大家的歧視或懲罰。其二是模仿(mimetic)的機制,即各個組織模仿同領域成功者的形式和做法,尤其是組織面臨的環境是模糊、不確定之時。其三是規范(normative)機制。即社會規范的長期積累,在某領域形成某種類似于強意義上的共享觀念和共享的思維方式,進而導致組織趨同。
三、合法性機制對大學趨同化的影響
(一)“媳婦”對“婆婆”依賴與順從——政府重點大學政策的馬太效應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建立了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一切社會生活都是在嚴密計劃安排之下進行的。高等教育自然也不例外,被納入了政府集權管理的框架之內。大到對高等教育的立法、規劃、評價,細至對高校的辦學目標、培養計劃、機構設置、人事安排、專業設置、招生就業,政府均對其通過各種制度予以嚴格規定。政府儼然成為掌控一切的“婆婆”,高校則成為順從的“媳婦”。于是,“媳婦”的發展只能完全仰仗“婆婆”配置的資源,并服從其安排、成為其附庸。久而久之,這種依賴便形成了慣性,“媳婦”也習慣了“等、靠、要”的思想,失去了自謀發展的動力,并極力地迎合“婆婆”,以獲得其認可,得到一定的“身份與地位”。因為,不同的“身份與地位”,獲取資源和發展空間的差異較大。就當下而言,這種“身份與地位”就是看是否能進入“211”、“985”院校行列。一旦進入,則意味著進入了不同于“一般”院校的等級,即所謂的“重點大學”的行列,進而將獲得“211”、“985”院校所能享受的資金、人才、招生等各種政策優惠。
“211”、“985”工程是為了應對知識經濟的到來、培養創新科技人才、適應國際競爭而提出的,是政府“科教興國”的戰略意志。入選“211”、“985”工程重點建設的高校,重要標準是學術水平高、學科實力強。事實上,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就已實行“重點大學”政策,一批綜合性研究型大學,如“北大”、“清華”、“南大”等依靠政府的傾斜政策,學術水平、學科的綜合實力的發展已遙遙領先于“一般”大學。也正是這些得天獨厚的優勢使他們成為“211”、“985”工程重點建設高校的首選,政府予以了“超國民”待遇,額外投入巨額資金。如,在“985”工程一期項目的“2+7”格局中,定位于沖擊世界一流大學的北大和清華,三年時間內從教育部各獲得18億元的投入;其余最初定位“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學”的7所高校,中國科技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也從教育部和地方政府或者中央部委獲得三年10億元左右的投入。在長期辦學經費不足、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其他經費渠道很不穩定的情況下,政府大幅度的經費支持對高校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是決定性的。但是,這種政府政策偏好引發的高等教育資源的單向流動,也導致了諸多“一般”高校可能被邊緣化的傾向,促使它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存在的空間和合法性到底在哪里,否則,將有可能游離于中心體制之外,辦學“經費短缺”也將可能一直伴隨他們。最終,“211”、“985”工程重點大學政策引發了馬太效應,“一般”高校為它們合法地生存于高等教育系統選擇了一條道路——向“211”、“985”大學看齊——無論距離它們有多遠。這便是強迫(coercive)性機制所起的作用。
(二)爭當“一流”、爭變“研究型”——學習“211”、“985”院校的成功榜樣
組織社會學新制度主義理論認為,當組織的目標模糊或環境的影響不確定之時,組織會非常自然地模仿其他組織。因為,此時組織不知道采取何種方案最佳,而模仿成功組織的行為和做法則可降低環境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大學組織本身就是一個目標模糊的組織。正如伯頓·克拉克所言:“高等教育的任務兼具知識密集型與廣博型,因此,大學或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之目標難以說明……學術和教育是為了自身的理由還是為了國家的利益? 大學應該培養統治人才還是教育普通百姓?是應該滿足學生的需要還是人力規劃的需求,或兩者都不是?”[3]其次,大學組織的外部環境也是不確定的,包括經濟發展、政府政策、生源和就業市場等外部因素,對于大學而言均是無法預測到其所帶來的影響結果。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但規模的迅速擴張也使大學辦學的目標定位暫時陷入了模糊的境地。同時,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社會變遷也使大學辦學的外部環境充滿了變數。于是,為降低由此帶來的風險,“一般”院校紛紛模仿“已獲得成功”的“211”、“985”院校的辦學模式,即追求“高、大、全”的辦學模式。通過對各高校主頁的“學校概況”一欄檢索可發現,很多學校在介紹時自稱是綜合型、研究型的大學,或者說要辦成綜合型、學術型的一流大學,要成為全國知名、世界有一定影響的高等學校。不僅老牌大學這么介紹,新辦大學也這么介紹,甚至剛剛批準成立高職的學校也宣稱要辦成亞洲或者東亞有影響的大學。這種爭當“一流”、爭變“研究型”的辦學模式帶來兩個后果。
一是各院校紛紛拓寬學科門類,向綜合化演進,進而導致各院校專業設置趨同。據統計,2009年,英語、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國際經濟與貿易、法學、電子信息工程、工商管理、會計學等專業在1079所本科院校中的布點率分別為86.65%、82.02%、65.80%、56.90%、55.79%、52.55%、49.95%,高度趨同。[4]
二是爭相發展研究生教育,特別是博士研究生教育。于是申碩、申博也就成為一些院校發展戰略中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已有碩士研究生教育的院校,更是使盡渾身解數,不惜巨資申請博士點。如,湖南某高校就曾經提出了“只要能申請到博士點,不惜財力”的口號。[5]在其看來,一旦申博成功,他們距離“一流”、“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也就是咫尺之遙。“已經取得博士點的學校的今天是我們學校的明天,它們是我們學習的榜樣。”[6]故,申博成功全校歡慶,失敗則舉校齊哀。如,2009年3月某師范大學就因“十年申博路,一朝夢成空”,出現了教授停課2天風波。[7]幾乎同時,某政法大學也因申博失利,“失落的情緒迅速在校園蔓延”,出于對評審程序公平性的質疑,該校向省政府遞交了《行政復議申請書》,請求對省學位委員會確定的第十一次博士學位授權立項建設單位進行重新評審。原因相同:“如果申博失利,XX大學將淪為一所三流學校”。
各院校爭向“211”、“985”院校學習,爭當“一流”、爭變“研究型”正是模仿機制起的作用。
(三)招生被“忽視”、畢業生就業受“歧視”——必須正視的尷尬
“我國高等教育系統是一個等級嚴格的金字塔式的系統,自下而上分別是民辦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普通地方專科學校、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地方重點高校、百余所‘211高校、三十余所‘985大學、8所所謂‘重中之重的‘985大學,最后是位于塔尖的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8]不僅政府根據這個金字塔體系進行教育規劃,配置資源,社會,如家長、考生、用人單位也以此為標準自上而下考量大學的“優劣”。在他們眼中,“211”、“985”院校是高等學校體系中的一個特殊層次和榮譽,是“一流”、“高水平”的大學。學生進入這類大學學習,不僅是家長培養子女獲得階段性成功的標志,同時也意味著將來可能比進入“一般”院校的學生有更好的出路。用人單位也依此認為“211”、“985”院校的畢業生素質比“一般”院校的學生高。不僅如此,“211”、“985”院校自身也在不同程度地顯示出這種優越感。在各“211”、“985”院校主頁的“學校簡介”均開宗明義點明本校“是‘985工程、‘211工程建設高校”,即為此優越感的表現之一。反觀一些“一般”院校則往往被貼上了“二流大學”、“野雞大學”的標簽,這在招生和就業兩個方面表現尤為明顯。
首先是招生被“忽視”。當下,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的推進,我國的高校錄取率逐年上升,民眾開始關注接受高等教育的質量,學生的高等教育需求正在從過去被動擇校向積極主動選擇學校轉變,高考的競爭也從能否上大學轉變為能否上“211”、“985”大學的競爭。作為付費上學的考生和家長,也以更挑剔的眼光審視各個學校,使得各高校為爭奪優質生源而展開激烈競爭。在同一競爭平臺內,“211”、“985”院校憑借業已確立的社會聲譽,自然成為考生、家長們的首選,而“一般”院校則往往被忽視或只是最后“無奈”的選擇。這種業已形成的“社會觀念”也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一般”院校出現生源危機,這已在處于高等教育金字塔底端的一些民辦高職院校開始顯現。
其次是就業受“歧視”。在高校畢業生就業形勢嚴峻的背景下,用人單位在選拔高校畢業生時設置了越來越多的限制門檻,甚至出現院校歧視現象,以至畢業學校是否為“重點”、是否有碩士博士點往往能決定畢業生就業的成敗。國內一知名企業甚至連招聘前臺服務員都要求是“211”院校畢業生。這也使得“一般”院校的畢業生就業率明顯低于“重點”院校。
正是社會上長期以來形成的“‘211、‘985院校才是‘一流的大學;‘211、‘985院校畢業生才是‘一流畢業生”的共享觀念使“一般”院校的招生被“忽視”、畢業生就業受“歧視”,迫使“一般”院校努力想擺脫“二流”的尷尬,向高等教育體系的金字塔頂端攀登,以尋求生存與發展的“合法性機制”。這就是社會規范機制導致的趨同。
四、余論
綜上所述,可以說我國大學趨同化的現象在某種程度上是制度安排的結果,并非完全是高校的責任。這其中,政府重點大學政策的暗示效應、高校自身盲目的求大求全、社會輿論價值取向的推波助瀾,均在不同程度對高校的趨同化起了導向作用。因此,對我國大學趨同化現象應客觀看待。如硬幣有其正反兩面一樣,院校趨同化現象亦有其利弊。一方面,為在競爭中獲勝,各院校必然會調動各方積極因素,挖潛增效,促進優勝劣汰,使部分院校和學科、專業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得到超常規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趨同化也可能導致院校無特色、人才無特色、培養質量下降;同類專業人才過剩、畢業生就業困難;高校無序競爭、教育資源浪費等等,而這些恰恰是目前我國要實現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邁進必須正視的重要問題。因此,面對大學趨同化這一現象,政府在制定重點大學政策時,是否要考慮如何構建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生態系統、促進高校多元化發展?是不是只有普通院校才有“985”、“211”工程,高職院校也應有自己的“985”、“211”工程?是不是要建立多樣化的人才觀和質量觀,對不同階段(主要指精英教育階段和大眾化階段)、不同類型(主要指普通高校和高職院校)、不同層次(主要指研究型大學、一般本科院校和專科院校)的院校采用不同的評價標準,引領院校辦出特色?這些都是今后我國發展高等教育需進一步探究的話題。
參考文獻:
[1][2]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57,61.
[3]伯頓·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統——學術組織的跨國研究[M].王承緒等譯.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4.22.
[4]教育部高教司編.中國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設置大全(2009)[M].北京: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60-700.
[5]高教時評:院校博士點申辦 載不動太多利益[EB/OL].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3/31/con tent
_2603266.htm.2009-03-31.
[6]我校申博工作面臨的形勢及其對策探析[EB/OL]. http://public.hbut.edu.cn/17/zsjhnews.asp?id=242.2007-12-28.
[7]陳江.“成”“敗”博士點[EB/OL].http://www.infzm.com/content/26113.
[8]趙炬明.精英主義與單位制度——對中國大學組織與管理的案例研究[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6(1):174-191.
(責任編輯 劉第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