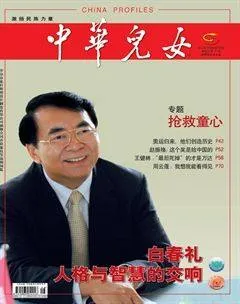從有待到無待,《逍遙游》中的自由與超脫
《莊子》“逍遙游”以宏大的筆觸極贊鯤鵬之偉岸,以不屑的口吻鞭笞叢林小鳥之短視: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斥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大致譯文如下:北海有一種魚,叫做鯤。鯤十分巨大,不知道有幾千里。鯤化而為鳥,叫做鵬。鵬也同樣是一個龐然大物,不知道有幾千里那么大。它振翅而飛,翅膀有如遮天蔽日的云彩。這種鳥,在海運來臨的時候將飛向南海。南海,也就是天池。當大鵬鳥在往南冥飛翔的時候,擊打起三千里的浪花,乘風而上九萬里,這一飛就是六個月。然而,蟬與斑鳩卻嘲笑說:“我們快速飛起,沖上榆樹和檀樹,但有時達不到目的地,就投落到地面上,何必要飛九萬里那么高呢·”麻雀也感到不理解,帶著嘲笑的口吻說:“它究竟要到哪里去呢·我使出吃奶的勁往上飛,也不過飛幾十丈那么高就得回來,在蓬蒿之間翱翔,已經是飛翔的最高境界了。而它,究竟要到哪里去呢·”
從總體上說,在莊子看來,無論是大鵬還是麻雀或蟬,都還沒有達到真正自由的境界,原因在于它們都仍然有所依賴。麻雀、蟬就不用說了,它們局限于叢林之中的狹小空間之中,根本談不上自由;就是大鵬鳥也沒有達到獨立不依的程度,它之所以能飛那么高,是借助于旋風的力量。因此這兩者都是需要超越的,只有達到了無所依賴的境界,才能夠具有真正的自由。
不過,在這兩者當中,莊子對大鵬鳥顯然是欣賞有加,而對于蟬、斑鳩和麻雀的描述則充滿了戲謔、嘲諷的語氣,甚至直截了當地說“之二蟲又何知!”
就這兩者比較而言,我們對于大鵬鳥也會很自然地肅然起敬,因為它視野開闊,氣魄宏大,有英雄氣概;而麻雀與蟬,在大鵬鳥面前如同小丑一般可笑,它們鼠目寸光,即使盡力地翻飛跳躍,最高也不過數尺而已,有什么資格嘲笑偉大的鵬呢·我們通常把這樣的人稱之為“井底之蛙”。因此,在這兩者中,我們當然要肯定鵬,因為它的見識和胸懷是井底之蛙所無法比擬的。
然而,這只是從比較、相對的角度得出的結論,如果我們從終極的角度來看,或者說從莊子所說的道的角度來看,則大鵬鳥與麻雀并沒有實質性的區別,甚至于大鵬鳥的處境更加可悲!
既然道(或者宇宙)是無限的,無始無終的,那么大鵬鳥無論飛多么高、多么遠和多長時間,都不可能接近無限,無限是不可接近的,可接近的則不可能是無限。大鵬飛了九萬里那么高,已經夠高的了,但與無限相比,仍不過是蓬蒿之間罷了。因此,大鵬對于麻雀的嘲笑實在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
在莊子看來,知識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如果按照這個觀點來衡量,那么大鵬實際上是很不幸的,它的不幸正在于它的有知,在于它力量的強大。它知道在它面前永遠有一個無窮的宇宙,而這個宇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這個無窮的宇宙面前,它存在與不存在都是一樣的,不管存在多長時間,都不過是一剎那而已。從這個角度看來,它對于無限的意識幾乎就是一個悲劇。
相反,麻雀與蟬倒是更加幸福,它們的幸福正在于它們的無知。它們不知道在叢林之外還有一個十分巨大的空間,更不知道還有一個無限廣袤的宇宙,它們上下翻飛于狹小的空間之中,并不知道它們自己的“小”,這種“小”只是在大鵬鳥的眼中才存在著。所以它們因知足而快樂,沒有面對無限時的煩惱。
因此可以說,大鵬與小鳥各有各的逍遙,又各有各的不幸。大鵬不知道小鳥何以幸福,而小鳥也不知道大鵬的煩惱。
從這個角度來看,井底之蛙也同樣是幸福的。它不知道在井之外有一個無限的宇宙,相反,在它眼里這個井就是全部的宇宙了。對于這個宇宙,它了如指掌,沒有任何陌生感,也沒有任何的困惑,所以它完全能夠把握這個宇宙中的一切,因而它生活在這個宇宙中是安詳的,這種安詳來自于它對這個“全部”宇宙的了解。
那嘲笑井底之蛙的人類,卻是不幸的。他之不幸在于他有意識,在于他比青蛙看得遠。他面對無窮卻不能游于無窮,他渴望把握世界和人生卻無法把握,在他面前永遠存在著陌生的領域,這使他永遠生活于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生活在這樣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總是充滿了恐懼和煩惱,從而就不可能幸福和自由。面對無窮的宇宙,人類只能感到自己的孤獨、無奈和渺小,甚至是恐懼。巴斯卡爾就曾經描述過這種感受:全宇宙的沉默使我恐懼。
只有無知才沒有恐懼,才能夠幸福和自由,但人不可能無知,因為人不可能沒有意識。從這個角度說,人實在是一種悲劇性的存在。人類的悲劇不在于生活的艱難,也不在于他們的自相殘殺,而在于這種與生俱來、無法擺脫的無限意識——意識到了無限,卻又無法無限地延長自己的存在。用哲學的語言來說,這叫本體論的恐懼。
人類常常以嘲笑的口吻談論那些微小的生命,可是,從廣闊的宇宙視野來看,人類與那些生命并沒有實質的區別。我們知道,還有比井底之蛙更無知的生命,這就是那些十分微小的生物。螞蟻是一種匍匐在大地上的生物,它們的天空大概只有一厘米那么高,那以上的天空對它們來說是不存在的。還有更小的生命。有一種花,叫掛葉菊,葉子差不多有巴掌那么大。在它的葉子上生活著一種針眼大的動物,俗稱“密蟲子”。它們一生都生活在一個葉子上,絕大部分時間是靜止的,即使爬行起來,也極端緩慢和短暫。一個葉子大概就是它們的全世界了,它們永遠不知道是生活在一個小小的葉子上。它們由于無知而很少欲望,很少欲望也就很少痛苦。
俯視著這小小的生命,心中不免油然生出一種感嘆:在這個無邊無際、無始無終的宇宙中,人類不也是生活在這樣一片小小的葉子上嗎·
在無限面前,無論是鯤鵬還是人類,都是渺小的,渺小得如同一粒灰塵;在時間面前,一切都是過眼的云煙,而人也不過是一個匆匆過客而已。即使你擁有天下又怎樣·你所擁有的一切最終都會離你而去。
責任編輯 王海珍
作者簡介
嚴春友: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論著有:《宇宙全息統一論》《精神之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