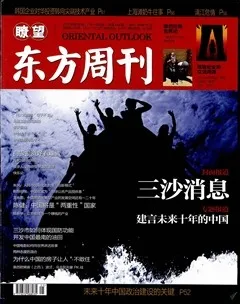兩種態度的混合
從過去落后發展到經濟水平越來越接近西方,會有從自卑感到平常心的變化。但是,如果任由簡單的民族主義情緒蔓延,就可能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從盲目的自卑感到盲目的優越感
瑪萊雅1997年首次到中國旅游,3年后,她重新回到東方,并花了9個月學習漢語。2001年5月,她成為駐北京的荷蘭記者。目前,她代表《忠誠報》和RIL荷蘭國際新聞電視臺。
那一年,被許多海內外的中國人當成了“中國年”:北京申辦奧運會成功、中國男子足球隊進入世界杯決賽階段、加入WTO歷經15年終成正果、上海合作組織成立。
即便如此,“如果10年前我跟老板說,中國會救歐洲的銀行、會救歐洲的經濟,他不會相信。”瑪萊雅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瑪萊雅來到中國這10年,中國在全世界變得越來越重要。與此同時,“中國人對西方的態度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自信的中國人讓外國人更自在”
瑪萊雅喜歡“下基層”,尤其喜歡去中國的鄉村。“中國正在城市化。但是中國的許多文化思想都跟農村有關系。”她的話聽起來頗有中國農村問題專家的味道,“城市化很好,可是如果能夠讓中國的農村都富起來,中國的許多問題就能解決了。”
她至今記得2002年到河南駐馬店采訪的經歷。“當時農村人不敢跟我說話,不是怕我問政治問題,而是怕我看不起他們。他們說,‘我們的水不好喝,飯不好吃,人太土。意思好像是說‘你們別來了’—樣。”
這樣的經歷,時常讓瑪萊雅覺得不大好意思。“我去一個老百姓家里采訪,他們會把采訪資料準備得很好,家里面也收拾得干干凈凈,還準備水果茶點。我走的時候,他們不直接跟我講,而是跟工作人員說,自己是不是沒做好,家里太小了。有時候我都不好意思麻煩他們。”
現在這樣的情況在減少。在瑪萊雅看來,這十年間“中國人更加自信了”。其中的原因顯而易見:中國令人驚奇的經濟發展速度,給了中國人自信的底氣。就在她來中國工作的3年后,上海港超越她家鄉的鹿特丹港,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港口。
即便在農村,物質和信息上的鴻溝也在變小。隨之而來的是,文化和價值觀念的鴻溝也在縮小。過去,最讓她難以忍受的是一些中國人對于像她的國家一樣的國家的某些說法。“不少中國人并不了解我們的文化,覺得我們都異常隨便,也不愛自己的父母。而這些印象不過都是來自一些美國的電影。”
現在,這樣讓瑪萊雅討厭的問題越來越少了。相反,許多中國人變得日益個性化。
瑪萊雅還記得,2001年她剛開始在中國的職業記者生涯時和一位出租車司機的聊天。當時司機問她,你有孩子嗎?有家庭嗎?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司機同情地說,你好可憐啊,你應該有個家庭。
“現在如果是一樣的對話,得到的回答就會不—樣。不管是什么人,他們會說,哎呀,你好自由好舒服啊,沒那么多事,有時間享受自己的愛好,過自己的生活。”
除了海南省之外,金玉米跑遍了中國的每一個省份。他對中國的縣城、鄉村相當熟悉。最近兩年,幾乎每個周末他都會開車到北京周邊登山。
他認為,中國依然是個會“穿越”的國家——到了一些落后的地方,感覺就像是換了個時代。而那里的人,對外國人尤其是西方白人的仰視和好奇依然存在。
“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的地位不同了”
在仰視和好奇還未完全消失之前,一種新的態度似乎正在中國一部分人中生長。
“中國一些發了財的商人和一些官員還是有些傲慢的。雖然是少數的。”金玉米說。
李成賢記得,幾年前美國人麥健陸(James McGregor)在一次公開演講中講到一個現象。隨著中國富人中打高爾夫的人增多,他打高爾夫便常會聽到一些中國人之間的聊天。有的中國人見到外國人時會說,中國不需要老外投資了,中國已經很強大了。
麥健陸有一長串顯示他豐富中國經驗的頭銜:曾經擔任中國美國商會會長,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及亞洲協會國際理事會,就經濟及貿易政策為中美兩國政府充當顧問,《華爾街日報》中國分社負責人,道瓊斯公司中國區首席代表。
作為一名普通外教,法國人克里斯多夫對中國的觀察范圍顯然要小—些。而在他的視野之內,也有著類似的感受。
克里斯多夫的一個朋友在中國待了30年,可是在和一些中國人聊天時,依然被認為“不了解中國人”。
不過,克里斯多夫認為當下有些中國人絕不只是對外國人傲慢,“他們對同胞同樣傲慢”。
他觀察到,在大街上行走的中國人中,有些人時常不知道避讓迎面而來的行人。一旦發生摩擦和沖撞,如果你試圖討要說法,對方多會露出鄙夷和嗤之以鼻的神情。
一些舉止言談看似深深傷害了他的感情,他多次惟妙惟肖地模仿那些人的表情和動作:雙目微微向下斜視,再目光朝上,單邊眉頭皺起,伴隨嘴角輕蔑地發出一聲“哧”。
他也曾試圖討要說法,但不止一次地遇到挑釁甚至肢體攻擊。所以,他并不認為外國人在中國享受超國民待遇之說是準確的。
克里斯多夫回憶,1998年他初次來中國游玩的時候,社會氛圍比較輕松。如今,經濟發展了,似乎一些人卻很容易動怒了。由此,這個在中國生活了8年的法國人,面對一些中國人有點不知所措。
相比克里斯多夫的感受,金玉米好像想得更多。“中國正變得自信。因此,一些中國人表現出的某種傲慢,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認為,一些人的這種態度顯然和中國走向強盛有關,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以及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經濟的強勢表現,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的地位不同了。
中國人變傲慢了嗎
這種新生長出來的態度,與原有的態度混合,以互相矛盾的姿態并存。
就在宣武門猥褻事件之前大約一周,互聯網上還有一位外國人引起了網民廣泛的道德抒情。在那條被瘋狂轉發的微博中,一名外國小伙子坐在麥當勞門口,與一名乞丐分享自己的薯條。
而在2011年10月,烏拉圭人瑪利亞·費爾南達跳進西湖救起了一名落水的中國女子,當時激起了許多網民對國籍與道德的追問。
“宣武門事件和這兩件事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這顯示了中國人面對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的矛盾狀態。”金玉米說。他認為,韓國與中國有著相似的近代史經歷,而韓國的經濟起飛早于中國,因此韓國人也經歷過類似的心態變化:對比自己發達的國家,懷有一種羨憎之情,就是又羨慕又痛恨,又媚外又仇外;對一些不比自己發達的國家,則又表現出某種傲慢和無知。
李成賢說,從過去落后發展到經濟水平越來越接近西方,會有從自卑感到平常心的變化。但是,如果任由簡單的民族主義情緒蔓延,就可能會從—個極端走向另—個極端,即從盲目的自卑感到盲目的優越感。
麥健陸在2005年出了一本名為《OneBillion Customers》(十億消費者)的書。這本書試圖以其過去在中國十幾年經驗,為和中國做生意的外國商人提供建議。書中對中國社會人情世故和潛規則的觀察,令一些中國讀者擊節贊嘆。
在談到中國的談判環境時,書中寫道:無論是政府間或商業間,充滿著中國對其本身和對外國人的理解。曾經遭受的恥辱在中國人的記憶中依然清晰,但那種追求領先外國人的優越情結也揮之不去。所以,你會發現自己同時面對著中國人懷疑和自大的兩面。中國人期望得到不同的待遇。
除此之外,他還從另—個角度闡釋了一些中國人面對世界時的矛盾狀態:自信,理性,希望成為世界級的競爭者;同時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不安全感。年輕人的放松與假國際化
通過外國人的眼睛觀察中國自身,正成為中國人重新審視自己的一條重要途徑。
2011年,中國的各大暢銷書排行榜中有—本美國人寫的書——《尋路中國》。作者是《紐約客》駐中國記者,美國人彼得·海斯勒。書中講述了作者駕車漫游中國大陸的經歷。
海斯勒在書中花了不少篇幅,調侃中國司機對交通規則的“超越”。
“在開闊的道路上,似乎每個駕駛員都剛剛從胡同里解放出來——安然加速,展開競賽,而最驚悚之處,莫過于超越其他車輛。在山坡上,他們要超車,在彎道處,他們要超車;在隧道里,他們要超車。如果被別人超了車,他們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反超那輛車,就好像在比賽—樣。根據我的判斷,這是駕駛員考試題中唯一一道三個選項都正確的試題:超越其他車輛時,駕駛員應該:A)從左側超車。B)從右側超車。C)兩側均可,視情況而定。”
金玉米說,彼得·海斯勒的想法代表了相當多的外國人的想法。因為規則意識不同步,造成了克里斯多夫在中國道路行走上的緊張。盡管多數時候,這更像是說明了中國這個交通硬件發展最迅速的國家,在交通文明上還落后許多。
海斯勒著墨頗多的另—個話題是長城。
在還未提到海斯勒和《尋路中國》時,金玉米就主動說到:“中國過去是個搞長城的國家。”
“很多外國人覺得中國最主要的符號就是長城。這個符號也容易讓許多外國人用來解釋中國文化:中國人用一面很長的墻,試圖把自己從世界中隔離出來。中國歷史上曾確實如此,直到改革開放之后。”
盡管相比長城的歷史,改革開放的時間非常短,但是很多情況在發生巨大的變化。
“我剛來中國的時候,必須要住外交公寓,不然不能獲得記者證和機構證。現在這個限制已經放松了,我可以決定自己住哪兒。”瑪萊雅說。
“很明顯,相比20多年前,中國在很多方面已經和世界接軌了。比如外國人的簽證制度,其實已經非常系統了。”金玉米說。
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中國年輕人,也讓他們感受到中國的世界觀和國際觀正在改變。相比父輩們,中國的80后、90后正在采用不同的方式與世界交流。“年輕人顯然更放松,對待外國人也更平等。”
不過情況也并非完全樂觀。
由于公司項目的需要,金玉米最近兩年和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有很多交流。他發現,這些80后、90后留學生似乎還沒有展現出對那個世界的足夠適應能力。
“他們不參加澳洲人的社交活動,只跟自己的朋友交往,他們本來有比父母多得多的機會接觸外面的世界。他們看似很國際化,可這是假國際化。這種情況并不是佳況,因為你覺得你懂,但實際上你可能還不懂。”金玉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