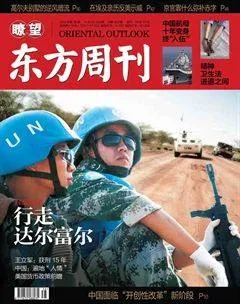黃裳先生和他的散文

一代散文大家黃裳先生離去,令人殊覺悲痛。這是不是意味著,一種已滲入中國文化血脈八十余年的文學傳統,一種優美的文體和那膾炙人口的文章風格,將永遠消逝·
從他去世當晚至今,我接到好多報刊的采訪電話。所有問題問完后,最末的也最重頭的問題,必然是:“黃裳先生的散文得到了那么多名家的肯定,您能不能詳細說一說,他的散文好在哪里·”
1997年春,我替黃裳先生編六卷本《黃裳文集》,翌年由上海書店出版。那時我把他的大部分文章看了一遍,有些則此前就已細讀并深愛。我反復想到的,也是這樣一個問題:都能感到這些文章好,但誰能說出它們到底好在哪·因年少氣盛,曾下了決心:此刻,恐怕沒幾個人比我讀得再全再細了,那就趁熱打鐵,好好回答這個問題吧!
但后來是,決心下過,想也想過,卻沒有做那種扎硬寨打硬仗的研究,也就沒能寫出像樣的有分量的論文,只在每卷文集的前面各寫了一段數百字的“弁言”,另外還寫過一篇題為《黃裳先生》的短文,表述了自己粗略的想法。
現在看,當時主要突出了兩點,一是在文體上,強調他的各類文章都屬“廣義的雜文”;二是在風格上,強調它們有濃濃的“書卷氣”。
如在《黃裳文集》卷一“錦帆卷”前,我寫道:“本卷所收多為作者記游作品,但它們又不同于一般的游記。在內容和寫法上,它們和作者談書、懷人、議世的散文隨筆并無太大的不同。作者常說散文與雜文不應有明顯的界限,他還喜歡將自己的作品統稱為‘廣義的雜文’,看來確有他的道理在。”
在卷二“劇論卷”前,則說:“本卷文章都是談戲的,但作者不愿稱之為劇評,也不承認自己是‘劇評家’,而寧可稱它們為‘論劇雜文’,說到底,還是他那‘廣義的雜文’的意思。不將這些文章作為評論,而作為具有評論味的散文隨筆來讀,確是能得到更多的樂趣的。”
卷三是“珠還卷”,收了好幾種本來意義上的雜文集,我在弁言中寫:“本卷中的許多作品似可歸入狹義的‘雜文’范疇,但作者仍保持著他一貫的風格。即使寫尖銳潑辣文章,依然不失厚重嫻雅,處處充滿獨特的書卷氣。”
第四卷“榆下卷”,收入的都是最具書卷氣的書話,我的喜愛之情在書前也溢于言表了:“本卷所收,多為‘書話’,這是作者最擅長的文體……當年,《榆下說書》初上市,讀書界為之雀躍的情景,至今猶令人感慨。”——從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一點當年對他的散文的欣賞、體驗的痕跡。
此后十多年里,不斷讀到黃裳先生的新作,也一直在思考他的藝術風格的特征。我寫那本散文史論性質的《今文淵源》時,黃裳所代表的風格也是著重考慮的一個方面。所以,今天再來敘說這一話題,思路可能會更清晰一些。
我發現,真要說清黃裳散文的魅力,似須從文體和風格兩個方面入手。文體,也就是“廣義的雜文”,這可說是淵源有自,是有傳統和師承的;風格,則是他個人的。而“書卷氣”,始終貫穿于他的文體和風格之中。
用大專家的底子,寫文學家的美文
黃裳的文體,即那種打破了各類體裁的局限,使各種文類都充滿作者的真性情和濃郁的書卷氣的寫法,是“五四”以后中國新文學的一大創造,這也就是周作人、俞平伯等開創的文人散文、學者散文的傳統。周作人將這方面的論說統稱之為“雜文學”,亦即各類文章之學,其實也就是“文章學”。這種打破文類邊界的努力,促使小品作家和論文作家都成為“文章家”,都要把文章寫好,使其可讀耐讀,而其中的關鍵,用周作人的話說,就是不僅要說得“理圓”,還須“有余情”。
那時的很多論文,現在讀,還是覺得好看,可讀性并不遜于文學作品,奧妙也就在此。
1923年9月2日,俞平伯在給周作人的信中說:
近日偶念及中國舊詩詞之特色至少有三點:
(1)impressive,(2)indirect,(3)inarticulate,推演出來自非長文不辦,然先生以為頗用得否·
這三個英語單詞都是借用,當然不可循其本義,但細按俞平伯一貫的文心,似可意譯為:(1)悠然心會(impressive),(2)朦朧蘊藉(indirect),(3)渾然一體(inarticulate)。這是中國舊詩詞特色,而俞平伯也使之變成了他的散文乃至論文的特色。
試看他的學術性專集《紅樓夢辨》《讀詩札記》《讀詞偶得》,乃至《唐宋詞選釋》,其風格大致如斯,與他小品散文中的議論說理部分并無二致,也因此,他的所有論著都可拿來當散文讀。雖然這些文章都是講邏輯的,表達也是精當的,但他更強調對研究對象的“心會”而不僅僅是邏輯推論,也更注意保持文章自身的“渾然一體”之美。
當然還有另一個特點,即這一派的文章都是寫給文化人看的,是含學術性的,不強調普及作用,不特別照顧讀者的不同程度,所以也就不像胡適那一派文章注重循循善誘和平白清淺。抗戰開始后,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新中國建立后,提倡“為工農兵服務”,普及成了為文的第一要義,文人的個性漸顯式微,這一派的文章也就看不到了。所以,“文革”過后,黃裳的文章在《讀書》雜志等處現身,《榆下說書》由三聯書店推出,一時成為人見人愛的珍稀品,這也就是這派散文的重見天日吧。
而在這一派的傳人中(施蟄存、張中行、王世襄、鄧云鄉、鐘叔河等均應在內),就文章本身說,黃裳無疑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在保持這一文體的純粹性上,黃裳也是無人可及的。他能那么“頑固”地寫這種充滿舊氣(但同時也頗有新意)的文章,昂然落筆,決不左顧右盼,誰也改變不了他的文體文風。這種為文的自信,亦即對自己所承襲的文學傳統的自信,想來也是很感人的。
至于黃裳的個人風格,應從四個方面來看,那就是:功底、見識、趣味、文筆。
先說功底。黃裳知識面很廣,文章深入到眾多領域,諸如文學史、戲曲史、版本目錄,書法繪畫、晚明史、京昆劇、魯迅研究、周作人研究、民國學人研究、紅樓夢研究……他每鉆一門,都是真讀,真鉆,能成為這一門中的專家,而且是一流專家。他能跟周汝昌討論《紅樓夢》,能跟錢鐘書討論古典文學,能跟姚雪垠辯論《圓圓曲》,能跟戲曲專家討論劇目。解放初期鄭振鐸掌管國家文物局時還曾請他到北京搞圖書版本,鄭振鐸本人就是一流版本目錄學家。他的《關于柳如是》在《讀書》發表后,眼界奇高的史學家朱維錚讀得拍案叫絕,我就親眼見到朱維錚在幾年后不忘向黃裳表示自己的欽佩之情。王元化是大學問家,也是文章大家,但看了黃裳的文章,連聲叫好,晚年和黃裳成了無話不談的文友。
正因為有這樣的功力打底,他才寫得出那手好散文。這是用大專家的底子,寫文學家的美文——黃裳散文的厚重、耐讀、不過時,最大的原因就在這里;這也是他的文章最主要的特色。
至于見識和趣味,其實二而一的東西,都與人的性格相關,見識是它的理性的表達,而趣味是它的感性的存在。黃裳先生的性格,那一目了然的特點,無非是兩條,即說話少、看書多。
黃裳不僅在人多的時候光聽不說,老朋友相對可幾小時不發一言,面對采訪也常常欲言又止終于還是不說;但要是談得投機,問得得法,他還是會忍不住說一通的,有時還會口出妙言,笑聲朗朗。他不說則已,一說,就一定有內容,是自己所思所想,寫出來往往就是一篇好文章。可能就因為他說得少,也就聽得多,讀得多,想得多。
每次去黃裳家,他總在看書,桌上,沙發上,茶幾上,都攤著看了一半的書。他的文章的書卷氣,跟他一生手不釋卷大有關系。如此讀書成癮,就把眼界看得越來越高,于是常聽他慨嘆:“沒有書看。”“最近沒什么好文章。”他時時向人打聽有什么有趣的好書好文,一旦看到一篇好東西也會急切地向人推薦,這時便口角含笑,眼中放光,一臉孩子氣。
人的趣味是一種極難言說的東西,它既有先天的因素,更有后天的積累和陶冶。在長期默默而深入的讀書、涉世、閱人及藝術體驗中,他形成了極高的趣味;以這樣的趣味記游、談戲、議世、論文,也就寫出了獨到的不俗的見解。寫作也有為工作而寫、為責任而寫、因有趣味而寫的不同,黃裳的性格從來是“依自不依他”的,他只肯因趣味而寫,遇到有趣的題目,他的文章倚馬可待,不然寧可一言不發。這就使他的散文更具個性和品位。
黃裳的文筆極具特色,充滿文人氣,雖是白話,卻有濃濃的古文韻味,厚重而有情;寫到關鍵處,輒鋒芒逼人,暢酣凌厲。他年輕時文字沉郁美艷,結實波俏;到晚年,爐火純青了,老辣中仍藏有一絲美艷,簡淡外形難掩其內在豐腴,于是,更耐讀了。
論戰時的“弱點”
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風格。正因黃裳散文具有如此魅力,它的弱點也就很難掩藏。越是優秀的文學作品越容易發現不足,《紅樓夢》與《戰爭與和平》是最好的例子。
我覺得,黃裳散文的弱點,在那些論戰性強,需要更充分地說理的地方,表現得較明顯;雖然這些文章往往叫好,有的讀者最喜歡的正他的這部分文章,他自己也往往以這些文章為得意之作。
黃裳那一代作家年輕時都喜歡魯迅的雜文,都愛學魯迅的罵人。魯迅在寫《“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前,馮乃超曾寫過一篇條分縷析的文章,魯迅說:“乃超還是老實。”便親揮大筆,遂成此文。魯迅這種不按常規說理,以一擊致敵死命的作文法,被后來許多雜文家奉為圭臬。黃裳本來就講究趣味,感到這種寫法其“酷”無比,對這種論戰中的機智佩服無以,所以有了機會就愛拿來用。
他從年輕時起(如1946年27歲時與吳祖光的論戰)一直到晚年,只要一投入論戰,就不愛按常規方式條分縷析,而總是從根子上入手,從對手最致命的地方突破,以圖一擊致敵死命。這種時候,他對“為文”的追求(其中有一種兒童般的逞能、“好玩”的心態),很容易取代對客觀性的追求。所以那次和吳祖光論戰后,柯靈批評他說“不是坦蕩蕩追求真理的態度”。
其實魯迅雜文的形象系統背后,仍有嚴密的邏輯系統作支撐,如名文《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一路說故事,一路的俏皮話,但稍稍一想就知道指的是什么,看得出理性的批判在暗中層層推進。后來不少雜文家在此就有缺漏,何滿子是最典型的,黃裳恰恰是喜歡何滿子雜文的。前文說過,俞平伯這一派的文體,強調“悠然心會”,不喜歡規規矩矩的推論,這也就留下了隱患,即稍不注意,就容易背離邏輯,讓趣味,讓自己的心境牽著走。黃裳晚年的一些論戰,雖以機智、狠辣讓人嘆服,讀文章時也覺暢酣,但終究經不起事后的推敲,在邏輯上顯得難以“理圓”,所以很難服人。
當然,這一派的散文并非不可有嚴密的邏輯,比如知堂的趣味不下于俞平伯,但理論上、邏輯上就要嚴密得多;同理,也是雜文大家的曾彥修與柯靈(他們也學魯迅),都很講究趣味,而邏輯也很嚴密。可見理性和邏輯還是可以為美文所吸收的,周作人當初論美文時,也是先強調“理圓”,然后才強調“有余情”的。黃裳散文如在理性與邏輯上更嚴密些(當然它們應隱于趣味文章背后,而不破壞文章之美),那是會更迷人也更服人的。
黃裳先生所代表的文體和文風不會隨他而去,我相信它們將長存于文壇;但也希望今后的散文家能在這樣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以使中國文章益增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