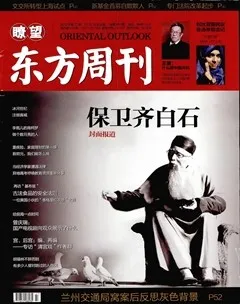再訪“基布茲”(上)
“基布茲”的成功奠定了現代以色列從無到有的基石,因為當初從流散狀態回到迦南的猶太人,就是靠著建立一個個“基布茲”才得以自食其力
2007年9月我訪問來滬的以色列國寶級作家阿摩司·奧茲,驚嘆于一位知識分子的名望可以同他的形象、氣質結合得如此完美。他的聲音聽起來發自某個深邃、邈遠的地方,他坐在那里,一個人就如同一片原野。還聽說,他也在以色列集體農莊——“基布茲”生活過。
我無法抵擋那種神奇的召喚,終于在一年半后回訪了他的國度。在阿弗拉以北四公里的地方,我走進了密茲拉“基布茲”。
夜色甫降,四野無人,基布茲的寧謐一下子把我襄得緊緊的,連靈魂都不放過。
奧茲待過的是一個名叫“胡爾達”的“基布茲”,不是這個密茲拉,不過,以色列的每個“基布茲”都有大同小異的風景和結構:一邊是花香鳥語的社區,一邊是繁茂的農田。中國人來到這里,當會產生一些復雜的感情,因為我們當初引以為豪的農村公社制度已經歸于歷史,而以色列人的集體農莊—希伯來語中稱為“基布茲”(Kibbutz)——卻存留至今。
每一戶人家的宅院都藏在花團錦簇之間,遍地都是長著各種花卉的花盆和瓦罐,有幾棵大樹的樹干上系著顏色鮮艷的絲巾,這是農莊里正受特殊養護待遇的樹木的身份證明。繞過幾棟樸素的平房,大片農田便齊整地在村邊攤開。偶爾能見到兩三個莊民、談話聲在清爽的空氣里消散得一干二凈,相遇對他們而言可能永遠波瀾不驚。
“基布茲”的成功奠定了現代以色列從無到有的基石,因為當初從流散狀態回到迦南的猶太人,就是靠著建立一個個“基布茲”才得以自食其力。對他們而言,那當然是民族團結勤勉的寫照。
在奧茲的小說體回憶錄《愛與黑暗的故事》里,這些素不相識的人并非那么容易就“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走到一起’。由于長年流散在各地,來自俄國、德國、法國、中亞、北非等地的猶太人各有其生活習慣,來自歐洲尤其是德奧等國的猶太人頗有優越感,一度看不上寄居東歐和中亞的同胞。不過幸運的是,在歷經2000年坎坷傳承仍生命不衰的文化機制的作用下,這些人總算是走到了一起。
“密茲拉”(Mizra)得名甚早,古地圖上就有,希伯來語里的意思是“播種”,讓人想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第一次世界大戰到上世紀20年代中期,第三次“阿利亞”(指大規模猶太移民潮)往巴勒斯坦輸送了數目巨大的猶太工人,密茲拉基布茲就是在這期間形成的,其成員多來自德國、奧地利和波蘭。在由七旬翁皮尼·希伯利開設的當地的小博物館里(他們多么敬惜自己的歷史!),還可以看見第一代移民帶來的德語書,以及每個基布茲博物館都能見到的農具、衣物、生活用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