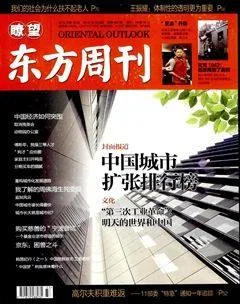中國經濟如何突圍
中國經濟突圍真正的危險,是面對嚴峻的外部形勢,不能沉著冷靜、客觀判斷,只囿于負面形勢給經濟增速帶來的下行風險,忽視了經濟趨緩過程所伴隨的內部結構改善這樣的積極信號,做出動員式的投資躍進的決策。這樣不僅會讓已有的調控成效付之東流,還會為未來進一步的產業升級制造障礙。
7月經濟數據近日陸續公布,消費、投資和出口等三駕馬車均不那么盡如人意,CPI同比漲幅下滑至兩年半谷底,同時進出口增速雙雙下跌,出口增速為1%,遠低于6月11.3%水準,而進口增速為4.7%,也低于6月的6.3%增幅;與此同時,工業增加值與固定資產投資等關鍵數據亦低于市場預期。
一些地方卻已經開始各種刺激經濟的行動,以“穩增長”的名義,計劃各類上馬項目,如寧波、南京、長沙均出臺了不同版本的刺激計劃。而近日開封舉債千億造新城,不乏為投資沖動的另一種解讀。
用項目投資來刺激經濟,實際上還是傳統的投資拉動舉措,但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的宏觀環境和幾年前相比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沿用老一套手段刺激經濟,恐有南轅北轍之虞。
當前的投資增速下滑主要是國內政策主動調控的結果。中國祉科院全球宏觀經濟季度報告顯示,政策主動調控對投資增速下滑的直接貢獻是52%,外需疲弱對投資增速下滑的直接貢獻占17%,兩者共同作用下導致的投資增速下滑占31%。整體來看,投資增速下滑只有三成是因為外需,而七成是因為政策調控。
可感欣慰的是,與投資增速下滑相伴隨的是投資結構的改善或優化。自上而下的應急性的投資刺激計劃容易造成市場資源配置行為的扭曲,表現為投資過度集中在房地產、“鐵公基”項目之上,這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其他生產性行業投資的擠出,并帶來關聯行業的過度膨脹。
近一年的調控效果表明,房地產、“鐵公基”及關聯行業的投資增速出現了明顯回落,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租賃和商業服務,教育,文化、體育、娛樂以及電力生產等行業出現了投資增速。這種轉變有利于服務業的發展,減少服務業滯后對居民消費的制約。
從消費來看,盡管7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3.1%,繼續延續此前增幅下滑的趨勢,但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不包括服務,同時還包括了政府、企業等社會集團的消費。如果采用包括服務并剔除社會集團消費的指標,比如從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來看,2012年1~6月同比增長8.4%,比第一季度的8.2%要高,且明顯高于去年同期的5.9%。換言之,從個人消費的角度看,以往常常提到的保障性動機等導致的“儲蓄壓倒消費”的現象,可能也在轉變之中。
就目前而言,更大的風險在于外需。一些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長期化不僅可能壓垮發達市場,而且正在拖累新興市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表現出“風景這邊獨好”的“金磚”國家,已經出現“松動”的跡象。國際評級機構可能因為增長放緩、改革乏力而將印度的評級從“投資級主權債務評級”下調,南非的評級前景也由“穩定”轉為“負面”。與發達市場相比,新興市場國內秩序對外部沖擊的敏感性更高,盡管危機的源頭在發達市場,但不排除新興市場甚至有先于發達市場出現新的風險的可能。
這些外部風險通過投資、進出口等渠道也可能對中國產生影響,表現為外需的下降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增長失速。從中國的外貿情況來看,盡管對歐盟、日本等市場出口出現停滯或放緩,但對東盟等市場的出口增速有所上升;盡管加工貿易增長乏力,但一般貿易增速不錯。與投資及消費的情況類似,外貿部門在下行風險或壓力之下,也表現出了結構上的優化。
中國的產業和宏觀經濟正在轉型期,與高速行駛的汽車一樣,只有適當放慢速度方能平穩轉彎。不管不顧地追求速度,要么是被慣性所牽引,在“不可持續”的舊路上越走越遠,要么是出現突然的方向性轉折,導致車毀人亡。
中國經濟突圍真正的危險,是面對嚴峻的外部形勢,不能沉著冷靜、客觀判斷,只囿于負面形勢給經濟增速帶來的下行風險,忽視了經濟趨緩過程所伴隨的內部結構改善這樣的積極信號,做出動員式的投資躍進的決策。這樣不僅會讓已有的調控成效付之東流,還會為未來進一步的產業升級制造障礙。
對政府而言,外部形勢越是危急,越要忍住赤膊上陣的沖動。反而是應當借此機會,綜合運用稅收、信貸等手段維持優化經濟結構的宏觀調控,同時清理簡化各種行政審批手續,降低國內交易費用,為企業創造良好的生產經營環境,務實微觀層面的競爭力和創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