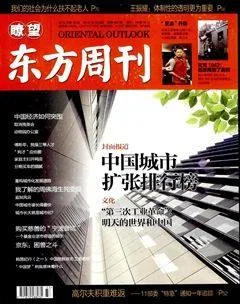我了解的周佛海生死變局

世人盡知周某在被判死刑之后未久,即由當時擔任國府主席的蔣中正下令減處無期徒刑。其實,這中間還有著無窮的變化與懸疑的起伏。
我早年習法,畢業后轉行(在《中央日報》)做了專門采訪法律的新聞記者,前前后后,從地院、高院,跑到最高法院,也自普通法庭跑到軍事法庭,甚至跑到了審判日本戰犯的特別法庭。這一路下來,既目擊過市井小偷的哭號喊冤,也得見南京大屠殺案主犯谷壽夫中將的受刑就死,更從旁檢視陸軍上將、前臺灣軍政長官陳儀的刑后遺體。此外,在下也曾敘述了戰后國家大審大號漢奸的始末。
可是,在這一連串的聽審、觀刑的經歷中,最讓我終生難忘的,還得數一九四六年十月七日南京首都高院舉行的那次“盛況空前而詭譎多變”的審判。
也許有人會問,法官審案,慎重莊嚴,法庭又何必像劇場般講究場面!旁聽者又怎會動了感情?而在下更做啥要搬出“盛況”、“多變”這一類的套語來加以狀述?
答案異常簡單,只緣受審被告是汪偽政權多有作為、事實上的頭號漢奸周佛海,而庭內庭外數以萬計的聽眾也多是周某當年治下的百姓。表面上,他們是來聽審,內心里,許多人竟然是趕來替他捧場。說得更正確一點,他們是借為周某歡呼捧場之舉,來表現對于勝利還都的重慶客的極端不滿!
……
審判中,周佛海以上佳的口才、煽動的言詞,聲稱他之所以參與汪偽組織,目的實在拯陷區同胞于水火,且以此博得法庭外聽審群眾的喝彩。但是就法言法,這種詭辯怎樣也掩蓋不了投敵賣國的事實。因此首都高院在慎重審理之后,依然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判以死刑。
世人盡知周某在被判死刑之后未久,即由當時擔任國府主席的蔣中正下令減處無期徒刑。其實,這中間還有著無窮的變化與懸疑的起伏。
周妻救夫
綜計自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首都高院判處周以死刑,到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國府主席下令為周減刑,這一百三十八天之間,攸關周某生死的案件便有著如此曲曲折折的發展。
先是在抗戰勝利之初,周佛海等因曾戴罪立功,有助國府復員,乃由軍統局長戴笠“邀”赴重慶暫避風頭。是時,周亦曾以親筆悔罪書狀托人呈送蔣氏。言道:“此次回渝,似墮落子弟回家,實無顏以見家長,辱承鈞座寬大為懷,特予愛護,雖粉身碎骨,亦無以報宏恩于萬一。”
呈文中,他并懇求,如果當局愛惜,不加誅戮,他當長期幽居深山密谷,將八年親身經歷形諸筆墨,以警戒后人。
蔣先生當時雖無明確表示,但周某自期有功于國府,復得蔣氏親信有力人物如戴笠者衛護,應無生死之憂。
及翌年三月戴笠乘機撞山而亡,全國各地復進發懲奸之聲,特別是左派人士以周年前曾為國府守護滬杭,不讓他人染指之言,更表不滿,如上海《文匯報》便曾刊登《周佛海怎么樣了》的“讀者投書”,指出:試問罪大惡極如周佛海者,為什么至今沒有發落?而且像他那樣的人,難道真的還要調查犯罪證據?……如果周佛海不立即明正典刑,那么中國根本無漢奸,中國根本無叛逆,我要為淪陷區同胞大哭!
終于,出于周犯行大重,被押返京受審,法庭在法言法,嚴正判以死刑。
此際,周某及周妻楊淑慧發覺事態嚴重,乃緊急采取兩項措施應急:一、急請名律師戴修纘及楊嘉麟寫好向最高法院聲請覆判訴狀,以周妻名義立即呈遞,除提具周某迭向國府請準自首之證據外,并歷述其秘密供應國府情報及協助國軍之事實,要求覆判。二、周妻為救夫心切,病急亂投醫,經人介紹,據稱曾與一保密機關首長內眷見面,并送去黃金一百五十大條,言明錢到刑除,從此便可高枕無憂。
不料公私雙管齊下結果,依然無濟于事,最高法院刑事第一庭(審判長葉在均、推事李紹言、孫葆衡及陳樸生)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宣示的判決書中,依然核準了首都高院所做判處死刑的原判。
周妻雖曾雙管齊下,但一則由于兩審法官之在法言法、鐵面無私;另一方面,她私下圖以買命的一千五百兩金子,更是被人訛詐,毫無效用。
至此,乃再與律師及親友商量,連忙采取三項對策:首先,由楊淑慧向首都高院具狀聲請再審,指出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條規定,法官審案時,對于被告有利及不利證據均應給予同等注意,而高院審訊時,被告重要證人彭壽、程克群(均為軍統派在周處潛伏的情報人員)二人正由軍統羈押中,未能對代周辦理自首及在周寓設立電臺與重慶聯絡之事到庭作證。現二人均獲釋放,已能到庭,故請準予再審,否則前審既對若干重要證據“漏未審酌,遽予判決,氏實難甘服”云云。
同時,也由楊淑慧出面,另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具狀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鄭烈,指出已向首都高院聲請再審,“惟查聲請再審并無停止執行之效力,但氏夫判處死刑,人死不可復生,設使再審之后,幸獲較輕之判決,但死者已矣,豈不抱屈九泉。謹呈請鈞長本好生之德,稍緩執行,俾氏夫緩死須臾,候最終法律上之救濟。哀哀上告,伏乞矜鑒,不勝迫切待命,感激之至。”
狀末并仿照古代婦女代夫陳情請命格式,謙卑地寫上一行“罪婦周佛海之妻楊淑慧謹呈”字樣,與一年半前猶充偽行政院長兼偽上海市長再兼偽中儲銀行總裁一品大命婦時的顯赫,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這種寫法雖不免落入俗套,但讀之也頗感人,無怪當日以革命元勛出任檢察長的鄭老先生,看了之后,果然按捺住他的火爆脾氣,不曾立即下令行刑,這樣,也才讓國府主席在兩個月后有著下令減刑的余裕。
CC派與陳布雷向蔣求情
也就在聲請再審、并哀求稍緩行刑同時,周妻也三番兩次向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懇請賜助,聲言周某在戰前原是CC派內特級上將,在附汪之后也曾掩護陳氏派駐上海代表林尹等進行敵后工作,二陳如尚念及舊情,實不應不伸援手。
陳家兄弟以情不可卻,也趕在同月二十五日聯名函呈當局,請求免周死刑。函并寫道:“惟周于勝利前一年所表現者,全能按照第三戰區預定計劃,例如派羅君強為上海市長(實為市府秘書長)、丁默邨為浙江省長,在京滬一帶暗中部署軍事,頗為周密,勝利后更使江浙兩省不致盡陷共黨之手,國府之得以順利還都,并運兵至華北各地,不無微功。”
這封信說得非常直率,相信對周之最后得以減刑,應有助力。
不料那些據理守法的各級司法官員就是不肯稍讓一步,周妻聲請高院再審的狀子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三日剛遞進去,該院在四天后便毫不猶豫地駁回。
此時,周妻眼見循司法途徑以求救濟之路已窮,一面抱著姑且再試心理,仍然針對高院駁回再審申請的裁決,向最高法院提出抗告;另一方面則全力纏住蔣主席的幕僚長陳布雷,請陳設法安排她徑自拜謁蔣氏,當面代夫求情,哀懇蔣氏以國家元首身份,使用約法(當時憲法)賦予特權,對周加以特赦或予減刑。
陳布雷一生行事守分守法,可是對當年相交至深、朝夕相處的首席助手周某,卻無法置身事外,見死不救,乃乘間破例向蔣氏請求,而蔣氏念及周某當年扈從之勤,與戰后助守京滬之功,也不能全然無動于衷。于是在陳氏安排下,當年二月某日,周妻乃得由保密局長毛人鳳陪同,前往南京黃埔路官邸晉謁蔣氏。
據隨周附逆且為周某密友的前輩報人金雄白記述當日情況如次:
(楊淑慧)進入室內,蔣氏已經坐候在那里,周太太一見到這國家的元首,是她丈夫多年忠心相事的領袖,現在,生死就操在他的手上,她止不住眼淚簌簌地下流,面向著他,立刻就跪在地上,她只剩得抽咽與悲泣,什么話也沒有講。其實,什么話還用得著講嗎?佛海為什么要參加汪政權?參加以后與蔣氏的關系如何?抗日勝利前六年中他做了些什么?戴笠雖然死了,蔣氏應該是最清楚的一個人。
今天,周太太所祈求的,不是什么功罪是非,而只是能留得她丈夫的一條性命。她以無言來代表千言萬語,除此之外,她還能說些什么呢?
室中的空氣,顯得凄涼而嚴肅,除了周太太的泣聲而外,萬籟俱寂。蔣氏面色也很鄭重,還不時皺著眉頭。終于他向周太太以輕緩的語調說話了。蔣先生說:“這幾年,對東南的淪陷地帶,還虧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來,安心回去吧!讓他再在里面休息個一兩年,我一定讓他再歸來的。”
蔣氏的寥寥數語,以一個私人的家室來講,已經是生死骨肉的綸音,她趴在地上再磕了三個摯誠的感激的頭,含著眼淚,隨了毛人風出了官邸。(見金著《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據金說,周妻拜謁蔣氏經過是她“在悵惘與悲痛中親自告訴我的,應該不會是什么空中樓閣”。照我們判斷,除了記述中所引蔣氏談話有添油加醋為周洗刷之嫌外,其余當不致距離事實太遠。
蔣介石發布減刑令
就在這次會面之際,蔣氏曾寫信給國府司法院長居正和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承認他曾透過戴笠對周某表示過“準予戴罪立功,以觀后效”之意,并提出“該犯似可免予一死,可否改判,即希望司法院核辦可也”的建議,還想把免周死罪的責任,讓司法機關負起。
這封信是以國民政府代電方式,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一日發出。但司法機關仍未因此改變主意,即在次日,最高法院刑事第六庭(審判長周韞輝、推事馮慶鴻、羅人驥、胡恕與羅國昌)便確切指出首都高院拒絕再審理由充足,當將周妻抗告駁回。
至此司法救濟之路已窮,蔣主席便不能不自損威信也自負責任地在當年三月二十六日,勉強發布如次的減刑命令:
查周佛海因犯《懲治漢奸條例》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罪,經判處死刑,褫奪公權終身。現據該犯呈報:某在敵寇投降前后,維護京滬杭地治安事跡,請求特赦。查該犯自民國三十年以后,屢經呈請自首,雖未明令允準,惟自三十四年八月十九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續為轉呈,準備事實表現,圖贖前愆。曾令該局奉諭轉知該犯,如于盟軍在江浙沿海登陸時響應反正,或在敵寇投降前后確保京滬杭一帶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則準予戴罪圖功,以觀后效等語,批示該犯在案。似可免其一死,經交司法院依法核議,茲據呈復,該犯在敵寇投降前后能確保滬杭一帶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對社會之安全,究屬不無貢獻。可否將該犯原判死刑減為無期徒刑,理合呈候鑒核等情。茲據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準將該犯周佛海原判之死刑,減為無期徒刑。此令主席蔣中正。
周某在老虎橋監獄聞此喜訊,得知絕處逢生,一時高興得如癡如狂,當即在囚室之中,賦詩一首如次,“驚心獄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無事殊。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絕處轉通途。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懷仍故吾,更喜鐵肩猶健在,留將負重度崎嶇。”
此時周五十初度,自以為行年不過知命。設能善變如昔,未始不可卷土重來,因此在那段時期,他的心情相當好,在獄中接見同鄉諸友舊屬易君左時,還不停與易氏大開玩笑,要易氏回去寫篇文章,題為“虎牢探奸記”,并強調是漢奸的“奸”,不是監獄的“監”!
不過,這種心情也沒有維持多久,漸漸的他孤處獄中,同牢親信如羅君強、楊惺華亦因“被他拖下水去”,而與他遠離,視同陌路。于是在內心大感空虛之余,再全然轉調另賦《春夜》一詩曰:“那堪伏枕聽鵑聲,寂寞春宵怨恨深;好夢乍回魂欲斷,半窗明月照孤衾。”
未久他患上慢性心臟病,漸次更感染了其他的并發癥,幾近一年掙扎之余,周已是燈盡油枯形銷骨立,終于變得既不能坐、更不能睡,只得把被褥疊高,日夜俯伏其上不斷喘息呻吟,特別是最后三十八天,更是不斷慘呼嚎叫,一直到全身銷盡,困頓至死。時間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有人說這就是天譴,死得比綁赴法場一槍斃命還要難過痛苦!
法官趙琛的嶙岣風骨
回過頭來,從周案前后的曲折迂回,我們也大可看出舊日司法人員的嶙峋風骨與公正胸懷。
猶憶當年蔣主席在頒發手令,指示“各黨、軍、政府機關應將已捕之漢奸一律移交法院審理”之后,原則上早將審奸之事完全委諸法曹裁決而未加干預,例如陳公博、陳璧君、王揖唐、王克敏、梁鴻志、褚民誼、林柏生、殷汝耕及丁默邨輩巨奸大惡,均任由法庭判以應得重刑。只是對于確曾戴罪立功的周佛海如何處置,則自始即感躊躇。
他先讓戴笠把周送往重慶暫避風頭,其后為了對歷史有個交代,又不得不把周押返南京移付法庭。
據知即在此時,他曾召見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以對周似可以將功折罪為由,謂法曹減無期徒刑。當謝氏將此一旨意轉告負責審奸的首都高院院長兼審判長趙琛之后,趙氏卻立予頂回,說周某叛國情節之重,遠在群奸之上,無論是在法言法,或者為整飭民族風紀氣節,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
趙氏也曾提出折中建議,指出在法,周某不能不判死刑;但元首基于政治或政策上考慮,卻可依約法加以特赦,或予減刑,借最高行政權力以為救濟。
趙氏意見經謝氏轉報后,蔣主席當下也沒說什么,原以為最高法院仍可酌情改判較輕之刑,不料最高法院刑庭諸公,一樣不肯屈法輕判。蔣雖不得已親函居正、謝冠生,明示欲請輕判之意,但法曹依然未允遵辦,最后,蔣才撿回拋不出去的滾燙番薯,自行負責,很不情愿地發出減刑命令。
不過,正直、強硬的趙琛,也因此影響了自己的前程。
本來趙氏精研法理、刑法尤稱大師,各方原期必有綜理法部之命,乃歷屆閣揆呈送所擬閣員名單之際,趙氏雖屢列司寇首選,但上頭批下來的總是另有某人!就是這樣,公正廉能的一代法學大家,便枯守在友人讓住的不及二十席的“官邸”之內,以最高法院檢察長致仕以終!
五十年代中,在下曾與趙氏談及周案,他總是肅容正色而言:“周佛海叛國大罪,難以歷數,依法,除判以死刑之外,別無他途可循。否則,我便是昧于忠奸之分,上對不起中華民族列祖列宗,下無以對中華民族的子子孫孫,中也有愧于公正廉明的司法同僚!”聽他言來,依然是無怨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