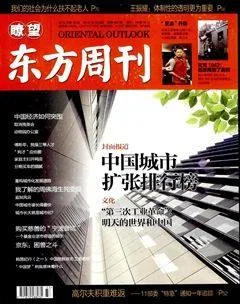傅斯年:我是三等人才
李方桂板著臉頗為嚴(yán)肅地說道:“在我看來,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xué)人員是二等人才,當(dāng)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
1940年12月底,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學(xué)所先后由昆明搬遷到四川南溪縣李莊鎮(zhèn)。傅斯年把房子分配完畢,即回重慶中研院總辦事處幫助上任不久的代理院長朱家驊處理各種繁瑣事務(wù),史語所的日常工作由李方桂代為主持。
李方桂者,山西昔陽縣大寨村人也,1902年李方桂出生于廣東,十歲時(shí)隨母親二度進(jìn)京讀書,后考入清華學(xué)堂,并于1924年渡海遠(yuǎn)赴美國安阿波爾的執(zhí)密安大學(xué)攻讀語言學(xué)和哲學(xué)。兩年后的1926年,當(dāng)他拿到了語言學(xué)學(xué)士學(xué)位,進(jìn)入芝加哥大學(xué)繼續(xù)攻讀語言學(xué),接受美國最重要的語言學(xué)家愛德華·薩丕爾、倫納德·布龍菲德爾和達(dá)爾寧·勃克等三位教授的悉心指導(dǎo)進(jìn)行語言學(xué)訓(xùn)練。正是得益于三位大師的精誠指導(dǎo),極具天賦的李方桂才成就了未來在語言學(xué)事業(yè)的輝煌功業(yè)。
1929年,李氏拿到了博士學(xué)位,決定回國。
在李氏回國之前,曾給趙元任寫信告知行期,趙氏又告知了中研院院長蔡元培,并建議把這位學(xué)成歸來的大字號“海龜”延聘到中研院語言組做研究工作。李乘坐的“不列顛皇后”號輪船剛一抵達(dá)上海,求賢若渴的蔡元培就派一位代表及時(shí)登船,把李方桂接到早已訂好的旅館中看護(hù)起來。此舉令喝慣了洋墨水的李方桂深為感動。
李氏住進(jìn)旅館的第二天,蔡元培就邀請他到自己在上海的家中做客并共進(jìn)午餐,席間談到準(zhǔn)備任命李方桂為中研院史語所專任研究員的打算。李方桂接受這個職位,于1930年正式進(jìn)入中研院史語所,在趙元任主持的語言學(xué)組與羅常培等著名學(xué)者共事。
1937年上海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前,李方桂與趙元任先后赴美國耶魯大學(xué)和夏威夷大學(xué)講學(xué)。1939年,李氏回國,此時(shí)史語所已遷往昆明,趙元任在昆明小住不久,即再度赴美到耶魯大學(xué)接替了李方桂留下的空缺職位。但中研院史語所語言組主任一職出缺,見李方桂歸隊(duì),傅斯年蒙生了讓其代理趙氏職務(wù)的打算。因事出倉促,想不到竟碰了釘子。
可能李方桂因當(dāng)年父親入仕為官和中年隱退的經(jīng)歷,幼小心靈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自他入清華學(xué)校之后,就對參政為官之人產(chǎn)生了厭惡之情,并立志以學(xué)術(shù)研究為自己的畢生事業(yè)。當(dāng)他自美返國后,在抗戰(zhàn)前八年的中研院研究生活中,對傅斯年平時(shí)顯現(xiàn)的霸氣與牛哼哼的勁頭越來越看不順眼,更對其整天晃動著笨重的身子,滿頭大汗地跑來跑去,為國民黨政府出謀劃策、指手畫腳的舉動感到不快,甚至從心理深處產(chǎn)生了憎惡之情。如今見傅氏找上門來讓自己出任代理所長的“官”,久積于胸中的塊壘經(jīng)此觸動,如同一根細(xì)小的引線點(diǎn)燃了火藥,槍管中的彈丸受到火力的助推,“唰”地一聲穿堂而出,朝著傅斯年發(fā)射而來。
李方桂板著臉頗為嚴(yán)肅地說道:“在我看來,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xué)人員是二等人才,當(dāng)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聞聽此言,頓時(shí)面紅耳赤,張口結(jié)舌說不出話。待回過神來,額頭上已是汗珠點(diǎn)點(diǎn),他掏出手巾一邊擦汗一邊眨巴著眼睛看了看李方桂,知趣地躬身作了一個長揖,退出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傅斯年懵懵懂懂地挨了一槍狼狽地溜走后,李方桂覺得自己剛才的言語有些過火,遂有幾分悔意。在以后的日子,李氏自動低調(diào)處理與傅斯年的關(guān)系,兩人在表面上又成了相互依托的朋友。
但二人很難傾心相交。正如多少年后李方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萊伍德市他的別墅中,對自己的口述記錄者所言:“除了普通的學(xué)術(shù)上聯(lián)系外,我們很少有共同的話題,因?yàn)槲覀兊难芯款I(lǐng)域不同。當(dāng)然作為朋友,又另當(dāng)別論……當(dāng)然啦,首先他是研究所所長,位置高高在上,再者……”
“再者”之后的省略號中隱含著什么具體內(nèi)容,無人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