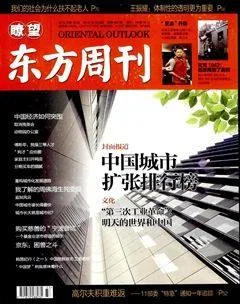災荒1942:是誰揭露了真相





勇于披露河南災情的媒體,只有重慶《大公報》、美國《時代》周刊、南陽《前鋒報》等寥寥數家,這些難得的災情報道,成了1942年河南災荒最珍貴的歷史記錄。
鄭州市十八里河鎮南劉莊村民劉春發,今年87歲,提起70年前的那場大災荒,他眼睛濕潤、聲音顫抖:“太慘了,太慘了……”
劉春發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從1942年夏天開始,天一直沒有下雨,莊稼絕收,村民斷糧,他們村餓死了幾十口人,他家就有3位親人餓死。
91歲高齡的景愛云是鄭州市南郊黃崗寺村人,她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時,黃崗寺村餓死的人更多,她娘、她叔、她的兩個堂妹都餓死了。
河南省檔案局保管利用處副處長劉志遠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由于時值戰亂,河南省政府幾度遷移,這個時期的檔案留存非常少。不過,僅存的這些檔案,還是真實地記錄了1942年河南旱災發生時的情況。
這場大災難至今少為人知,僅隱約存現于當時零星的新聞報道和后來少量的文學作品中。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歷時數月,走訪河南、陜西多地,搜集史料,查閱檔案,尋訪親歷者,探尋1942年河南旱災的歷史真相。
“500萬人”
1943年12月河南省政府編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災工作總報告》中的《河南省三十一年(民國三十一年,即1942年)各縣旱災調查表》顯示,全省111個縣中有96個縣被列表統計,其中災情嚴重的有39個縣,受災總人數達1200萬人。
1946年,河南省社會處編印的《河南災情實況》一書這樣記載當時的災情:田園龜裂,赤地千里,二麥顆粒無收,秋禾全數枯萎。于時樹葉草根,都成上品,腐木細泥,亦用果腹……災民因饑餓難忍,而服毒者,縊死者,自刎者,甚至殺兒以求一飽者,所在多有,司空見慣,同時無主棄嬰,到處可見,音若泣聲,到處可聞,死尸橫野,無人收埋,鬼哭神號,無殊地獄。陰森凄慘,絕異人寰……
河南省檔案館收藏的《國民黨上蔡縣執委關于報因災吃人情形的呈》證實,河南旱災期間,確有“吃人”慘劇發生:上蔡縣呂店鎮第十八保第十一甲王莊60余歲的貧民劉卷良,家貧如洗,乞討無門,曾在(1943年)3月4日將餓死的乞丐“解割煮食”,以救饑荒。
而據《河南災情實況》中《河南省各行政區人口受災損失統計表》附注中所列,此次旱災死亡人數達300萬。
關于這場河南旱災的死亡人數,另外一種說法是“500萬人”。
在《江流天地外》一書中,時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郭仲隗回憶:1942年,我續任第三屆國民參政員,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數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準報災,亦不救濟,我以參政員奔走呼號,不遺余力,“結果河南餓死了500多萬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報了1602人,開政治上未有之奇”。
同樣,在當時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的筆下,河南旱災的死亡人數也是“500萬人”。
1943年3月22日,白修德在報道《等待收成》中提到:在河南 3400 萬人中,我們估計有300萬已經淪為難民。此外,還將有 500 萬人會在秋收季節前死去。
而在白修德晚年的回憶錄《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中,“500萬人”這個數字再次出現:“我在最后一周里集中精力匡算出了災區預計將發生的死亡人數,最樂觀地估計,有 500萬人已經或正在以這種或那種方式死去,占正常人口的 20%。”
除了餓死的500萬人,還有300萬災民背井離鄉,外出逃難。他們拖家帶口,一路討飯,向西面和南面的國統區、邊區艱難逃亡。
甚至吃“石頭面”
今年87歲的鄭州人劉春發回憶,因為莊稼絕收,村民們都沒東西可吃,連榆樹皮都刮下來吃了。榆樹皮刮下來后,去掉外層,把內層白色的部分曬干、搗碎,與花生皮一起在磨上碾,做成饃吃。劉春發說,榆樹皮不苦,但是很黏,吃完身上腫。
盡管如此,榆樹皮還是有限的,很多村民連榆樹皮也吃不上,慢慢就餓死了。他們村當時有200多口人,餓死了幾十口。劉春發家共有7口人,其中奶奶、父親和妹妹3人都餓死了。
當時,政府不僅沒有救災發糧,還向老百姓征糧,不交就打人、嚇唬,逼得老百姓紛紛逃離。因為河南北面和東面已經淪陷,逃荒的老百姓只能向西、向南逃。當時為了防止日本鬼子西犯,隴海線洛陽以東的鐵軌已經拆毀,老百姓只有步行到洛陽,然后扒火車向西逃。有去西安的,有去寶雞的,最遠有跑到新疆的。劉春發因為有老有少走不開,留在了老家。
91歲的景愛云娘家是鄭州黃崗寺村的,她回憶說,當時日本鬼子殺人放火,村民們被殺、餓死的很多,不少老百姓都外出逃難。她娘也逃出去了,結果餓死在路上。她的叔叔和兩個女兒都餓死了。
88歲的河南宜陽縣人趙士友向《瞭望東方周刊》回憶,1939年至1943年是他老家尋村黃窯旱災最為嚴重的幾年。那時候,家里沒有吃的,常吃一種用柿蒂和粗糠磨成的面。旱災最嚴重的時候,吃得最多的是野菜和樹葉,甚至吃“石頭面”。
“石頭面”的做法,是把一種質地松酥的石頭拍碎,磨成面,攪點菜,然后在烙饃的鏊子上炕干吃,“這個不能吃多,吃多了解不下溲”。
在趙士友的家鄉,經常有逃荒的災民路過,鄭州人最多,開封以南周口、鄢陵、扶溝一帶的人也不少。幾乎每天都有攜家帶口的逃荒者上門討飯,“這個走,那個來,我們也沒啥給他們的,最多抓一把面,自己還沒啥吃的”。
趙士友回憶,當時大批的逃荒者,住在村里的破廟和空窯里,有餓死在村里的,有大老遠背著家具來賣的,“還有賣孩子的”。
商丘虞城人萬翠蘭,今年87歲,她向本刊記者回憶,她娘家是虞城曹余莊的,因處于低洼地帶,四周常年積水,旱情沒有鄭州那邊嚴重,但還是有很多土地干裂、莊稼旱死。
她記得后來的蝗災比較嚴重:蝗蟲飛來時一大片,遮住了太陽,莊稼很快變成一片光桿。遇到墻壁,蝗蟲能爬滿墻。為了治蝗,老百姓都在地里挖溝,把打死的蝗蟲就地掩埋。
勇于披露災情的媒體
由于時隔久遠,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親歷者,已經無法完整回憶起70年前那場大災荒的詳細情節。
而當時的一些新聞報道,則真實記錄下了當年災荒的慘絕景象。
1942年10月26日美國《時代》周刊報道:兩萬平方英里的河南省北部地區正陷入饑餓之中。男人和女人們正在吃樹皮和草根,腹部腫脹的孩子們被賣掉換取糧食。數千人已經死去,數十萬人走投無路,千萬人面臨著一整個漫長冬天的大饑荒的折磨。
一個母親有一個嬰兒和兩個大些的孩子,在討飯的長途中疲勞不堪,坐在樹下休息。她叫兩個大些的孩子到前面的村子里討一點吃的,當孩子們回來時,母親已經餓死,嬰兒還依然使勁吸吮著她的奶頭。
在洛陽,成捆的樹葉被賣給饑民當食物,一塊錢一捆。孩子們的肚子因為吃下這種食物而變得膨脹和水腫。有時饑民的家庭找來家里所有殘存的食物,共同吃上最后一次飯然后集體自殺。
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報道:隴海路上河南災民成千成萬逃往陜西,火車載著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樣,沿途遺棄子女者日有所聞,失足斃命,更為常事。
在洛陽街頭,蒼老而無生氣的乞丐群像蜜蜂一樣嗡嗡響,“老爺,救救命吧!餓得慌啊!”他們伸出來的手,盡是一根根的血管,再看他們的全身,會誤認為一張生理骨干掛圖。他們的體力跟不上吃飽了的人,一個個地邁著踉蹌步子,叫不應,哭無淚,無聲無響地餓斃街頭。
沿途災民扶老攜幼,獨輪小車帶著鍋碗,父推子拉,或婦拉夫推,也有六七十歲老夫妻喘喘地負荷前進。一路上的村莊,十室九空了,幾條餓狗畏縮著尾巴,在村口繞來繞去也找不到食物,不通人性的牲畜卻吃起自己主人的餓殍。
因為吃了一種名叫“霉花”的野草,災民們臉部浮腫,鼻孔與眼角發黑。而在連“霉花”也沒得吃的葉縣,災民們正在吃一種干柴,一種無法用杵臼搗碎的干柴,一位老農夫說:“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在河南災區,牛早就快殺光了,豬盡是骨頭,雞的眼睛餓得都睜不開。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在驢上到豫東馱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斗糧食。
1943年4月6日南陽《前鋒報》報道:饑餓的災民們吃干了的柿葉、剝下的柿蒂,蒺藜搗成的碎粉,吃麥苗,撿收鳥糞,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籽,甚至掘食已經掩埋了的尸體。
他們宰殺了平日愛如生命的雞犬,宰殺了他們相依為命的耕牛,賣掉他們的鋤頭、破襖,然后賣出他們的土地,最后摘下他們的心頭肉——賣了兒女,賣了老婆。然而,結局還是被死亡劫去。
在黃泛區,野犬吃人吃得兩眼通紅,有許多瀕死但還能蠕動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在鄭州,有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鄭州馬永道夫婦,親自動手煮吃了他們的親生女兒香菊;在洛陽,有個滎陽籍的災民親手殺死他的一妻二子后投井。
勇于披露河南災情的媒體,只有重慶《大公報》、美國《時代》周刊、南陽《前鋒報》等寥寥數家,這些難得的災情報道,成了1942年河南災荒最珍貴的歷史記錄。
《大公報》被停刊三天
1943年2月初,《大公報》發表了記者張高峰真實報道河南大災的通訊《豫災實錄》與總編輯王蕓生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觸怒了國民黨當局,被勒令停刊三天。
張高峰(1918—1989),天津蘆臺(今天津市)人。1940年秋,他到遷入四川樂山的武漢大學政治系讀書,兼任《大公報》通訊員。
1942年12月,《大公報》派張高峰到河南任戰地記者。他從四川經西安到洛陽,后從洛陽南行,經過密縣、登封、臨汝、寶鹽到達葉縣。沿途,他看到成千上萬的河南難民蜂擁入陜,到處是骨瘦如柴的乞丐,隨處可見災民扶老攜幼、推著獨輪車逃荒。他親眼看到附近村里的孩子一個個餓死,村民吃了有毒的野菜而全身麻痹浮腫。尤其令他憤懣的是,災情如此嚴重,縣鄉政府還逼著農民納糧,交不出糧就抓到縣政府痛打,還逼災民賣地抵租。
張高峰以眼見耳聞的事實寫了一篇通訊,名叫《豫災實錄》(原名《饑餓的河南》),發表于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他憤怒地說:“災旱的河南,吃樹皮的人們,直到今天還忙著納糧!”他還尖銳地指出,中央早就決定對河南從減征購,省政府也在唱賑災高調,可惜這莊嚴的命令沒收到半點效果。
2月2日,《大公報》發表了總編輯王蕓生寫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王蕓生指出,河南的三千萬同胞,大都已深陷在饑饉死亡的地獄,至今尚未見發放賑款。尤其令人不忍的,災荒如此,糧課依然,縣衙門捉人逼拶,餓著肚納糧,賣了田納糧,讓人聯想到杜甫筆下窮兇極惡的“石壕吏”。
恰好,與這篇社評同版,轉發了一條來自河南魯山的中央社新聞,稱“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實征購,雖在災情嚴重下,進行亦頗順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貢獻國家”。王蕓生引用這條消息后寫道:“這‘罄其所有’四個字,實出諸血淚之筆!”
王蕓生感嘆,我們生活在天堂一般的重慶,重慶無冬,人們已感近幾天的寒冷。盡管米珠薪桂,重慶還很少聽到餓死人,一般人家已升起熊熊的炭火。而在河南,朔風吹雪,饑民瑟縮,缺衣無食,又有多少同胞凍餒而死!……看重慶,念中原,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據王蕓生后來回憶,在這篇社評發表的當晚,新聞檢查所派人送來了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限令《大公報》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報》遵令于1943年2月3日、4日、5日停刊了三天。
不僅如此,《豫災實錄》作者張高峰亦受到當局報復。據張高峰之子張刃回憶,1943年 3月初,張高峰在河南葉縣被國民黨豫西警備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訊,后押至戰區司令長官總部,由當時被河南民眾稱為“四災”(水、旱、蝗、湯)之一的國民黨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中原王”湯恩伯親自夜審。湯明確提出了豫災報道和張高峰給重慶《新華日報》供稿的事,張高峰據實回答,但不承認自己有共產黨員身份,之后僥幸脫身。
“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
王蕓生后來知道,《大公報》之所以被停刊三日,是“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
2012年8月18日,本刊記者在陜西省圖書館收藏的《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五輯至第二十八輯)中看到,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王蕓生、總經理曹谷冰撰寫的《1926至1949的舊大公報》一文,披露了《大公報》被停刊事件的真實原因。
王蕓生回憶,當時,因為停刊事件他向蔣介石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詢問究竟,陳布雷回答:“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是省政府虛報災情。李主席(培基)的報災電,說什么‘赤地千里’、‘哀鴻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并且嚴令河南的征實不得緩免。”
關于“蔣介石大罵報災者”一事,本刊記者搜索民國史料時發現,民國時期著名軍閥、蔣介石的結拜兄弟馮玉祥,在其回憶錄《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里也進行了生動記載。
馮玉祥回憶,當時,河南大旱,餓死人無數,就在這樣慘痛之下,蔣介石還叫河南征糧。那位河南主席實在沒有辦法,大膽地向蔣介石說:“旱災太厲害。”蔣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罵起來說:“一點廉恥都沒有,一點人格都沒有,就是胡造謠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說有旱災!”無人格長、無人格短地罵了一個鐘頭。
《我所認識的蔣介石》還披露,當時,河南省的參政員郭仲隗大罵政府:“河南這樣大的災,你們眼瞎了么,看不見?你們的耳朵聾了么,聽不見?”他在參政會內足罵了一個鐘頭。郭還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幾種東西,送給各院部長官,包括“觀音土”。
外媒實地調查
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中提到的“后來又有外國記者團故意去照了許多相片帶回來”,指的正是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和英國《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到河南災區實地調查事件。
白修德(1915—1986),本名叫西奧多·H·懷特(Theodore·H·White),美國人,抗日戰爭時長期任美國《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因為熱愛中國,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白修德。
1942年10月,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來自洛陽和鄭州的傳教士的信件,得知河南正發生著罕見的大災荒,他根據這些材料寫了《十萬火急大逃亡》的災荒報道在美國發表,當時并未引起人們的充分關注。
1943年2月,《大公報》因報道河南災情和批評當局被“停刊三日”后,白修德深受震動,決定親赴河南實地調查。
1943年2月底,白修德和好友、英國《泰晤士報》攝影記者哈里森·福爾曼一起,沿隴海鐵路經寶雞、過西安到達河南境內進行調查采訪。
一路上,白修德和福爾曼看到了一幕幕令他們難以置信的慘絕景象:狗在路旁啃著人的尸體,農民在夜幕的掩護中尋找死人身上的肉吃。無盡的廢棄村莊,乞丐匯聚在每一個城門口,棄嬰在每一條道路上號哭和死去。
飛馳的火車頂篷上,不時有擁擠的難民從車上摔下來。其中一個剛剛摔下來的難民,流著血躺在路基上,車輪切掉了他的腳。他孤身一人,號哭著,他那被軋平的血肉殘留在鐵軌上。他腳部的骨頭露出來,像細弱的白色玉米稈。
白雪覆蓋的鄭州,碎石鋪成的街道充滿了衣衫襤褸、人形鬼貌的饑民……當他們要死的時候就躺在爛泥和水溝旁待斃。一個姓馬的婦女試圖吃掉她的小女兒,嬰孩身上的肉被送到公堂作證據。官府指控她殺了孩子并吃了她的肉。她辯解說是孩子餓死在先,然后她才去吃了死者的肉。
與災民的悲慘處境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駐防在河南的軍隊依然在征收糧食和實物供養自己,而當地每個政府官員也會按月得到定額的糧食。
令白修德和福爾曼意外的是,他們離開鄭州之前,當地官員設宴招待他們,菜肴異常豐盛:有兩個湯,有辣藕片、胡椒雞、荸薺炒牛肉,還有春卷、熱蒸饃、米飯、豆腐、雞和魚,最后,“我們還吃了3個霜糖餅”。
后來,白修德在著作《中國的驚雷》中再次回憶起了這頓飯:“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
在返回途中,白修德急速在洛陽電報局向美國《時代》周刊發了一篇揭示河南大災真相的新聞稿《等待收成》。1943年3月22日,該報道在《時代》周刊刊發,國際輿論一片嘩然。
當時正值宋美齡在美國四處演說、求取貸款,白修德的報道使她惱羞成怒,她強烈要求《時代》周刊老板亨利·盧斯解雇白修德,被盧斯拒絕。
回到重慶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蔣介石面呈實情,但蔣卻拒不接見。后來,在宋慶齡的安排下,蔣介石最終同意會見。
關于蔣介石會見白修德一事,白修德晚年在自己的回憶錄《探索歷史——一個人的歷程》中進行了詳盡記述:蔣介石在他昏暗的辦公室接見了我,他站在那里顯得身材挺拔,儀容整潔,用僵硬的握手表示禮節后,就坐在他的高靠背椅上,臉上帶著明顯的厭煩神情聽我講述。
會見中,白修德說了人們如何被餓死,說了征稅,還有乘機敲詐勒索的丑行。但蔣介石否認征收了農民的稅,也堅稱“不可能出現狗吃死人的情況”,直到同行的福爾曼當場出示了“狗站在路邊刨食死尸”的照片。
白修德寫道:(看到這些照片)總司令的腿開始輕輕抖了一下,有點神經質地抽搐,他問道,照片是從什么地方拍的?我們告訴了他。他拿出他的本子和毛筆開始記下來……接著,他向我們道謝,說我是“比我親自派出去的所有調查員”更好的調查員。
白修德事后發現,這短短20分鐘的會見,起到了一些作用:糧食開始從陜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多余糧食……
引發“民變”
與旱災同樣嚴重的是蝗災。
《河南災情實況》記述,在1942年之后蝗災連續大暴發期間,大批飛蝗,遮天蔽日,逐隊群飛,所過之處,遇物即嚙,禾苗五谷,當之立盡……蝗蟲長自泛區漸次年延,遍及全境……總計四年(1942~1945年)受害面積達272839678畝!
1942年6月28日,《河南民報》披露,尉氏縣境內發現蝗群:大群飛蝗,遮蔽天空,東西達十余里寬,由北向南飛去,一時月色為之籠罩暗淡……
“湯災”,是指國民黨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中原王”湯恩伯給河南人民帶來的人為災禍。他不僅橫征暴斂、抽丁拉夫,設立苛捐雜稅達38種之多,而且所轄部隊紀律渙散,奸淫搶掠,橫行鄉里。
當時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謝偉思給美國政府的報告中寫道:河南災民最大的負擔是不斷增加的實物稅和征收軍糧。全部所征糧稅占農民總收獲的30%~50%,其實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稅,通過省政府征收的全國性的實物土地稅,還有形形色色、無法估計的軍事方面的需求。
在天災人禍的多重壓迫下,饑餓的河南災民不堪重負,發生“民變”。
1944年春夏之交,日本在中國發動“一號作戰”,40萬國軍潰敗。當湯恩伯部向豫西撤退時,豫西山地的農民舉著獵槍、菜刀、鐵耙,到處截擊這些散兵游勇,后來甚至整連整連地解除他們的武裝,繳獲他們的槍支、彈藥、高射炮、無線電臺,甚至槍殺、活埋部隊官兵。湯恩伯5萬多國軍士兵,就這樣毀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