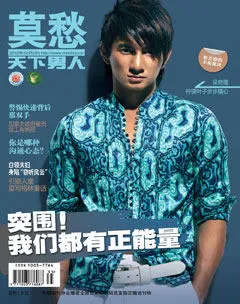“我”的四個面孔
我們都是千面人:公開場面上熱情開朗,回到家里沉默寡言;面對上司畢恭畢敬,與同事周旋靈活機動;買東西錙銖必較……
大多數情況下,對付這些相互矛盾的自我,我們游刃有余。我們在這些不同的面具之間換來換去,甚至沒有覺察,除非聽到別人提醒:“你怎么這樣?我簡直認不出你來了。”別人這么一說,我們馬上又會覺得自己的形象四分五裂,模糊不清。
心理學家認為,從童年開始,“自我”就是“我”同外部世界的交接點,它讓我們隨機應變,以適應所處的境地,回應別人的問話。但是,如何在適應外界的同時又不失去自我?心理治療師簡·特納說:“如果我在說話或做事時感覺不自在,那就說明我背離了真實的自我。當一個人表現出真實的自我時,他會感到安全、清醒與和諧。”因此,在尋找真實自我的過程中,要特別關注內心隱秘的情感,傾聽它的聲音。
心理學學家克里斯多夫·安德烈認為,自我的面孔雖然千變萬化,但大致可以分為四種主要類型。
窒息的“我”
思凡有過這樣的經歷:上大學時,有一次和朋友閑聊,請朋友說出他最大的缺點是什么,朋友說他是個非常虛偽的人,為人一點也不真誠。朋友的批評一下把思凡說懵了,因為他一直以為自己是個隨和而善良的人。
因為我們害怕沖突,壓抑自己的攻擊性,就產生了窒息的自我。簡·特納認為,害怕沖突源于我們對基本安全感的需要。“當心靈深處有一個不和諧的聲音小聲嘀咕時,我們害怕它會招來危險,就會立即把它壓住。從遠古人那兒遺傳下來的記憶中,我們保留了‘反對別人會威脅生存’的觀念。”所以我們以為,如果遇事同別人爭辯,也許老板會開除,警察會罰款,小商小販還會嘲笑我們。低調做人至少不會惹上大麻煩,但遺憾的是,這需要壓抑內心深處的欲望、期盼和夢想。
若想改變這種狀況,我們應該慢慢懂得,說服別人最好的辦法是開口講話,別人的粗暴反駁并不是什么致命的災難。可以先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開始這么做,然后遇到重大事件時也試著這么做。
變形的“我”
熱戀中的麗莎像變了一個人,朋友們為此憂心忡忡:“我們都認不出她了。”這是典型的弗洛伊德筆下的變色龍女人,她認定自己的本來面目不值得別人愛,于是在無意識中改變了自己的人格,換成了一個自以為對方喜愛的樣子。
變形的我通過別人的認同發揮作用。它沒有獨立的存在,只能依賴別人的眼光,自愿做別人的囚徒。它是如此強烈地渴望成為另一個人,為此不惜奉獻自己的快樂和幸福!當矛盾的自我沖突不斷時,就會產生焦慮、暴怒等情緒甚至生病,這些都是信號,表明我們在尋找自我的途中迷路了。
心理學家建議:我們應該學會區分“我本來是什么樣”以及“我應該是什么樣”,把內心深處真實的自我表現出來,這并不會妨礙你和他人的交往,反而會獲得對方情感上的認同。
教條的“我”
誰要反對他,誰就要倒霉了:因為教條的我是強行裝出來的,害怕差異和不同。他工作時說一不二,回到家像個暴君,對孩子充滿威嚴,但在其他場合,卻表現得相當令人愉快。這個看上去明晰、威嚴的我,實際上極度脆弱。在威武莊嚴的外表下,他生活在被別人摧毀的恐懼中。
馬克在公司里總是溫文爾雅。回到家,得知妻子想離開他時,一下子變得蠻橫無禮,他對妻子大喊大叫,說要走盡管走好了,他就是這樣,永遠也改變不了。這些話的真正含義是,他害怕妻子的離去會把他摧毀。如果一個一向和藹可親的老板,暴怒之下把文件扔到某個下屬的頭上,他這么做,無非是害怕別人比自己優秀。
教條的自我在青少年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個階段,人往往拒絕任何妥協,容不得反對意見。簡·特納解釋說:“青少年沒有別的辦法確認自我,但是成年以后,我們知道自己是誰,這就意味著我們懂得該在什么時候說‘不’,什么時候說‘是’。成熟的標志就是學會保持平衡。”
自在的“我”
這是自我的成熟期。通過傾聽自己的情緒和感覺,接觸到最深層的自我,能夠說出我究竟是誰。
心理學家認為,我們只有與自己達成統一,才能與自我的不同側面和平共處。我們都知道,當我們處于不同的環境,面對不同的人時,會有不同的表現;但是在所說、所想、所做和所感之間,我們大致能夠保持一條連貫的脈絡。不管是行動上還是言語上,最要緊的是與真實自我的那個最堅硬的核心保持一致。也就是說,說話做事時,我們不應當違背自己最基本的價值觀。更何況,只有了解自己最真實的需求,才能懂得別人的需求。這樣一來,在尊重自我與尊重他人之間,我們就能達到平衡。(摘自《心理月刊》)
編輯 鐘健 1249768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