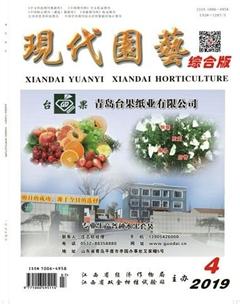廣南縣發(fā)展蒜頭果的意義、優(yōu)勢及建議
王菖莉 陳福 徐德兵 楊華斌 賈代順
摘要:蒜頭果(Malania oleifera)是國家二級保護植物、云南省極小種群和國家珍貴用材樹種,加上果油神經(jīng)酸含量達46%,主要生長在石漠化區(qū),具有較高的經(jīng)濟、生態(tài)價值,2018年毛油價格達65萬元/t,統(tǒng)籌發(fā)展好蒜頭果產(chǎn)業(yè),對推進石漠化經(jīng)濟生態(tài)協(xié)調(diào)發(fā)展、促進精準(zhǔn)脫貧和鄉(xiāng)村振興具有重要意義。主要分析了廣南縣蒜頭果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基礎(chǔ)和優(yōu)勢,并對產(chǎn)業(yè)發(fā)展提幾點建議,希望對產(chǎn)業(yè)發(fā)展有所幫助。
關(guān)鍵詞:蒜頭果;發(fā)展意義;優(yōu)勢;建議
蒜頭果(Malania oleifera Chun ef Lee)屬鐵青樹科蒜頭果屬,常綠喬木,是我國特有單屬單種古老植物、國家二級珍稀瀕危保護樹種、云南省極小種群重點拯救保護對象和國家二類珍貴用材樹種。蒜頭果生長迅速,但因受其自身生物學(xué)特性、氣候及特定環(huán)境的限制,自然資源分布狹窄,僅零星或小片狀間斷分布于云南東南部的廣南縣、富寧縣及廣西西部的石灰?guī)r山區(qū),具體位置為北緯22°23~24°48,東經(jīng)105°30~107°30區(qū)域內(nèi),云南主要分布于海拔300~1640m,廣西主要分布于海波300~1000m。常綠喬木,高達20m,胸徑達40cm;樹干挺直,樹皮灰褐色,稍縱裂;是微酸至中性樹種,土壤pH值4.5~7.2,幼苗、幼樹期喜陰濕環(huán)境,隨著樹齡增大而逐漸喜光。
1發(fā)展意義
1.1合理的開發(fā)利用,將極大地促進該物種的保護
生物多樣性保護及地帶性植物保護是當(dāng)今世界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課題之一。隨著人口增加和經(jīng)濟的發(fā)展,人們對環(huán)境的破壞也越來越大,出現(xiàn)了許多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資源銳減等現(xiàn)象,導(dǎo)致許多生物物種的消失,使生物多樣性面臨著自身進化和人類嚴(yán)重干擾的雙重威脅。世界各國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呼聲日益高漲,人們已意識到拯救珍稀瀕危物種,保護地帶性植物,維護生態(tài)平衡的重要性,相繼制定了世界性和各國的保護生物多樣性、拯救瀕危野生生物和保護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多項公約和政策法規(guī),并將“拯救瀕危野生生物”列為了《生物多樣性公約》框架下的一項戰(zhàn)略任務(wù)。蒜頭果為國際預(yù)瀕危保護植物,在《云南省極小種群物種拯救保護緊急行動計劃》重點保護對象中名列第11位,是滇東南喀斯特石灰?guī)r地區(qū)特有的高價值珍稀物種。因此,要實現(xiàn)對蒜頭果的保護,首先必須要壯大該物種的種群,只有開展蒜頭果種植相關(guān)技術(shù)研究與開發(fā)利用,防止野生資源過度利用和破壞,才能更好地保護這一物種。
1.2有利于石漠化區(qū)域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
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和民生林業(yè)建設(shè)是黨中央作出的重大舉措,石漠化治理是國家在西部實施的重大生態(tài)項目之一。云南省石漠區(qū)生態(tài)脆弱、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生態(tài)治理區(qū)域涉及面廣,而群眾靠山吃山,單一營造生態(tài)林已嚴(yán)重影響了山區(qū)群眾的生產(chǎn)、生活,也難以真正摘掉“貧困帽”。因此,如何找到具有強大的生態(tài)功能,又具有較高經(jīng)濟價值的優(yōu)勢樹種,促進石漠化區(qū)經(jīng)濟、生態(tài)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成為各級各部門的難題。蒜頭果生長迅速,主要分布在云南東南部的廣南和廣西西部巴馬等300~1640m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區(qū),是喀斯特石灰?guī)r地區(qū)的特有樹種,樹高可達20m,冠幅可達16m2,屬常綠闊葉樹種,根系發(fā)達,抗旱能力極強,是良好的生態(tài)樹種和治理石漠化的優(yōu)良鄉(xiāng)土樹種,對推動石漠化區(qū)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1.3極高的經(jīng)濟價值,有利于石漠化區(qū)精準(zhǔn)脫貧和鄉(xiāng)村振興
首先,蒜頭果種仁含油率為64.5%,油中富含40%~50%的神經(jīng)酸(順-15-二十四碳烯酸),是一種長鏈不飽和脂肪酸,最早發(fā)現(xiàn)于哺乳動物的神經(jīng)組織,故命名為神經(jīng)酸,最早從鯊魚油中分離出來,又名鯊魚酸。1972年,英國權(quán)威神經(jīng)學(xué)教授Sinclar等研究發(fā)現(xiàn),鯊魚腦組織在受重創(chuàng)后的短時期內(nèi)能夠自行修復(fù)。該現(xiàn)象被證明是因為鯊魚部分腦組織中一種為“神經(jīng)酸”的物質(zhì)在修復(fù)大腦神經(jīng)信息傳遞通道——神經(jīng)纖維上發(fā)揮了神奇的作用,這一發(fā)現(xiàn)引起世界各國科學(xué)家的高度重視。后來,大量醫(yī)學(xué)研究證明,神經(jīng)酸是大腦神經(jīng)細胞和神經(jīng)組織的核心天然成分,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fā)現(xiàn)的能促進受損神經(jīng)組織修復(fù)和再生的特效物質(zhì),是神經(jīng)細胞特別是大腦細胞、視神經(jīng)細胞、周圍神經(jīng)細胞生長、再發(fā)育和維持的必需“高級營養(yǎng)素”,對提高腦神經(jīng)的活躍程度,防止腦神經(jīng)衰老有很大作用。具有恢復(fù)神經(jīng)末梢活性,促進神經(jīng)細胞生長和發(fā)育的功能,并對心血管疾病及人體自身免疫缺乏性疾病等有顯著的療效。目前,國內(nèi)99.99%高純度神經(jīng)酸國際市場人民幣13萬元/kg左右。其次,通過對蒜頭果成分檢測,在蒜頭果仁中發(fā)現(xiàn)了蒜頭果毒蛋白(malanin),是蒜頭果種仁中分離及純化出的一種新型蛋白質(zhì),是一類有酶活性的有毒蛋白質(zhì),對人和動物有強烈毒性。但據(jù)云南民族大學(xué)民族藥資源化學(xué)國家民委一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研究表明,蒜頭果蛋白對雞、兔的紅血球都具有凝集作用,是一種植物凝集素,為在細胞生物學(xué)、免疫學(xué)、腫瘤、生殖生理等方面提供新的研究手段,為蒜頭果蛋白作為凝集素的開發(fā)利用提供了科學(xué)依據(jù)。云南大學(xué)醫(yī)藥學(xué)院研究表明,蒜頭果蛋白(malanin)分子量分別為30KD(A鏈)和23KD(B鏈)左右,體外抑制腫瘤細胞活性測試表明,蒜頭果蛋白對人宮頸癌細胞(Hela細胞)具有較強的毒性,說明蒜頭果蛋白具有用于免疫毒素治療癌癥的應(yīng)用前景,為研制新一代抗腫瘤藥物打下了基礎(chǔ)。最后,蒜頭果還是最好的珍貴用材樹種。蒜頭果是高大喬木,樹干通直,高達20m,胸徑達40cm,木材紋理較好、密度大、耐腐蝕、不裂不翹。是家俱、船舶等上好材料,是國家珍貴用材樹種,市場價高達4000元/m3左右。
總之,蒜頭果因極高的經(jīng)濟價值,如能更好地開發(fā)利用,對石漠化精準(zhǔn)脫貧和鄉(xiāng)村振興將產(chǎn)生積極作用。
2發(fā)展優(yōu)勢
2.1資源優(yōu)勢
2013年,由廣南縣林業(yè)局、云南省林業(yè)科學(xué)院油茶研究所和文山州林業(yè)局種苗工作站組成了調(diào)查組,歷時16個月,完成了廣南縣蒜頭果資源調(diào)查。經(jīng)調(diào)查,廣南縣蒜頭果主要分布在董堡鄉(xiāng)、蓮城鎮(zhèn)、舊莫鄉(xiāng)、曙光鄉(xiāng)、南屏鎮(zhèn)、那灑鎮(zhèn)、楊柳井、珠琳鎮(zhèn)8個鄉(xiāng)鎮(zhèn)23個村委會66個自然村,分布面較廣,總株數(shù)12945株,而全世界僅存有野生蒜頭果資源20000多株,全部處于野生狀態(tài),廣南縣占資源量的64.73%,年產(chǎn)種子45t左右。廣南發(fā)展蒜頭果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yōu)勢。
2.2工作基礎(chǔ)
2.2.1開展了蒜頭果主要生境因子分析研究,為栽培區(qū)劃提供依據(jù)。蒜頭果喜冬無嚴(yán)寒、夏無酷熱的溫暖濕潤氣候,一般年均溫在16~19%較適宜,但能耐-6°C的低溫。廣南蒜頭果分布在22°23~24°48N和105°30~107°30E狹窄區(qū)域內(nèi)。多分布在江河流域兩側(cè)坡背陰面,石灰?guī)r山區(qū)及石灰?guī)r山區(qū)與土山過渡帶。通過典型優(yōu)勢植株調(diào)查,90%以上優(yōu)樹分布在海拔1200~1500m,初步確定蒜頭果適宜栽培區(qū)為海拔1200~1500m。多生長在中坡以下,坡度30。以下,少許長于山頂,但生長不良。95%生長在陰坡、半陰坡及半陽坡,少許在陽坡生長的,早期植被較好,土壤濕潤。多數(shù)分布于江河流域兩側(cè)陰坡面。經(jīng)到最適宜區(qū)董堡、蓮城、舊莫蒜頭果林下取10個土樣檢測,pH值為4.34~6.96,平均值達5.56,說明蒜頭果喜歡微酸性至中性土壤。主要為黃壤、砂壤及石灰?guī)r發(fā)育的近中性土壤。同時,土樣的鈣含量平均高達1111.38mNkg,有機質(zhì)高達214.21 g/kg,說明蒜頭果對鈣及有機質(zhì)要求較高。
2.2.2苗木快繁技術(shù)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開展蒜頭果實生繁殖和嫁接技術(shù)研究,建立了快捷的蒜頭果苗木快繁技術(shù)體系。采用沙床催芽,使出芽率達92%,采用芽苗砧嫁接,成活率達84%,取得了較好效果。通過沙藏點播或植芽苗,解決了蒜頭果移栽成活率低的問題,為蒜頭果規(guī)模化發(fā)展奠定了基礎(chǔ)。
2.2.3品種選育按程序開展。自2004年以來,為解決蒜頭果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良種問題,在廣南縣委、縣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投入200多萬元,由云南省林業(yè)科學(xué)院油茶研究所承擔(dān)蒜頭果良種選育工作,由于是一個新樹種,無經(jīng)驗可借鑒,油茶研究所從良種選育技術(shù)方法及指標(biāo)體系建立、優(yōu)良單株選擇評價方法及工作開展、無性繁育技術(shù)研究、傳粉機理研究等開展了系統(tǒng)的育種工作,經(jīng)過11年的努力,初步選定目標(biāo)遺傳育種單株230株,建立了完善的檔案,為蒜頭果良種選育奠定了基礎(chǔ)。
2.2.4產(chǎn)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高效栽培技術(shù)研究與示范基地建設(shè)。廣南縣已完成《蒜頭果產(chǎn)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計劃到2037年,全縣完成基地建設(shè)1.67萬hm2,目前,結(jié)合退耕還林工程,每年以533hrn2速度推進。云南省林業(yè)科學(xué)院油茶研究所先后開展了蒜頭果移栽成活率、混交技術(shù)、栽培密度、栽培模式、高效栽培技術(shù)、病蟲害綜合防控等研究,基本解決了蒜頭果的栽培技術(shù)問題。截至2018年底,在廣南董堡、蓮城、舊莫、曙光等鄉(xiāng)鎮(zhèn)建立示范基地1053.67hm2。
2.2.5產(chǎn)品加工。廣南縣年僅產(chǎn)蒜頭果干種子45t左右,受資源限制,廣南永豐神經(jīng)酸科技開發(fā)有限公司從事蒜頭果收購及初加工,毛油價65萬元/t,經(jīng)南京圣諾永豐生物科技實業(yè)有限公司、杭州圣諾生物科技實業(yè)有限公司等企業(yè)精深加工為神經(jīng)酸膠囊銷售,公司生產(chǎn)的和壽堂牌《神經(jīng)酸膠囊》售價在1980元/盒,規(guī)格為48g(240mg×50粒×4瓶),神經(jīng)酸含量31.2%,折價神經(jīng)酸13.3萬元/kg。由云南省林業(yè)科學(xué)院油茶研究所為科技支撐,廣南圣諾永豐神經(jīng)酸科技開發(fā)有限公司申報的神經(jīng)酸(順15-二十四碳烯酸)通過了國家衛(wèi)計委新資源食品審批,批準(zhǔn)文號為衛(wèi)食新通字[2017]2,意味著為蒜頭果保健品,食藥準(zhǔn)字號產(chǎn)品開發(fā)敞開了大門。昆明醫(yī)學(xué)院2017年開發(fā)出了利用蒜頭果開發(fā)出了神經(jīng)酸神經(jīng)噴劑和含片,上市后銷量較好。
2.2.6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已開展蒜頭果原生地、地理標(biāo)志、蒜頭果之鄉(xiāng)保護申報工作,進一步開展在專利、標(biāo)準(zhǔn)、品種等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創(chuàng)新與申請保護研究工作。
3幾點建議
3.1制定相關(guān)扶持政策
縣委、縣人民政府應(yīng)及時制定出臺《廣南縣蒜頭果產(chǎn)業(yè)發(fā)展苗木扶持辦法》《廣南縣蒜頭果種植基地建設(shè)扶持辦法》等相關(guān)扶持政策。對在廣南縣從事蒜頭果種植的單位或個人,經(jīng)縣林業(yè)局審核,報縣人民政府審批,無償提供苗木,對在廣南縣境內(nèi)建立的3.33hm2以上的蒜頭果基地,經(jīng)縣林業(yè)局核實及組織驗收,達到技術(shù)及撫育標(biāo)準(zhǔn)的,經(jīng)報縣人民政府審批,給予一定的補助。其它在種源保護、加工基地、產(chǎn)品認(rèn)證等也出臺相應(yīng)的扶持辦法,促進蒜頭果持續(xù)健康發(fā)展。
3.2建議把蒜頭果納入大健康產(chǎn)業(yè)加以扶持
目前,發(fā)達國家(歐盟、日本)已把神經(jīng)酸作為大腦營養(yǎng)補充劑廣泛應(yīng)用于智力提升、記憶力改善、神經(jīng)性疾病治療。隨著我國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老齡化的加重,神經(jīng)酸產(chǎn)品不再是發(fā)達國家專利,將在我國產(chǎn)生良好的市場前景,建議縣委、縣人民政府將蒜頭果產(chǎn)業(yè)納入大健康產(chǎn)業(yè)加以扶持。
3.3加強對現(xiàn)有資源的保護
近年來,隨著蒜頭果多部位提取物在醫(yī)療、保健方面的特殊功效不斷被挖掘,蒜頭果資源的珍貴性越顯凸出,搶采盜采嚴(yán)重,進一步加劇了野生蒜頭果資源的人為破壞性,野生種群數(shù)量急劇減少,加上火災(zāi)、生境破壞等因素,資源保護壓力持續(xù)加大。建議建立極小種群自然保護小區(qū)及種質(zhì)資源庫,保護野生種質(zhì)資源和進行遺傳多樣性保護,為開發(fā)利用保存種源。加大對伐樹采果、搶采盜采等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避免物種再遭受破壞。
3.4加強創(chuàng)新團隊建設(shè)和知識產(chǎn)權(quán)保護
抽調(diào)一支技術(shù)隊伍,組建創(chuàng)新團隊,從良種選育、豐產(chǎn)栽培、產(chǎn)品研發(fā)等開發(fā)全產(chǎn)業(yè)鏈研究,為蒜頭果產(chǎn)業(yè)發(fā)展提供新動能。盡快在原生態(tài)產(chǎn)品、地理標(biāo)識產(chǎn)品、蒜頭果之鄉(xiāng)等知識產(chǎn)權(quán)領(lǐng)域開展申報工作,提升蒜頭果產(chǎn)品品牌;鼓勵技術(shù)人員開展標(biāo)準(zhǔn)制定、論文發(fā)表、專利申請等工作,夯實發(fā)展基礎(chǔ)。
3.5激勵科技創(chuàng)新,解決當(dāng)前制約蒜頭果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技術(shù)瓶頸
一是盡快建設(shè)蒜頭果種質(zhì)資源庫,進行優(yōu)良種質(zhì)資源收集保存。由于自然和人為因素,蒜頭果野生資源急劇減少,進行種質(zhì)保護已迫在眉睫,否則將面臨優(yōu)良種質(zhì)資源枯竭。二是建立蒜頭果天然種群保護區(qū),使野生蒜頭果資源免遭破壞。三是加快蒜頭果良種選育攻關(guān),實現(xiàn)蒜頭果產(chǎn)業(yè)量與質(zhì)的提升。目前,由于蒜頭果無良種,只能實生種植,始果期長,豐產(chǎn)性差,效益低。要實現(xiàn)蒜頭果的高效栽培,必須要解決良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