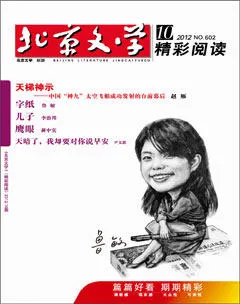字紙外的傳統敬畏與現代文明進程

城市龐大且復雜,要把握城市生活并將其藝術化,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說過,當下都市小說很難寫好的重要原因,是我們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都市文化經驗,這與我們成熟的鄉村經驗是非常不同的。近幾年,魯敏的小說創作一直在尋求變化,她試圖走出小鎮“東壩”進入城市,并頑強地尋找書寫都市的可能性。這篇《字紙》就是她繼續尋找的一個重要佐證。
《字紙》里,老頭子老申帶著頑固的少年記憶,對寫有字或印有字的紙張都非常著迷——這是鄉村里非常傳統的崇拜與敬畏。在他老年后進入城市,仍然葆有著這種樸素的,他本人引以為豪的慣性,對一切的紙質印刷品、特別是報紙愛不釋手。當然,這些帶字的紙為他帶來了虛榮,填補了老年性的“混吃等死”。他知道很多別人不知道的事情(哪怕根本無需知道),無論是面對兒子、兒媳還是別的什么人,他都可以夸夸其談無所不能。老申由此獲得了巨大的滿足,更增添了一種對字紙的感激、尊崇之情。他細小不舍、積攢搜集起的報紙越來越多,以至于連陽臺都堆積不下了,“那些紙張,從三個堆到六個堆,再到九個堆,個個兒的都差不多跟老申本人一樣高了,碼得格格正正的,像一排士兵方隊,筆直地站在陽臺上,蔚為壯觀。”
但老申與字紙的依偎關系很快碰到了現代性的擊打:兒子帶他去了一趟書店。在書店,老申驚懼地發現了自己的問題,在龐大的書店里,老申用自己的方法什么也沒有讀到,也無法讀到,尤其是海量日產的電子書專區,他像暴風雨中的小樹葉兒一樣根本找不著北……兒子拉他走,卻發現拉不動了。“老申的身子歪著,臉上的表情也歪著,簡直像是中風,那模樣,說不出是憤怒還是傷心。他固執地站著,不能移動,好像哪里有了內傷,沒紅沒腫沒疙瘩,最高明的醫生都瞧不出。”老申被現代傳播的高度發達與豐富徹底擊中了——從書店回來后的老申“明顯不那么活潑,眉眼有點空洞了。報紙雖還是照看,廣告紙片兒雖還是照拿,但那虔誠勁兒卻明顯弱下去,更了不起的是,無師自通!他竟一下學會了默讀與瀏覽,一份報紙,嘩嘩嘩翻著,跟任何一個老練的閱讀者一樣,不過五分鐘,嘩,看完了。然后,馬虎而倦怠地疊了,再馬虎地堆到陽臺上,神情散淡得很。”——他心里清楚,過去視為珍寶的、他這么多年一直堅守和篤信著的“敬惜字紙”已經沒有價值了,那么“高級”的令他“心尖兒發顫”的字紙,在今天已是一堆不折不扣、等著化為紙漿的垃圾。
《字紙》究竟要寫什么?表面上似乎是寫這個老申的孤獨、衰老、愚昧、戀物、自閉……細想想,又不完全是。實際上,這種個體的精神衰變,正體現出傳統農耕文明里的字紙敬畏與現代文明強大力量之間的必然沖突。
少年時代的老申與字紙的關系始于“用帶字的紙擦屁股”,這些紙片正是鄉土生活的文化碎片:同學的分數、過期的賬目。尤其在爺爺是村干部的田小茂家上廁所時他被“震住”了:田家用的居然是來自國家和中央的報紙。他小心地帶走了三小片報紙,然后不斷地拼接,每玩一次結果都不同……老申正是帶著這樣的對字紙的高級感受成長起來的,這是一種虔誠的知識崇拜。這樣的記憶“甜美而令人心兒發顫”,使老申直到老年仍念念不忘揮之難去。實際上,這不僅僅一個個體的心理學問題,也是世代農耕文明孕育下的現實性問題。尤其對老申這一代人來說,就算他“也能識文斷字,但在旁人及他自己的意識中,終究還是個粗人”,他對于“知識文化”與“新聞、信息”有著強烈的渴求與追慕之心,竭力想通過投入“字紙”來緊跟這個時代、享用這個時代。一葉障目之下,他一度以為他做到了。但直到他進了書店、見識到現代印刷術的海量“垃圾”及電子傳媒術的日產“無限空間”之后,老申意識到,他所認真閱讀并精心保存的那些報紙、那些知識、那些新聞,什么也不是!在這樣龐大迅猛、難以超越的電子世界面前,他覺悟到自己的愚蠢與可笑,完全像一只落伍的、自不量力、井底觀天的青蛙。
他的解決之道即是:決心退回到他現有的小小字紙陽臺里去。這樣,當破爛王來收報紙的時候,老申申張了他的“循環論”,拒絕賣報:“你們把我這廢紙收回去了,幾個輪回,一個大循環,它們還是要回到我這里來。你買了賣,我賣了買,轉過去又轉回來!你們倒說說,這有什么意思?”最終,老申成了一個孤獨的勝利者,他“隱約含笑,移步換景,一個人轉到陽臺上,那八九堆一人多高的報紙,如世界上最微觀的叢林,他側著身子在其中輕手輕腳地走,擠擠挨挨地走……那些字紙,為感知遇之恩,忽地軟化了、變形了,飛散開來,如同懸浮在半空中的黑色顆粒,粗糲、爛漫而窒息,倒襯得老申的背影有了幾分飄逸之態。”
老申的退守,是勝利,同時也是失敗,是傳統白紙黑字遭遇海量信息時代的個體潰敗,也是鄉村農耕文明遭遇到現代信息文明之后的必然性疼痛。面對傳媒技術、面對信息進步,面對正在崛起新文明的便捷與暴力,老申只有躲藏回他固有的記憶,以陽臺作“字紙爐”去祭奠傷逝的傳統。現代性的確帶來了諸多好處,眾生為其謳歌,高舉雙臂歡呼,它是如此地高效、迷人,擴大人類的占有,沒心沒肺地于瞬息間層層覆蓋,可其中的殘酷性與疼痛感又是如此地折磨人啊!但現代性正是這樣的一條不歸路,無論老申有怎樣的感受,無論每一個肉身的個體要經受怎樣的傷害,它都會一如既往、轟隆向前,沒有悲憫可言。魯敏對這一命題的巧妙捕捉,顯示出她獨具的眼光和力量。
《字紙》篇幅雖薄小,言外之意寬大厚沉。
責任編輯 張頤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