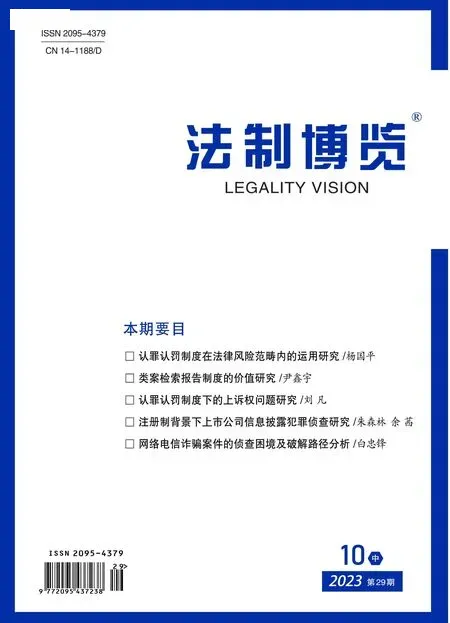農業行政處罰程序的幾個問題探討
孔維益 徐學榮
1.宣威市板橋街道農業綜合服務中心,云南 宣威 655413;2.宣威市獸藥飼料監察所,云南 宣威 655400
行政處罰程序與實體并重[1],違反法定程序作出的行政處罰在行政訴訟中將被人民法院判決撤銷或確認違法、無效。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依法行政的當下,國家對行政執法程序提出了更高要求。《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年)》[2]把完善執法程序作為全面推進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著眼提高人民群眾滿意度,著力實現行政執法水平普遍提升的一個重要內容。然而,在農業行政處罰實踐中,一些執法人員還沒有對執法程序給予足夠的重視,存在重實體(即證據),輕程序的思想,從歷年農業農村部案卷評查情況通報來看,都存在執法程序不合法或有瑕疵、有疏漏等問題,不時有因為程序不合法而被人民法院判決撤銷的案例報導。為貫徹落實《法治政府建設實施綱要(2021-2025 年)》,進一步完善、規范農業行政處罰程序,提升農業行政執法水平,作為一名基層農業行政執法工作者,筆者對基層農業行政處罰實踐中立案前調查取證、陳述申辯、法制審核和集體討論決定等有關行政處罰程序的爭議問題,在查閱相關法律、法規、規范性文件及有關資料的基礎上,從程序和實體方面提出個人淺見,與廣大同仁探討。
一、立案前調查取證的問題
(一)程序方面
發現違法行為→立案→調查取證,是適用行政處罰案件在調查階段的基本程序。然而,在農業執法實踐中,為提高行政效率,執法人員發現違法行為后,有的直接進行調查取證,然后補辦立案手續;有的則采用即時通信方式報請行政處罰機關負責人同意后進行調查取證,然后補辦立案手續。誠然,這兩種操作方式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還可以防止行政管理相對人隱匿、毀滅、偽造有關證據材料等,有利于全面收集固定證據。但這兩種方式合不合法,有沒有行政風險呢?筆者認為,按照公權力“法無授權不可為”原則,如果沒有法律、法規、規章或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則涉嫌程序違法。對于第一種方式,暫沒有法律、行政法規、農業農村部規章及規范性文件規定。就云南省而言,《云南省行政處罰程序規范》(云府法〔2015〕63 號,已失效)[3]第十二條規定,在現場檢查中發現違法行為時,可以先行調查取證,符合立案條件的,應當在7 日內決定是否立案,決定立案的應當補辦立案手續。但該文件有效期至2021 年2 月28 日,現已不再適用,故云南省的執法人員如果還在使用這種方式,則涉嫌程序違法。對于第二種方式,沒有法律、行政法規規定,但《農業行政處罰程序規定》[4]第五十七條有相關規定,即在邊遠、水上和交通不便的地區按普通程序實施處罰時,農業行政執法人員可以采用即時通信方式,報請農業行政處罰機關負責人批準立案和對調查結果及處理意見進行審查。據此,農業執法人員可以有條件采用這種方式,但適用范圍較窄。為使農業行政處罰程序更具操作性,提高行政執法效率,建議修訂《農業行政處罰程序規定》,規定在監督檢查中發現違法行為,可以先行調查取證,補辦立案手續;或者規定可以采用即時通信方式,報請行政處罰機關負責人批準立案,補辦立案手續。
(二)實體方面
對立案后,調查取證過程中可以采取的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以下簡稱《行政處罰法》)、《農業行政處罰程序規定》都有具體的規定,但對日常監督檢查過程中或對違法線索進行核查過程中發現的違法行為,立案前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固定證據,沒有專門的程序法予以規定。筆者認為,立案前可以采取的措施,其實屬于實體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的監督檢查過程中可以采取的措施。據筆者初步統計,現行22 部與農業行政處罰有關的實體法律及行政法規,有11 部具體規定了在監督檢查過程中可以采取包括現場檢查、查閱、復制資料、向有關人員調查了解情況、采樣、留驗、抽檢、查封、扣押等措施。筆者認為,盡管只有11 部法律、法規作出具體規定,但基于實體法律、法規、規章賦予農業行政處罰機關的監督檢查職權,農業執法人員在日常監督檢查過程中或對違法線索進行核查過程中發現違法行為后,可以采取現場檢查、查閱、復制資料、向有關人員調查了解情況、采樣、留驗、抽檢、查封、扣押等措施,收集有關證據、材料。但查封、扣押必須有法律、法規的規定,方可以實施。應當注意的是,查封、扣押和先行登記保存證據,實施前須向行政機關負責人報告并經批準。
二、陳述、申辯的問題
《農業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二十三條第二款規定了采取普通程序查辦的案件,陳述、申辯期限為3 日。在農業行政執法實踐中,對于采取普通程序查辦的案件,當事人在陳述、申辯期限內是否可多次向行政機關提出陳述、申辯意見,以及當事人明確放棄陳述、申辯權利后,行政機關是否可以在陳述、申辯期限內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存在爭議。第一,關于多次陳述、申辯的問題。筆者認為,按照私權利“法無禁止即可為”原則,在陳述、申辯期內,當事人可以多次行使自己的權利。行政機關應充分保障當事人行使陳述、申辯權利,允許當事人多次提出陳述、申辯意見,使其能夠全面表達其陳述、申辯意見。若在陳述、申辯期限內只給當事人一次陳述、申辯機會,就可能因時間倉促、當事人考慮不周,而不能全面表達其陳述、申辯意見,變相剝奪了當事人的權利。第二,關于當事人放棄陳述、申辯后,是否可以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的問題。根據《行政處罰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作出行政處罰決定之前,……拒絕聽取當事人的陳述、申辯,不得作出行政處罰決定;當事人明確放棄陳述或者申辯權利的除外。”參考山東省臨沂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魯13 行終90 號行政判決書①肥鄉縣春雨汽車運輸隊與臨沂市交通運輸局行政處罰二審行政判決書(2016)魯13 行終90 號。:“……被上訴人作出放棄陳述申辯權的處置決定后,其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而不能事后反悔,放棄權利的后果就是接受行政處罰……被上訴人提起本案訴訟,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是國家法律所禁止的行為。”筆者認為,當事人明確放棄陳述、申辯權利后,行政機關不需要等陳述、申辯期限滿,即可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應當注意的是,對于符合聽證程序條件的行政處罰案件,當事人不僅享有陳述、申辯的權利,還享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若當事人只放棄陳述、申辯權利而未明確放棄聽證權利的,行政機關不得在當事人申請聽證的期限內作出行政處罰決定,否則屬于程序違法②滁州市公路運輸管理處、韋俊富交通運輸行政管理(交通):公路交通行政管理(公路)二審行政判決書(2018)皖11 行終97 號。。
三、法制審核的問題
(一)實體方面
法制審核的適用范圍,新老制度規定不一。2021 年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規定了“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直接關系當事人或者第三人重大權益,經過聽證程序的”“案件情況疑難復雜、涉及多個法律關系的”“法律、法規規定應當進行法制審核的其他情形”四種應當進行法制審核的情形。通過對比發現,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沒有引用“可能造成重大社會影響或引發社會風險”這一情形;將《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推行行政執法公示制度執法全過程記錄制度重大執法決定法制審核制度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8〕118 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直接關系行政相對人或第三人重大權益”“經過聽證程序作出行政執法決定”這兩種單獨適用的情形,合并成了一種情形。地方各級政府及行政機關為貫徹落實行政執法“三項制度”,出臺的重大行政執法決定法制審核辦法、目錄清單等,也有與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不相符的情況。這就可能造成法律適用上的混亂。
(二)程序方面
《行政處罰法》規定,有法定應當進行法制審核情形的,在行政機關負責人作出行政處罰的決定之前,應當由從事行政處罰決定法制審核的人員進行法制審核,但未明確法制審核的時間節點,各部門的規章、規范性文件,或未明確規定或規定不一。筆者認為,只要在行政機關負責人作出行政處罰的決定之前進行法制審核,都不違反法律規定,但法制審核不是為履行法定程序而流于形式走過場,其根本目的在于對行政處罰進行監督和把關,若法制審核在履行告知程序前,則可早發現問題,早提出處理建議,使執法機構能夠及時糾正或彌補,若待當事人履行完陳述、申辯或者聽證權利之后再進行法制審核,那么對于在陳述、申辯或聽證、法制審核過程中發現需要糾正或補充調查的,行政機關在予以糾正或補充調查后又要重新履行告知程序,如此降低了行政效率。
四、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的問題
(一)實體方面
一是關于集體討論決定案件的適用范圍。《行政處罰法》沒有規定集體討論決定的具體適用范圍,但《農業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五十五條作了具體規定,即:符合聽證條件,且申請人申請聽證的案件;案情復雜或者有重大社會影響的案件;有重大違法行為需要給予較重行政處罰的案件;農業行政處罰機關負責人認為應當提交集體討論的其他案件,應當由農業行政處罰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對于符合聽證條件的案件,《農業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五十九條已作具體規定,執法實踐中可操作性強,只要按照規定去做就行,但對于“案情復雜”“有重大社會影響”“有重大違法行為”的案件,法律、行政法規、農業農村部規章及規范性文件沒有具體規定,執法人員在認定上存在困難。筆者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綜合有關觀點后認為,“案情復雜”一般包括:案件涉及面廣、多起違法行為交錯或涉嫌多種違法行為、違反多部法律規范、直接證據不充分、證據認定存在困難等情況;“重大違法行為”一般是指:違法行為情節嚴重、性質惡劣、社會危害后果嚴重、有法定從重處罰情形等情況;“重大社會影響”一般是指性質惡劣、社會危害后果嚴重等的重大違法行為,在社會上造成重大影響。
二是關于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的組織形式。在集體討論的具體組織形式方面,法律、行政法規、農業農村部規章及規范性文件沒有明確規定,在執法實踐中可以是黨組會、局長辦公會等集體會議形式。在人員組成方面,包括出席人員和列席人員,行政處罰機關負責人為出席人員,其他有關機構負責人、案件承辦人、案件審核人員等為列席人員。出席人員應當在討論記錄上簽名。需要注意的是,根據《農業行政執法文書制作規范》(農法發〔2020〕4 號)(以下簡稱《制作規范》)第四十八條第六款規定,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的案件,《行政處罰決定審批表》“執法機關意見”欄,應由農業行政執法機關主要負責人根據集體討論決定填寫。
(二)程序方面
《行政處罰法》未明確規定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決定的時間節點,但筆者通過對《行政處罰法》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二條的推斷,結合對《制作規范》第四十八條的理解,應當是在當事人履行完陳述、申辯或者聽證權利之后,對需要進行法制審核的案件,還須在法制審核通過之后進行。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將擬給予行政處罰的集體討論與給予行政處罰的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混淆,否則會導致法定的集體討論程序錯誤。如農業執法實踐中,有時執法機構會組織該執法機構集體或提請行政機關案件審查委員會對執法人員制作的案件處理意見書進行集體討論。這種討論與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有本質區別,它不是法定意義上的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因為,這類討論一是在組織形式上不必是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進行;二是在程序上也不必在經過陳述、申辯或者聽證程序、法制審核程序之后進行;三是討論的對象不是作出行政處罰的處理意見(《行政處罰決定審批表》)。因此,不能因為實施行政處罰告知程序前已進行集體討論而不再經過行政機關負責人集體討論,此時如果省略相應程序則涉嫌程序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