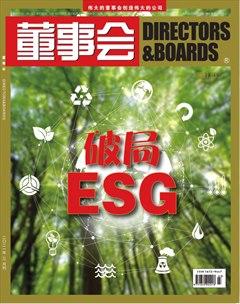中介機(jī)構(gòu)如何面對(duì)“真實(shí)的上市公司”?
衛(wèi)文省
眾所周知,提高我國(guó)上市公司治理是一個(gè)系統(tǒng)工程,需要考慮方方面面的因素,調(diào)動(dòng)方方面面的積極性,科學(xué)組織,嚴(yán)格考核,下大力氣推動(dòng)才可能見效。推動(dòng)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有效提升,需要調(diào)動(dòng)利益相關(guān)者的積極性,而會(huì)計(jì)師事務(wù)所是參與上市公司治理的利益相關(guān)者中很重要的一環(huán)。會(huì)計(jì)師事務(wù)所的執(zhí)業(yè)態(tài)度和服務(wù)質(zhì)量一定程度上對(duì)于改善上市公司財(cái)務(wù)信息質(zhì)量、規(guī)范財(cái)務(wù)管理水平,乃至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準(zhǔn)影響較大。會(huì)計(jì)師事務(wù)所有義務(wù)為上市公司治理增添正能量,而不是帶來一系列問題和隱患。
前不久,一則《證監(jiān)會(huì)立案調(diào)查深圳堂堂 強(qiáng)化審計(jì)市場(chǎng)監(jiān)管》的新聞報(bào)道引人注意。報(bào)道提到:證監(jiān)會(huì)針對(duì)深圳堂堂執(zhí)行的*ST新億2019年年報(bào)審計(jì)業(yè)務(wù)開展了現(xiàn)場(chǎng)檢查,發(fā)現(xiàn)其在執(zhí)業(yè)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根據(jù)檢查情況,證監(jiān)會(huì)已對(duì)*ST新億及深圳堂堂涉嫌違法違規(guī)行為立案調(diào)查。據(jù)此可以做一個(gè)并不完全準(zhǔn)確的判斷:深圳堂堂在*ST新億的公司治理中應(yīng)該沒有發(fā)揮足夠的正面作用。
引人關(guān)注的是,證監(jiān)會(huì)立案調(diào)查深圳堂堂后,*ST新億依舊執(zhí)迷不悟,再度續(xù)聘其為公司2020年的審計(jì)機(jī)構(gòu),并收到上交所的監(jiān)管問詢函。*ST新億在問詢函回復(fù)中辯稱:目前正處于被調(diào)查階段,調(diào)查結(jié)果尚未確定,且證監(jiān)會(huì)無明確會(huì)計(jì)師事務(wù)所被立案調(diào)查期間不能參與審計(jì)業(yè)務(wù)的相關(guān)法規(guī),所以未構(gòu)成限制深圳堂堂承接上市公司審計(jì)業(yè)務(wù)。
筆者以為,中介服務(wù)機(jī)構(gòu)要努力為上市公司治理增添正能量。
首先,嚴(yán)格依法開展業(yè)務(wù),在為上市公司提供高質(zhì)量服務(wù)推動(dòng)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斷提升的同時(shí),不斷為自身贏得更為寬松的外部發(fā)展環(huán)境。企業(yè)都想把自身打造成長(zhǎng)盛不衰的“百年老店”,作為中介服務(wù)機(jī)構(gòu)也需要有這種理念,堅(jiān)持法律底線和行業(yè)底線,不為市場(chǎng)上短期利益所誘惑而降低服務(wù)水準(zhǔn),不提供放棄原則和底線的“有償服務(wù)”。一旦因?yàn)檫`法違規(guī)甚至是犯罪而倒下,更多的中介機(jī)構(gòu)很快會(huì)填補(bǔ)上來,倒下的中介機(jī)構(gòu)很難再站起來,重新獲得比原來更好的外部發(fā)展環(huán)境。
其次,靠信譽(yù)和口碑承攬業(yè)務(wù),靠扎實(shí)的高質(zhì)量服務(wù)實(shí)現(xiàn)與上市公司的共成長(zhǎng)和“雙贏”。中介服務(wù)機(jī)構(gòu)在面對(duì)上市公司涉嫌違法違規(guī)甚至是犯罪的要求時(shí),要敢于說“不”。不敢說“不”,可能會(huì)暫時(shí)幫你拿到業(yè)務(wù),實(shí)現(xiàn)盈利。但此舉可能會(huì)助長(zhǎng)上市公司放棄底線,走上違法犯罪的不歸路,而中介服務(wù)機(jī)構(gòu)作為合謀與幫兇也會(huì)被問責(zé),嚴(yán)重時(shí)候可能會(huì)面臨滅頂之災(zāi)。
此外,當(dāng)好醫(yī)生,及時(shí)為上市公司診病療傷,保證上市公司健康高效運(yùn)行。為上市公司提供服務(wù)的同時(shí),中介服務(wù)機(jī)構(gòu)有更為便利的條件了解“真實(shí)的上市公司”,此時(shí),要積極向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灌輸“依法合規(guī)”的經(jīng)營(yíng)理念,從潛移默化中消除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心中的“雜念”;要敢于對(duì)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的董監(jiān)高的違法違規(guī)決策提個(gè)醒,甚至是拒絕提供放棄底線的服務(wù);發(fā)現(xiàn)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以及經(jīng)營(yíng)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風(fēng)險(xiǎn)隱患,要善于向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進(jìn)“忠言”,在關(guān)鍵時(shí)刻拉人家一把,不讓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乃至其董監(jiān)高因此而墮入被法律追責(zé)的深淵。幫人就是幫己,如果上市公司及其大股東能夠及時(shí)了解到中介服務(wù)機(jī)構(gòu)的善意,那么合作前景會(huì)更廣闊,口碑效應(yīng)會(huì)幫助中介服務(wù)機(jī)構(gòu)拿到更多的業(yè)務(wù)份額,何樂而不為?
當(dāng)然,中介服務(wù)機(jī)構(gòu)要努力為上市公司治理增添正能量,不僅要在跟上市公司打交道時(shí)來做,還要增強(qiáng)主觀能動(dòng)性,多學(xué)習(xí),多向自身的行業(yè)主管部門和證券監(jiān)管部門匯報(bào)溝通,熟悉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和大政方針,不至于因?yàn)樽陨淼臒o知和懶惰,在服務(wù)上市公司時(shí)被動(dòng)觸雷,在嚴(yán)重影響上市公司治理甚至是健康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把自己的飯碗砸了。那樣的話,有點(diǎn)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