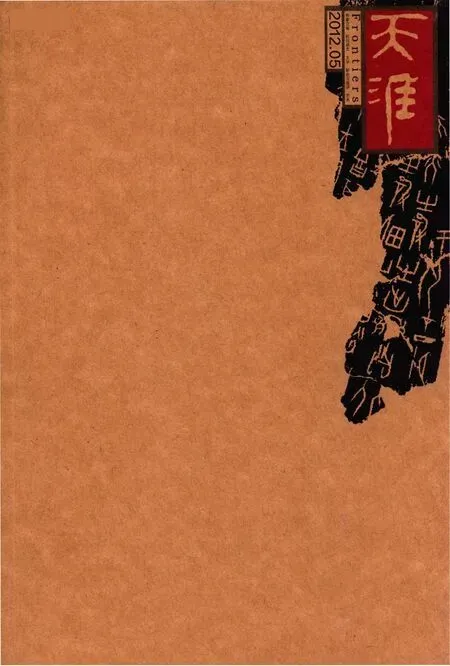當代藝術、倫理政治與社會主義認同
魯明軍
當代藝術、倫理政治與社會主義認同
魯明軍
當代藝術在西方的濫觴與新左翼運動的興起是息息相關的,這使得當代藝術及其種族、階級、性別等意指自然地具有一種意識形態功能。然而在中國,不論從1980年代還是從1990年代算起,當代藝術的興起與社會主義運動似乎并無直接的關系,至少社會主義不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直接推力,某種意義上,它所抵抗的對象恰恰是(中國)社會主義,也由此常常被賦予一種“啟蒙”的意涵和功能。當然,這或許是兩種社會主義的定義分歧,不過這一分歧背后卻共享了一個價值前提,即當代藝術本身作為一種自由、民主之政治表達的通道和出口。
這意味著,重新檢討當代藝術與社會主義認同,不僅是對今日當代藝術中普遍的職業化、策略化、資本化及去我化的反思,更是對可能內在于其中的社會主義認同本身的揭示和檢省。
毋須諱言,社會主義絕非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具有豐富的意義層次和思想內涵,在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中的具體表現也是極為多元和可變。就繪畫本身而言,我們也殊難給予它一個準確的定義。比如在中國,一提起社會主義繪畫,自然想到現實主義,但實際上即便是在毛澤東時代,表面上現實主義占據主導,但我們也不難發現除此之外并不乏其他話語方式與表現風格。問題在于,這樣一種以敘事為主的現實主義風格也不一定源自法國和蘇聯,實際上中國古代繪畫中就有敘事傳統,且此與早期印度繪畫敘事在中國的傳播與交流亦不無關系……等等諸種可能的歷史根源使我們不得不產生疑問,到底誰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呢?在西方、東歐、西歐及美國等區域間的差異也很大,而且冷戰前后的情況也迥然不同。因此,討論當代藝術中的社會主義認同不是重新定義當代藝術,也不是界說社會主義,而是探問和揭示其中可能的復雜面向。盡管如此,我想在此討論社會主義認同定然不是簡單的藝術形式分析,更多是探掘內在于話語方式中的價值訴求和意義指涉。事實證明,今天體現在當代藝術中的社會主義認同亦非形式語言,而多是內在的文化政治所指。
自199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認同、“后革命”反思一直是當代藝術中的極為常見的題旨之一,王廣義的“大批判”、隋建國的“中山裝”、李松松的“廣場”、艾未未的“瓜子”(甚至包括張曉剛的“大家庭”)等都可以被歸結為社會主義認同與反思。栗憲庭、孫振華等已就此做過深入的探討。我們固然可以將此作為視角重新梳理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藝術,我們也承認這一清整本身對于當下而言的確不乏檢討和反省意義。問題在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當代藝術中的社會主義認同是不是過于表面、簡單和過于符號化、臉譜化一點了呢?換句話說,當代藝術對于社會主義的記憶與反思是不是僅只停留在這樣一個層面上呢?除了意識形態之外,日常生活中的社會主義又是如何體現在當代藝術中的呢?
拙文《用具—記憶—藝術:從日常情感到倫理政治》(以下簡稱《用具》)曾以宋冬、趙湘源母子的“物盡其用”和陳彧凡、陳彧君兄弟的“木蘭溪”為對象,基于“用具—記憶—藝術”這一視角,對內涵其中的日常情感與倫理政治進行了探討。兩件作品都是對家族記憶、倫理情感的討論,但是這一認同本身與時代演變的關系并沒有得到有效而深入的思考和揭示。比如“物盡其用”,由于我們太過強調趙湘源對于物的“迷戀”,而忽視了其背后的社會根源。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主義的復雜性呈現了出來。趙湘源之所以收集這些廢棄的日常器具與用品,不僅源自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物質匱乏現實,也與傳統的家族倫理情感與文化認同息息相關。而后者本身也已然成為中國社會主義的一部分(詳后)。陳彧君、陳彧凡兄弟的“木蘭溪”亦然。我想,通過這一討論,或許會為當代藝術、社會主義及儒家倫理三者之間架起一座內在的價值橋梁。
日常情感、倫理政治與當代藝術
在《用具》一文中,筆者對宋冬母子的“物盡其用”和陳氏兄弟的“木蘭溪”兩件作品做過比較詳盡的分析和論述,并將其引至(形而上學)思想史的解釋,但并沒有深入到中國社會主義及其根源。而事實是,他們的創作并不乏社會主義認同。特別是“物盡其用”,直接勾連于社會主義的日常生活與倫理政治。


1.“物盡其用”:日常倫理與情感認同
“物盡其用”是宋冬和母親趙湘源合作完成的作品,作品由趙湘源歷時數十年的幾萬件報廢但沒有被丟棄的日常器具和用品組成,體量龐大,規模甚巨。筆者在此無意對這件作品作詳盡的描述,因為既有的相關研究、述評已經數不勝數。但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從2004年策劃至今,它已歷時七八年,其間的不斷展出及種種發生(比如母親趙湘源的去世)也已成為作品的一部分。看得出來,這是一件簡單、樸素的作品,但所內涵的意義卻又極為復雜而令人糾結。物與人、人與人、人與事等等之間的隱蔽關聯都若隱若現,時明時暗。
在巫鴻先生編著的同題文本封底有這么一段話:
趙湘源是宋冬的母親,像中國千千萬萬勤儉持家的婦女一樣,她保存下來大量的生活用品:化石般的洗衣皂,孩子們的瓶瓶罐罐、鍋碗瓢盆……“物盡其用”是她的人生信條。它承載著人間相濡以沫的痕跡和溫暖,承載了物資匱乏時代對生活的理解與敬重。它是對一個逝去時代的展覽,從北京到光州,從柏林到紐約,無數觀眾默默地流下眼淚,好像突然見到過世已久的親人和摯友。它也是一種默默地收集與保存愛的哲學,頑強地對抗著將置換與丟棄作為基本態度的當下,記錄著中國老百姓對家庭與生活的永恒的愛。
令人感動的是,宋冬始終堅持認為這是他母親趙湘源一個人的作品。誠如他所說的,作為藝術家,母親趙湘源一輩子只做了一件作品,但這件作品她做了一輩子。
在這里,用具建構了歷史,但其并不是僵死、抽象的,它具有可生成性。這意味著此用具已經超越了通常意義上的用具。正是這些用具,重建了個體與生活的關系。或者說,個體因此才真正體認到生活本身。生活之為生活的意義,也因此才得以彰顯。“物”與“用”的同構不僅是對于歷史的尊重,也是對現實的反思,更是對人的日常情感、家庭倫理與共同體紐帶的精神重塑。
2.“木蘭溪”:宗族想象與倫理重建
陳彧凡、陳彧君兄弟倆雖然長期居住在杭州,但對于老家福建莆田的那條河流——“木蘭溪”卻情有獨鐘。裝置“木蘭溪”的創作便源于這份情結。對于兄弟倆而言,沒有什么特別的用意,也沒有打算賦予它什么深刻的觀念,就是想以藝術,甚至只是“以模型的方式搭建一個家鄉的生態空間”,嘗試還原曾經的某個日常生活場景,以使自己能夠“更具體地觸摸記憶的碎片”。在這個意義上,“木蘭溪”儼然是一個“道具”。
然而,事實也沒這么簡單。再造“木蘭溪”背后,彧凡、彧君似乎還是有著更深的體驗和思考。譬如,為什么是“木蘭溪”,而不是其他呢?……我想,這與其說是對于某個記憶碎片的感喟,不如說是通過訴諸“河流”,試圖重新喚起歷史和尋根的自覺。此“木蘭溪”自然不是彼“木蘭溪”。對于藝術家而言,更重要的毋寧是“木蘭溪”這樣一個話語及其生成過程。他們選擇大量廢棄的包裝紙箱(瓦楞紙)、書本、青石粉、木板等作為基本材料,在一個極為簡易的臺子上面,“搭建”起他們的記憶之河——“木蘭溪”。因為河心的“烏篷船”,兩岸的“碼頭”和“閣樓”,“木蘭溪”不再“靜止”。“木蘭溪”已然是藝術家生命中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此時這樣一個場景的復原及其賦予主體的心境和認同。
表面上這的確“復活”了歷史,也“拯救”了記憶,但實際上,它建構和型塑的只是藝術家自身。反過來這也暗示我們,并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自覺。這無疑是一種具有嚴格禮儀規定和倫理基礎的宗族結構的地方性文化心理和自我認同。有意思的是,陳彧凡、陳彧君雖然出生、成長在這樣一個極具地方性的家族中,但上世紀初族內很多親屬因移民馬來西亞,所以,在他倆的經驗和記憶中,不僅銘刻著莆田家族生活方式的印記,還始終存有一份對遙遠的另一半家族——“南洋”的想象。這也告訴我們,為什么他們對“木蘭溪”如此鐘情。顯然,這并非一種簡單的個體性自覺與選擇,而是一種復雜的情感結構和文化倫理認同。
陳氏兄弟并沒有宏大的反思和關懷,某種意義上也是現實迫使他們作出這樣的選擇。對于他們而言,只有一個目的,回到真實的自己,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而不再是不斷地被他者化,被異域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兄弟倆與宋冬、趙湘源母子有著共同的倫理自覺與價值訴求。
意識形態之外:誰之社會主義?
誠如前文所言,今日之當代藝術對于社會主義的自覺與反思某種意義上還停留在臉譜化、符號化的表層,而沒有深入到社會主義本身的內在肌理。我想,我們在檢視和追問當代藝術中的社會主義認同前,有必要澄清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誰之社會主義兩個基本問題。于此,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的論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視角和框架。
長期以來,討論中國社會主義,總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框架之內。我們習慣以“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實際運用”來解釋,并由此創立了毛澤東思想。于是,社會主義在中國自然地成了中國式社會主義。然而,在溝口雄三看來,“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完全不同,它不是發生于資本主義的成熟階段,而是產生于資本主義尚未成熟的時候,它不是以工廠的工人而是以農民作為革命的動力的”。基于此,他提出:
正是在中國強有力伸展著的相互扶助的社會網絡、生活倫理以及政治理念,才是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就是說,社會主義機制對于中國來講,它不是什么外來的東西,而是土生土長之物;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在使這些土生土長之物得以理論化的過程中,或在所謂階級斗爭理論指導下進行革命實踐的過程中,起了極大刺激作用的媒介而已。
這的確是一個大膽的結論,但我想,它絕非溝口雄三先生對于傳統中國想象的率性之言,其中隱含著他長期關于中國歷代社會、政治、文化與思想演變的深入考察和研究。
實際上,對于這樣的結論,我們在政治、社會維度上并不難得到解釋。秦暉在反思辛亥革命時也曾提出其到底是“改朝換代”還是君主和平立憲的質疑。他說:“辛亥的局面其實完全可以用傳統的邏輯來解釋,倒是君主立憲與我們的真實傳統嚴重相悖。”社會主義亦然。在《土地改革=民主革命?集體化=社會主義?》一文中,秦暉便曾尖銳地指出:為什么崇尚“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農業中不乏虎虎有生氣的合作化(乃至“集體化”),而全力倡導集體主義精神的社會主義政權以及民粹派“村社社會主義”者卻反而把合作化弄成了梗喉的魚骨,使人欲吐不能?與秦暉的論述相對的是甘陽的“通三統”,他認為從晚清以來所謂的傳統瓦解,到政治社會革命和改革開放,整個過程實際上可以看成是尋求奠定現代中國的一個連續統。特別是對于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建設,則予以了全新的解釋,重新確認了其對于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基礎意義。……可見,雖然今日之左派(甘陽)、右派(秦暉)對于社會主義的立場和態度不同,但對于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認識本身還是不乏共識,雙方一致認為此社會主義并非馬克思主義所謂的社會主義,而更多源自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傳統。
在政治維度上,社會主義與古代傳統不乏連續性,但社會主義革命對傳統倫理文化的破壞也是歷史事實。或許正因如此,民眾反而對傳統文化倫理(比如宗族、家庭)更為自覺。在這種反向的推力之下,這種傳統的日常情感并沒有被瓦解,而是潛在地得以持續生長。當然,我們并不能否認傳統倫理文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沖突與張力。這一點其實也體現在當代藝術作品中,比如本文所針對的兩個個案:宋冬、趙湘源母子的“物盡其用”與陳彧凡、陳彧君兄弟的“木蘭溪”便是。在這兩件作品中,雖深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痕跡,但支撐話語的還是內在于其中的日常情感、家族記憶與倫理認同。實際上,之所以強調這樣一種自覺,也是為了走出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從而回歸日常生活及其情感結構。唯其如此,才能真正體認生活本身及人之為人的意義。何況,這樣一種自覺本身也是對缺乏血肉感的意識形態之功能性主導的一次深度檢討和反省。
對于“物盡其用”而言,盡管廢品與用具的收集源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年代日常物質的匱乏現實,這樣一個背景促使了趙湘源去收集這些用品,對她而言,這一日常行為的理由非常樸素而簡單:只是擔心物質的匱乏,以備將來繼續使用。在這里,這些廢棄物品和用具的原初功能已消失殆盡,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樣一種行為本身所內涵的日常情感與倫理意義反而得以彰顯。特別是在今天這樣一個物質過剩的年代,重新檢討這些廢棄物所承載的生活之道尤具歷史與現實的針對性。它不僅意在促使我們重新認知歷史,體味記憶,也不斷地提醒我們直面現實,重建倫理政治。換句話說,這不正是社會主義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的隱性介入嗎?
不同于“物盡其用”的是,陳彧凡、陳彧君兄弟的“木蘭溪”并非直接源自社會主義經驗。但“木蘭溪”所負載的宗族倫理和共同體紐帶重建的意義,實際上又不得不回到西方現代化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對于宗族的破壞和損毀。或許,正是這種外在的瓦解反而促使后世不斷地付諸相應的檢討、反省及重建的努力。因此,這與其說是傳統與現代之別,不如說是傳統倫理政治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之爭。

當我們從政治意識形態中走出,回到日常生活及其倫理政治時,自然會對中國當代藝術中的社會主義認同生成新的認識。我們不能肯定社會主義意識普遍滲透在中國當代藝術中,但可以肯定的是除了政治意識形態主導的“大批判”、“中山裝”等之外,還有基于日常倫理和家族記憶的“物盡其用”和“木蘭溪”。如果說前者更多是一種外在的形式認同的話,那么后者則已然滲透在話語的內部與深處。
阿甘本曾說:“當下的進入點必然以考古學的形式出現;然而,這種考古學不向歷史的過去退卻,而是向當下我們絕對無力經歷的那個部分的回歸。”據此我想,宋冬、趙湘源母子也好,陳彧凡、陳彧君兄弟也罷,實際上都是以一種考古學的方式回歸他們無力經歷的那段去經驗化的“幼年”生活。換言之,對于他們的作品,我們也須以視覺考古學的方式進入,單純的形式分析和圖像解釋都很難進入到其內在的話語結構與認同層次。
“經驗的毀滅”與“剩余的時間”:何為當代藝術?

如前文所言,反思當代藝術與社會主義認同,一方面是基于當代藝術的視角重新思考中國社會主義及其思想根源,另一方面則通過重思社會主義認同,進一步對于當代及當代藝術本身有所檢討。我們并不難發現,內在于當代藝術中的社會主義認同實際上是一個關于經驗的問題。那么,當代藝術與經驗到底是什么關系呢?
學界通常認為當代藝術是反經驗(歷史)的或超越經驗(歷史)的一種實驗性的話語方式。這當然是一種普遍的觀念和認識。實際上,丹托早已深刻地意識到,繪畫與歷史的落幕則意味著當代藝術必須從歷史敘述中解放出來,從而走向一個多元與開放的視域。阿甘本主張以考古學的方式介入也是因此之故。而事實業已證明,本文所討論的這兩個個案也殊難在藝術史的維度上得到相對恰切的解釋和定位。甚或說,當代藝術原本就與藝術史無涉。
表面上,“物盡其用”中的社會主義認同是非常經驗化的,甚至令不少人誤解為現實主義。然而,簡單的表層意指背后隱含著復雜的認同與思想層次。
其一,“物盡其用”盡管具有社會主義意指,但作品本身則生成于資本和消費(或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日常私人化的廢棄物收集這一社會生活經驗顯然悖離了當下生存經驗,但是它從另一個視角則恰恰觸及了當代人的記憶與情感神經。可見,一方面它在社會經驗之外,另一方面它又深深植根于經驗。
其二,“物盡其用”看似更像是趙湘源作品,但作者還是宋冬。對于宋冬而言,事實上這些器具、用品無疑皆在(所能體認的)生活經驗之外,至少在這件作品之前,他的日常生活中即便物理事實存在,也不具有經驗意義上的位置。恰恰是通過藝術創作,使得他重返歷史與經驗之外的真實生活。
其三,在這件作品中,觀看者無疑也是作品的一部分。對于觀看者而言,特別是對于不同年齡階層的觀看者而言,因為經驗迥異,面對這件作品時的反應也不盡相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對于這樣一個龐大的日常生活與歷史記憶的空間,很多人還是頗感陌生,毋寧說,即便個別用具“似曾相識”,但整體而言還是經驗之外的一種真實呈現。
可以說,除了趙湘源之外,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如此龐大的日常器具和用品收藏都是經驗之外的實踐。而這樣一個藝術再造(集中在美術館展出)更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之外,或者說它已然超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反過來,它以一種他者的眼光在凝視著我們的生存現實。這的確更像是阿甘本所謂的經驗與歷史之外的幼年生活。廢棄物貫穿了宋冬的成長過程,即便很多用具與宋冬曾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也不在他的歷史經驗中。或言之,正是生活本身讓他不得不無知于這些真實經驗。
回過頭看,社會主義是宋冬這一代人成長中不可或缺的經驗,他們本身便成長于中國社會主義的演變和發展中。然而,事實是社會主義更像是他們經驗之前的經驗,這些社會主義的遺產雖然與他們自身內在相關,但他們自始至終并不自覺,或被排除在他們的生活經驗之外。因此,我們今天所謂的倫理政治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只是幼年的發生和存在。特別在今天,對于他們所熟知和常常體認的經驗而言,社會主義恰已遠離了歷史和現實。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所內含的烏托邦性質本身便具有經驗與歷史之外的“幼年”意義。或許,這是社會主義與當代藝術之間最隱匿、但也是最直接的關聯所在。
無獨有偶,對陳彧凡、陳彧君兄弟而言,亦復如此。其實,“木蘭溪”只是他們幼年的生活方式,并不是他們成長歷史中的經驗存在。因為長大后,“木蘭溪”淡出了他們的生活實踐,反而可能成為認識經驗和成長歷史的一部分。所以直到意識到生活中還有一個時間維度存在時,“木蘭溪”才真正進入了他們未來的經驗。或許,作為藝術的“木蘭溪”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唯一觸及生命經驗的通道或出口。
當然,“木蘭溪”無法等同于社會主義,但“木蘭溪”背后的倫理政治所指不可避免地含有社會主義的痕跡。由此,我們亦可以認為“木蘭溪”具有社會主義所指,而這一所指與其能指的同構實即陳氏兄弟的幼年——即經驗與歷史之外的——生活。對于他們而言,“木蘭溪”恰是時間之外的時間或成長之外的成長,亦即阿甘本所謂的“剩余的時間”之表征。
在這個意義上,到底何為當代,何為當代藝術呢?在權利政治和資本主義大行其道的今天,倫理政治也好,社會主義也罷,似乎都顯得不合時宜,這意味著它已然不在其中的經驗與歷史中。共時性現實已經暗示了真正當代或許是唯一“剩余的時間”,亦即幼年的生活。它被懸置于歷史與現實的經驗之上,并反過來以冷峻的眼光凝視著這個破碎而又晦暗的歷史與現實表層。誠如阿甘本所說的:“當代人不僅是一個感知現時之黑暗,領會一種注定無法抵達之光明的人;當代人同樣是一個劃分并篡改時代的人,他能夠改變時代并將它投入到與其他時代的關系中。”因此,“當代人是一個堅守他對自身時代之凝視的人,他堅守這種凝視不是為了察覺時代的光明,而是為了察覺時代的黑暗”。巴特總結了這個答案,“當代的人是不合時宜”之人。一方面,他與時代保持著一種獨特關系,它既依附于時代,同時又與時代保持距離。可見,所謂的當代藝術既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時間界定,亦非簡單的價值判斷,而是內在于基于經驗之體認與反思的非經驗或超經驗的話語生成,毋寧說這是一種去目的化的凝視的政治。
社會主義認同與藝術的倫理政治
盡管本文將中國當代藝術中的社會主義認同置于日常倫理的層面,但此并不否定意識形態的一面;盡管筆者強調其中傳統儒家倫理文化傳統的一面,但并不否認馬克思主義對它的深刻影響。我想,更重要的是呈現其內在的復雜關聯及其張力。何況即使在馬克思主義這里,也沒有否認道德與精神。誠如伊格爾頓在其引起極大爭議的新著《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的結論中所說的:
他(馬克思)比右翼保守主義者更敵視國家機器,并把社會主義視為民主的深入,而不是民主的敵人。他心目中美好生活的模型基于藝術自由表達的理念之上……
他沒有盲目崇拜物質生產。相反,他想要盡可能地廢除物質生產。他的理想在于休閑而不是勞動。如果他不屈不撓地關注經濟問題,那不過是為了削弱經濟對人類的控制力。他的唯物主義思想與人類秉持的道德和精神理念完全相符。
事實上,即便是討論倫理政治,也不能回避政治意識形態的背景。而今,面對這樣一個問題,不論內在的反思,還是自我的焦慮,它既是一個思想史的疏解和探問,也是一次深刻的現實拷問和檢省。這樣一個反思也告訴我們,當代藝術不僅是一種時間政治,也具有一種倫理政治的可能。
阿倫特亦曾告訴我們,政治產生于人和人之間,它是作為關系而成立的。而家庭之所以取得根深蒂固的重要性,是因為家庭是這個陌生荒涼世界中的庇護所,有力的城堡,保護我們希望帶到這個世上的親人。現代政治摧毀了家庭,表面上給予了所有人以立足之處,即所謂的權利與自由,可是政治闕如的自由,最終則失去了生命本身,乃至自由本身。生命的基礎是如何與他人一道自由地共存于這個世界,而政治的意義在于如何使這種自由共存成為可能。因此之故,“政治不是手段”,而“一直是復數人類永不止息的努力,努力共同生活、共享世界,并相互保證彼此的自由。或許它可以再度如此。這就是政治的承諾”。在這個意義上,家庭或許消解了政治的復數性,但是它所具有的倫理意涵超越了家庭這個空間從而使政治回到政治本身,使僅只作為權利的政治重返作為倫理的政治。倫理政治才是真正的政治。而這也是當代藝術的政治意指本身。
魯明軍,學者,現居四川。主要著作有《藝術·反藝術·非藝術——一個社會學的進路(上、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