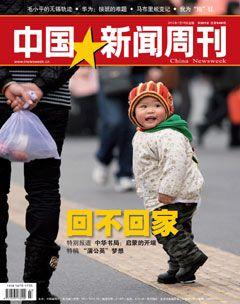誰在感動(dòng)中國
徐智慧

時(shí)光流逝不易察覺,央視《感動(dòng)中國》走到了第十個(gè)年頭。十年前主持人是白巖松和敬一丹,今年還是他倆。白巖松說:“十年前我只是姓白,頭發(fā)還沒白,現(xiàn)在一半都白了。”敬一丹則說,“這是一個(gè)跟好人的約會(huì),已經(jīng)約會(huì)了十年。”
《感動(dòng)中國》每年新春正月播出,跟春晚沒隔幾天,一年只播一期,卻意外收獲了巨大成功。原因何在?在這個(gè)商品社會(huì)肆意咀嚼了30年,信仰缺失、價(jià)值觀淪落的時(shí)代,人們需要這樣一個(gè)節(jié)目,也許就像溺水者需要有人援手拉一把。
這個(gè)超越了國家、民族和意識(shí)形態(tài),關(guān)注人性閃光的節(jié)目,因何會(huì)擁有打動(dòng)人心的力量?
“感動(dòng)”誕生
2002年的一天,北京羊坊店路央視新聞中心評論部一間辦公室內(nèi),十幾個(gè)人正煙熏火燎地開策劃會(huì)。
時(shí)任評論部主任梁建增想做一個(gè)年度新聞人物節(jié)目,遇到一個(gè)困惑,若評年度新聞人物,必須包含胡長清,他是第一個(gè)因貪腐被處決的副省級(jí)高官。但又怕觀眾不能接受把一個(gè)負(fù)面人物評為年度新聞人物。
評論部副主任陳虻提出,做一個(gè)主題性的節(jié)目,既能把正面人物放進(jìn)來,同時(shí)又把負(fù)面人物排除在外。在參加策劃會(huì)的白巖松看來,《感動(dòng)中國》的第一個(gè)火花就此誕生。
在隨后探討中,節(jié)目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既然叫《感動(dòng)中國》,就得提煉“感動(dòng)”的特質(zhì),最后定為:打動(dòng)人心的人格力量。
打動(dòng)人心的力量無所不在,這就要把“地位、職業(yè)、財(cái)富、影響力”這些外在因素排除掉,直指人心。有些人很草根,并不是一貫英雄偉岸,但關(guān)鍵時(shí)刻挺身而出,人性突然燦爛,這就是《感動(dòng)中國》要尋找的人。
他們找到了張前東,這個(gè)四川礦工在已經(jīng)脫險(xiǎn)的情況下,轉(zhuǎn)身又回到塌陷的井下,帶領(lǐng)63位礦工兄弟走出洪水倒灌的巷道。
在制片人朱波看來,這不同于以前“高大全”的先進(jìn)人物,張前東平時(shí)是一個(gè)普通礦工,放在人堆里都找不到,但危急時(shí)刻人性光輝一閃光,便足以照亮人們的心靈。
還有中央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的研究員劉姝威,這個(gè)經(jīng)濟(jì)學(xué)者僅僅寫了一個(gè)600字的內(nèi)參,揭露上市公司藍(lán)田股份的資金騙局,給自己引來了訴訟和死亡威脅。劉姝威當(dāng)選第一屆《感動(dòng)中國》人物時(shí),也有爭議,有人覺得,她不就是寫了篇文章嘛,怎么感動(dòng)中國了?朱波則認(rèn)為,一個(gè)知識(shí)分子,勇于揭露騙局,代表了社會(huì)主流價(jià)值觀,值得鼓勵(lì)。
金庸先生在一次記者會(huì)上提到劉姝威,說她是當(dāng)代中國的俠女。“不是拿刀劍的才叫俠義,拿起筆來主持正義也是俠義。”
《感動(dòng)中國》原本準(zhǔn)備在東方時(shí)空早間節(jié)目播出。第一期片子做出來后,時(shí)任新聞中心主任李挺先審片,看完一抹臉上的淚,對朱波說:“這么好的片子,放在早間播可惜了,讓臺(tái)里領(lǐng)導(dǎo)們看看片,爭取放在晚間黃金時(shí)段。”
于是,這個(gè)時(shí)長2小時(shí)的節(jié)目被改在央視一套晚間黃金時(shí)段播出,同時(shí),新聞聯(lián)播做預(yù)告,《焦點(diǎn)訪談》做專題,央視能提供的最好資源全都給了,片子還沒播出,就得到了超常規(guī)的優(yōu)待。
人性之光
《感動(dòng)中國》成功了,公眾反響之熱烈讓制作團(tuán)隊(duì)大感驚訝,但也給他們增加了無形的壓力。
節(jié)目一年年做下來,最大的難題倒不是尋找人物,而是在人物類型上有所突破。這既是觀眾胃口的需要,也是這個(gè)節(jié)目重塑時(shí)代價(jià)值觀的內(nèi)在需求。制片人朱波為此頗費(fèi)腦筋。
“愛崗敬業(yè),有重大貢獻(xiàn),以一己之力推動(dòng)社會(huì)公平正義”,這些評選標(biāo)準(zhǔn)不可動(dòng)搖。朱波覺得還可以突破。而宏揚(yáng)傳統(tǒng)美德和良好社會(huì)風(fēng)尚,在人物選擇上難以求新。
一天,他們看到了一則捐腎救母的新聞,朱波眼前一亮。山東棗莊人田世國,給患尿毒癥的母親捐了一顆腎,為防母親擔(dān)心,還想法設(shè)法瞞著她。
“每年有很多捐腎的報(bào)道,多是大人捐腎救孩子,孩子捐腎救母,還是頭一次聽說。”傳統(tǒng)美德,百善孝為先,朱波和策劃一合計(jì),就把他列為候選人上報(bào)了。
更大的突破,來自一個(gè)名叫尾山宏的日本人。尾山宏是日本著名律師,代理中國戰(zhàn)爭受害者向日本索賠,從1963年起,參與了近四十年來所有的對日訴訟案件。他還多次自掏腰包將中國受害者接到日本東京出庭。尾山宏的舉動(dòng)觸怒了日本國內(nèi)右翼勢力,多次受到恐嚇。
在一次匯集央視新聞中心精英的策劃會(huì)上,《實(shí)話實(shí)說》制片人海嘯推薦尾山宏。朱波表示反對,中國人還沒選好,倒選一個(gè)日本人。海嘯說,“你太狹隘了,尾山宏為了中國人利益,頂著‘日奸的罵名,這樣的人不能感動(dòng)中國?”朱波調(diào)閱了尾山宏的所有資料,看完后感慨,這老爺子真不錯(cuò),這個(gè)獎(jiǎng)應(yīng)該給。
尾山宏來中國領(lǐng)獎(jiǎng)時(shí)發(fā)生了一段小插曲,同年獲獎(jiǎng)的還有楊利偉等名人,當(dāng)他們坐在休息室里等候錄節(jié)目時(shí),進(jìn)來幾個(gè)年輕人,向尾山宏鞠躬,感謝他為了正義而奔波。尾山宏說,我不僅是為了中國人,也是為了日本人,為了人類正義,如果日本人拒不認(rèn)錯(cuò),忘卻歷史,對日本民族的未來沒有好處。
尾山宏的入選,讓《感動(dòng)中國》人物評選打破了國別、地域限制,更重要的是,讓這個(gè)節(jié)目的價(jià)值觀突破了國家、民族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局限,升華到人類正義的高度。2009年,他們再次把德國人薩布利亞·坦貝肯選為《感動(dòng)中國》人物。這個(gè)盲人姑娘騎馬穿越西藏,第一個(gè)開發(fā)出藏語盲文,創(chuàng)辦盲童學(xué)校,給西藏盲童帶來知識(shí)之光。
“打動(dòng)人心的力量”,說到底就是提供什么樣的價(jià)值觀,給社會(huì)提供什么榜樣。
節(jié)目開播的幾年,《感動(dòng)中國》欄目組致力于糾正錯(cuò)誤、扭曲的價(jià)值觀:為搶救電線桿付出生命的大學(xué)生得不償失,賴寧一樣的救火少年不值得鼓勵(lì)。通過回歸人類普世價(jià)值,讓《感動(dòng)中國》的人物不僅被中國人民接受,也被世界人民接受。
不同于純粹宏揚(yáng)主旋律的作品,《感動(dòng)中國》處處閃著人性之光,感動(dòng)每個(gè)心存善意的人。
不僅如此,照看留守兒童的教師、艾滋病人義工的入選,體現(xiàn)了他們對社會(huì)缺憾、不公的思考。一次做完節(jié)目后,《中國青年報(bào)》總編陳小川打電話給朱波,稱贊他重塑了中華民族的價(jià)值觀,既有傳承,又有新的倡導(dǎo)。
在這一點(diǎn)上朱波很自信,“中國人的價(jià)值體系是怎樣的,在每一年的《感動(dòng)中國》都有體現(xiàn)。”《感動(dòng)中國》也許不像剛開播時(shí)那樣讓觀眾震撼,但這也說明,社會(huì)更寬容、理性、進(jìn)步,以前特別感動(dòng)的人和事,觀眾習(xí)以為常了。
“如果有一天,人們不再看《感動(dòng)中國》,說明已經(jīng)世界大同,人們不再需要榜樣了。”朱波半開玩笑地說。
感動(dòng)自己
《感動(dòng)中國》開播兩年后,各省開始效仿,推出《感動(dòng)湖南》《感動(dòng)湖北》等節(jié)目。
一次欄目組開會(huì),有人在白板上寫下“一直被模仿,從未被超越”相互激勵(lì)。七八年過去,白板跟著欄目組搬家數(shù)次,上面寫過無數(shù)方案,惟有這行字,從未被擦掉,已經(jīng)成為《感動(dòng)中國》欄目組的一個(gè)符號(hào)。
同樣保持不變的,還有一個(gè)幾乎沒有變化的欄目組。9年來,制片人一直是朱波,主持人是敬一丹和白巖松,總導(dǎo)演樊馨蔓除了有一年因身體不適退出外,其余8年一直擔(dān)綱“導(dǎo)筒”。甚至燈光、舞美、包裝、錄音等技術(shù)工種,9年來也一直沒有換過。每年一到10月份,他們就知道,朱波的電話該打過來了。
這個(gè)超級(jí)穩(wěn)定的制作團(tuán)隊(duì),在央視非常罕見。
《感動(dòng)中國》籌備制作最緊張的年底,同時(shí)也是商業(yè)演出市場最火的時(shí)候,晚會(huì)一臺(tái)接一臺(tái)。但當(dāng)商演和《感動(dòng)中國》相沖突時(shí),外請的燈光師會(huì)毫不猶豫地推掉商演,有一年,燈光師為此推掉了上百萬元的大型商演合同。而《感動(dòng)中國》給音樂、燈光開的價(jià)格,往往遠(yuǎn)低于商演價(jià)格,但他們都樂意接受。
這讓朱波很感動(dòng),“大家都認(rèn)為這臺(tái)節(jié)目有價(jià)值,有意義,值得干,就算經(jīng)濟(jì)上有損失,也不在乎。”
這臺(tái)節(jié)目首先要保證真實(shí),都是真人真事,獲獎(jiǎng)人物到北京錄節(jié)目時(shí),接待人員只能跟他們敘幾句“北京冬天習(xí)不習(xí)慣”“衣服夠不夠”之類的寒暄,與節(jié)目有關(guān)的話題一概不能談。樊馨蔓每次都叮囑工作人員,最多只能讓獲獎(jiǎng)?wù)呱吓_(tái)走走位置,不能泄露跟節(jié)目有關(guān)的信息,讓他們上臺(tái)自由發(fā)揮,錄制時(shí)一條過,不允許失敗,不能重來。
“跟別的節(jié)目不同,《感動(dòng)中國》的錄制,是按照紀(jì)錄片的模式做的,我們只是記錄現(xiàn)場發(fā)生的故事,原則只有一個(gè),保證真實(shí)。”樊馨蔓說,錄制這臺(tái)節(jié)目,需要十臺(tái)攝像機(jī)天衣無縫地緊密配合。要保證現(xiàn)場不發(fā)生失誤,就要預(yù)先進(jìn)行大量模擬,工作量十倍于平常。“每次一錄完,攝像師、導(dǎo)播都像做了一次減肥運(yùn)動(dòng)。”
《感動(dòng)中國》因其真實(shí),打動(dòng)人心,同樣把這個(gè)團(tuán)隊(duì)凝聚在一起。《感動(dòng)中國》首先感動(dòng)了制作團(tuán)隊(duì),所以觀眾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一臺(tái)充滿敬意的節(jié)目,看到的是去除虛飾的白巖松和敬一丹。
每次來到《感動(dòng)中國》錄制現(xiàn)場,白巖松會(huì)卸除主持人身份,以一個(gè)有血有肉的人的身份參與節(jié)目。“累,當(dāng)然會(huì)累。掉眼淚不累嗎?”他說。但他堅(jiān)持職業(yè)新聞人準(zhǔn)則,在舞臺(tái)上做自己該做的,不許掉眼淚。他說自己的淚,在事先看片子時(shí)已經(jīng)流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