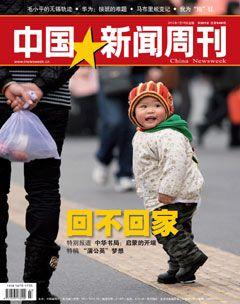百年書局的當代生存
萬佳歡

2003年左右,中華書局陷入真正的經濟困頓之中。這個在知識界評價極高的出版社必須考慮向市場轉型。他們最終決定把一部分出版物的讀者群從知識精英拉回至普羅大眾。借由與閻崇年、于丹等“學術明星”們合作的“解讀經典”式圖書,這家專業的古籍出版社成功自救。
雖然并不是以徹底放棄古籍和經典出版為前提,但中華書局這些“輕啟蒙”式的延伸出版物還是遭到種種非議。一些人認同中華書局的品牌以及他們的市場化嘗試;而另一些人至今仍然將此看作百年書局墮落的標志。
“就像穿著長衫去跑步”
1997年,面對入不敷出的現實,中華書局決定做最容易賺錢的教輔書,甚至時尚、旅游類圖書。但這些探索紛紛以失敗告終,畢竟這些領域與書局古籍出版的主業相距得太遠。“賠得很厲害,”中華書局大眾圖書分社社長宋志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往市場走的路上,我們是吃了不少虧的。”
轉型的失敗讓書局員工徹底失望,從1997年開始的6年時間里,全書局100多員工中有將近一半選擇了離開。
2003年,中華書局新一任領導層上臺,決定將古籍學術著作和面向市場的大眾類圖書同時提上日程。
次年3月,“大眾讀物工作室”成立。出版社內部的一些員工覺得之前就“改革來改革去”,已經“習慣了”;另一些人則持反對意見——很多一直做高端學術類書籍的學者都恥于言利。
而彼時的中華書局經營負債累累,大批庫存圖書積壓,100余名離退休人員需要養活;在崗編輯每月平均工資不到兩千元。用宋志軍的話說,當時的中華書局已經“到了底”, “如果不改,就是死路一條”。
“要面向市場,最大的困難在于轉變中華書局固有的觀念,如何統一掙錢和保持品牌、品質的關系,”書局副總編顧青對《中國新聞周刊》感慨,“這點是真難。”
大眾讀物工作室在爭議聲中成立起來,成員只有宋志軍等四五個年輕人。部門設定的方向是面對大眾做普及讀物。但究竟做什么,大家也心里沒數。
彼時,《百家講壇》也正開始轉型,借由閻崇年的講座,收視率節節攀升。
宋志軍看著閻崇年站在一個講臺后面用文白夾雜的話語和懸念迭出的小節設計重述“清十二帝疑案”,他覺得自己也許找到了一個方向:我們為何不以“正說”歷史的概念,與閻崇年合作出書?
宋志軍找到欄目組和閻崇年,合作很快談妥,圖書定名為《正說清朝十二帝》,首印數五千本——對于中華書局來說,這個有些可憐的數字已然是邁向市場的印量。以前,中華書局學術著作的印量只有兩三千冊。
而反對聲又開始了,比如是否在書上加腰封。很多人認為,充斥著夸張推薦語的腰封會被讀書人恥笑。
“這種老社走市場化道路,就像穿著長衫的人要去運動場上跑步,”宋志軍做了個比喻,“市場意識很不足”。
從書的開本大小到版式設計,他完全不知道影響銷售的因素是什么,只能一點點摸索。他擔心書局內部的美編還會把書做成老樣子,于是去外面找美編。為了趕上2003年國慶長假銷售季,這本書不再使用單位里的錄排室,成為中華書局第一次走出去找排版公司的項目,大大縮短了出版時間。
宋志軍事后總結,這本書之所以能做出來,除了領導開明,還因為自己自2001年入社三年來,從未做過責任編輯,“是一張白紙,沒有固有的框框和限制”。
“還有簽售這種東西?”
就連閻崇年本人也沒想到,《正說清朝十二帝》居然會登上暢銷榜,并且成為中華書局市場化嘗試以來的第一本暢銷書。
《正說清朝十二帝》在2004年10月推出后,便迅速在北京秋季地壇書市上大放異彩。宋志軍發現,那點可憐的首印量根本不夠,書局開始以上萬冊的印量連續加印,一個月內加印了五次。
北京市場的火爆引發外地書商緊急進貨。多個城市的書店開始邀請閻崇年去作演講和簽售。“還有簽售這種東西?我們完全不知道。”宋志軍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一下子有了賺錢的書,書局的工作人員都很振奮。但大家都認為這是“天上砸下來個餡餅,運氣好”,并不覺得這樣的成功還可以復制。
有書店的朋友提醒宋志軍:“你們跟得越緊越好。為什么不馬上做‘清朝十二臣?”于是,中華書局的正說歷史系列接連做了十本。依靠這一系列,大眾讀物工作室2005年的發貨碼洋從頭一年的500萬猛增到2300萬。
而與另一個百家講壇“明星”于丹的合作讓中華書局的銷售量再上高峰。
2006年國慶,于丹在百家講壇連講7天《論語》,一舉成名。
于丹“心靈雞湯式”的歷史重讀顯然符合中華書局大眾讀物想要對普通民眾進行“普及化輕啟蒙”的想法。經過協商,中華書局答應首印60萬冊,這家百年老社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之高的首印量。“當時要拍板做那么多是很有風險的。”宋志軍回憶。
11月26日,《于丹〈論語〉心得》首發。于丹在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進行新書簽售活動。活動從下午1點進行到晚上10點半,其間書多次斷貨。事后統計才發現,于丹一共簽了一萬冊,平均一個小時簽一千冊。
一直呆在現場的中華書局副總編顧青也扛不住了。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圖書大廈原來是晚8點關門,不許關。警察在后頭盯著,想撤都撤不了。” 公安局海淀分局的三個副局長趕到現場,對書局人員說,“不簽到最后一個讀者,你們不許走。”
消息傳開,中華書局的訂貨電話幾乎被“打爆”,這本書單月發行126萬冊。
在于丹建議下,中華書局成立了近20人的營銷團隊,主動推廣圖書。在幾十個城市的簽售活動中,處處讀者瘋狂,到每個地方都得先聯系警察局。
《于丹〈論語〉心得》至今銷量已經達到520萬冊,還順利拿到10萬英鎊的英文版稅。
“堅守傳統”的新方式
2007年,中國出版集團內部圖書評獎,評委會針對《于丹〈論語〉心得》發生了激烈爭論,最終無緣獎項。
近些年,連續數本暢銷大眾讀物讓一些人接受了市場化嘗試,但反對意見仍然存在,一些書商和老讀者覺得《于丹〈論語〉心得》這樣的書過于通俗,“中華書局不應該做這樣的書”。好多朋友甚至要跟顧青“絕交”,對他說:“你怎么能做這種書?這是墮落啊。”
面對這些指責,宋志軍曾寫過一篇題為《為快餐加點營養》的文章:大眾需要快餐,我們就只能做;但是有的快餐有蒼蠅,咱們可以給它弄得干凈點,語言材料好一點。
“如今這樣的新時代,生存是第一位的,”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古籍整理和傳統文化的傳承工作需要大投入。沒有飯吃,怎么做事?”
在1997年之前的十余年時間里,中華書局幾乎沒有進過新員工,它試圖以縮減規模、減少支出的方式來堅守古籍整理工作。而書局卻日益陷入困頓,這樣的方式宣告失敗。
“當時有好多古籍項目,根本不敢接,太貴。” 宋志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編輯們只能給外面干活掙錢。”
2003年之后,中華書局開始把自身的定位從“傳承者”擴大為“傳播者”,讀者群也從知識分子,擴大為普羅大眾。“光在象牙塔里,公眾沒反應,也不能實現傳承文明的工作啊。” 顧青說。
除了大眾圖書分社的“講解”類普及圖書,中華書局的普及工作還有一半由“基礎圖書分社”完成。他們將《墨子》《周易》等著作采用文白對照等形式加注出版。
實際上,1990年代初,就有很多人把中華書局整理出來的《二十四史》等古籍翻譯成白話,做成了暢銷書。“我們做了很多艱苦的初步工作,但錢都讓別人給賺了。”宋志軍說。
現在,中華書局古籍出版部門有50多位編輯,這個團隊仍然是中華書局的核心,也是目前投入最大的部門。在銷量方面,古籍出版和大眾出版分別都能貢獻1.5億碼洋,基本可以平分秋色。
無論是古籍整理還是大眾出版,中華書局出版物所依托的資源仍是中國傳統文化。書局曾拒絕出版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書,因為“沒這方面的專業人才”。“我們不會做莎士比亞或者《喬布斯傳》,不會做,也肯定做不動。”顧青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08年以后,“百家講壇熱”逐漸冷卻下來,中華書局開始獨自開發“一本書讀懂”系列。其中《一本書讀懂中國史》每年都有幾次重印。這樣的出版方式既能獲得很好的市場反應,也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對特定作者的依賴。
“如果哪個門類都去做,也許在一定時間內可能可以做大,但別人很容易擊潰你,因為你沒有長項。”宋志軍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不做市場的第一名,但要做中國傳統文化門類里的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