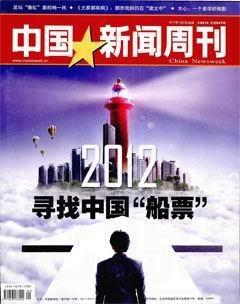文化創意的能量來自內心
賴聲川
近幾年大陸各地都在將古人留下來的一切產業化,不管是房子還是園區,都要變成一個產業。但是忽略了文化的再創性和創意,如何創意、再創是認識本身的事情,不是創意來了就來了。我的行業是劇場,我們每天晚上的演出,臺上演員和臺下觀眾是呼吸同一個空氣,就算有DVD可以回家看,但無法復制看戲的經驗本身。我經常被問的問題是,如何準確猜測市場?
可是,在創意事業中去研究市場,還不如研究自己心中認為什么是重要的。我這句話是針對創作者、創意的人來講。每天研究市場的趨勢,最多是跟風。怎么創造一個市場,這才是文化創意產業最可貴之處。
《寶島一村》是2008年底演出的戲,那是全世界經濟最慘的時候,居然有這么一出戲票房非常好,三年后還是場場爆滿。那時候一些雜志報道了這件事,說在經濟最困難的時期,有少數幾個先知知道市場怎么樣。我看了覺得很好笑,我們怎么知道市場在哪兒?其實我們做文化創意產業,如果想市場在哪里,去追那個市場,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陷阱,因為它是很虛的東西,真正的文化創意產業還是來自創作者本身的內心,那個東西反而是最重要的。
對導演來說,你在關注什么,你的作品就反映出什么。最重要的不是舞臺的燈光、布景、設計,反而是看你懂不懂人,懂不懂各式各樣的人。對人心的理解是導演最重要的功課。
喬布斯說過一句名言:消費者不需要事先知道他們要的是什么。他是針對iPad要上市時記者問的問題—一這么成功的產品你做了什么調研?他說什么調研都沒有做,是我們的工作是來指導他們要什么。我也一樣,你來看我的戲也沒有說事先要知道你看什么,是我給你看什么。
1985年,在臺北,我的劇團第一個作品、我的作品《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是非常實驗性的作品,探討相聲在臺灣的死亡。評論家說,這是用相聲來說相聲的祭文,是實驗性的做法。想不到它得到了巨大的商業市場成功,大到我們自己都想象不到。后來磁帶出了以后,賣了100多萬套,200多萬卷,臺灣只有2000萬人,這還不算盜版的數量,他們說盜版是5倍,我都不敢相信。它成為了當時的一種現象,一個非常實驗性的作品突然之間獲得了巨大的市場成功。
第二年我們壓力更大,我們拿出的作品是《暗戀桃花源》,這個作品一直演到今天。如果25年前你跟我說,你來做一個作品,讓它25年后還在演出,打死我都不知道做什么;如果當時有人跟我說《暗戀桃花源》25年以后還會演出,打死我也不相信。我們只能在那個時空做我們該做的事情。有一個分析告訴你說《暗戀桃花源》可以演25年嗎?完全沒有。完全就是出自我們的創作愿望,演出之后能走多少場戲沒有人知道。最厲害的好萊塢導演也不能告訴你他的電影到底有多少票房。慢慢地在行業里做久了才能有個大概的預測。
前一陣在一個論壇中有機會碰到“文化創意產業之父”約翰·霍金斯先生,聊天中,他跟我透露,“文化創意產業”這個名詞是他當年為他在倫敦的電影公司向英國政府申請一筆贊助款時“發明”的一個名詞。他說,為什么用“產業”這個似乎與“文化”和“創意”不搭調的名詞,是因為用“藝術…‘文化”這一類的詞,說破嘴說了多少年也沒人理會。有了“產業”,政府才可能會重視,而英國政府果然注意了,給了贊助。
于是霍金斯先生創造了一個他自己都說不清的一個名詞,現在這個名詞正在世界各國帶動上千億的投資,是新時代經濟最時髦的名詞。
大部分人對“文化創意產業”這六個字中只重視最末兩字,因為大部分人的目標和理解都在這兩字。只要是產業就能賺錢,只要能賺錢,不明白好像也沒關系。
然而,好的文化創意產品必須是來自文化和創意。好創意、好戲,不是錢可以直接買的。這是了解文化創意重要的一點。很多人堅信人類必須吃飽肚子才有閑情去搞文化藝術。這其實是暴發戶的思維,因為文化人類學早已觀察在人類最早的活動中,藝術本來就是必要的一環。
現在,文化被重視了之后,在各個方面機會真的是來了,而我們有沒有創意的能量來創造市場,怎么發明一些東西讓市場來到我們這邊?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
我一直強調創意是發現,是一關一關地揭露或許原來存在的東西。我認為尋找靈感的過程必須是內在的途徑,而非外在。
可是我們從小被教給不同的方式,被貼了標簽,這些足夠造成每一個屏障阻擋創意的產生。
現代大部分的教育都是在于方法,我們所有的教育都沒有放在智慧方面。如果這兩者必須兼具才能成功的話,顯然我們漏掉了兩個領域中的一個。這個時代已經跟智慧脫節了。在今天,我們過度重視了方法,智慧被遺忘,社會甚至已經沒有辦法定義什么叫智慧。
所以,現在我們的社會所有的教育都跑到了周圍,中心空了,一切都在學方法,可是沒有人在乎給它營養的到底是什么東西?我認為文化創意必須從中心出發,我們必須建立起那個中心來。這個東西是什么,也是非常抽象的,我今天也沒有答案,只是提出我們發現的一個非常奇妙的,在全世界共同的缺憾。
在社會快速發展中,我們得到很多,也失去很多。得到的我們都看到了,失去的傳統、文化,我們卻不容易看到。有時候,對于這種失去,提醒我們的不是社會學家,不是科學家,而是話劇。
我對2012年充滿期待,但也抱有擔心。因為這兩年,話劇變得蓬勃、時髦,許多人于是把它視為可操作的商品,我非常擔心過度的商業化會影響大陸話劇的發展。話劇本來和商業就有交集,但話劇終究是文化,看似蓬勃的話劇市場如果沒有足夠的好創意、好戲來支撐,也無法持續發展;另外,大陸的場地費是全世界最貴的,這不僅把很多觀眾擋在劇場之外,也使得一些小成本話劇的生存十分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