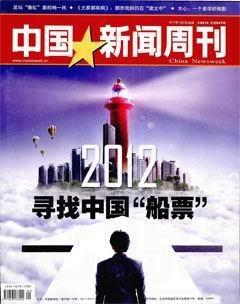教育改革的動力在民間
楊東平
201 1年8月,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播放了一部我擔任總顧問的6集專題片《教育能改變嗎》。這部原本應在一年前國家《教育規劃綱要》頒布之際播放的片子,一年之后才得以播出。但這一提問并沒有過時,它持續地徘徊于每一個人心中,起伏于希望和失望之間,印證著“社會焦慮”這個年度主題詞。令人糾結不已的都不是什么新問題,而且將會繼續發酵升溫,成為今后的教育焦點。
如果說國家關注的教育問題主要是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和引進,是國家競爭力,是“錢學森之間”,那么城市家長擔心的則是兒童的身心健康、沉重的學業負擔、熾烈的擇校競爭、高昂的擇校費這類基本民生。不僅如此,2011年初,美國華裔教授蔡美兒的一本《虎媽戰歌》,使得“中國虎媽”風靡世界。年末,又有鼓吹“三天一頓打,孩子進北大”的“中國狼爸”登場,演繹著一個“如狼似虎”的家庭教育環境。
學校的情況也不妙。佩戴“五道杠”的湖北小學生黃藝博成為“官模官樣”學生的標本。各地頻頻爆出的給差生戴“綠領巾”、給后進學生穿紅校服、讓學生按不同成績使用不同顏色作業本等等給學生貼標簽的行為足以印證扭曲畸形的教育價值觀依然存在。我們已經進入全民教育、大眾化、互聯網的新時代,然而,主流依然是名校崇拜、培養尖子和“精英”、面向少數人的教育。望子成龍、出人頭地之類的陳腐價值,在獨生子女時代和“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商業鼓噪下被前所未有地“洗白”了,從而將眾多兒童逼人“贏在起點,輸在終點”的悲慘人生,甚至過早地累倒在“起跑線”上。
一些農村兒童則直接殞命在上學路上。一個數以千萬計的青少年群體——貧困地區的農村兒童、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迫切需要的仍然是交通安全、營養、健康等基本保障,以及教育機會。“校車”成為一個令人驚駭的詞匯,從此,我們將日復一日像擔心礦難那樣忐忑不安。它所呈現的是農村地區持續十年的大規模撤點并校造成的“上學難、上學貴、上學遠”的惡果,而且不止于校車,還包括輟學率上升、大班額、寄宿制學校等眾多問題。在現代化的名義下,學校被從農村“連根拔起”。農村教育的“空心化”“城市化”和“被城市化”所造成的農村發展的整體性危機,正在浮出水面,亟待認知和破解。
然而另外一些具有轟動效應的教育事態,啟示我們從不同的側面認識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局。
2011年,全國平均高考錄取率達到創紀錄的72,3%,包括山東在內的十多個省市的這一比率已經超過了90%。與此同時,公眾的選擇性明顯增加,越來越多的老百姓開始“用腳投票”,高考棄考人數達100萬,新一輪的留學潮如火如荼。出國留學人數以20%的速率增長,高中出境學習人數已占留學總人數的22.6%。“洋大學”在快速登陸,除原有的寧波諾丁漢、蘇州的西交利物浦、珠海聯合國際學院之外,上海紐約大學已經招生。今后幾年,僅廣東省就將再引進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4所境外大學合作辦學。
這顯示,由于學齡人口大幅減少、政府教育投入大幅增加,教育的供求關系正在明顯改善。中國教育已經超越了極其貧困、極其短缺的階段,處在一個新的轉折點上。今天,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去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我們正處于有“大變革前夜”意味的歷史時機。因此,比“教育能改變嗎”更為深刻的提問,是探索教育變革的動力機制。
中國社會的各種問題都可歸為根本性的體制和政府治理問題。人們熱切期盼《教育規劃綱要》確定的“去行政化”改革早日到來。然而,南方科大改革的一波三折,助長著人們的失望和無力感。毫無疑問,根本解決問題的宏大思路、自上而下的整體性改革都是重要的和值得期盼的;但是,除了單純的批判、抱怨和等待,我們還能做些什么?那樣是不是把自己降低為旁觀者,從而消解了公民的責任?正在發生的另外一些事件,啟示我們去想象教育變革的真實圖景。
由民間愛心人士鄧飛等發起的“免費午餐”公益行動,獲得社會各界的廣泛支持,短時間內籌集資金達兩千多萬,顯示了微博改變社會和公眾參與的巨大力量。這一由民間發動的公益行動得到了政府回應和迅速跟進。10月,國務院決定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每年撥款160多億元,覆蓋680個縣市、惠及2600萬農村學生。免費午餐從民間行為變為政府行為,不僅彰顯著公民社會的真實力量;作為政府和民間良性互動、通過公眾參與改善政府治理的典型案例,也預示了一種促進社會變革的新模式。
如加拿大著名教育家邁克·富蘭撰著的《變革的力量——透視教育改革》所揭示,世界各國自上而下強力推行的教育變革大多是失敗的,轟轟烈烈之后往往無疾而終。因為教育變革是一個非線性的、不穩定的動態過程,其結果是不確定的。因此,我們需要新的思維方式和工作機制。他認為,應“使變革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更多地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改革,而不是靠政府和專家外在的強迫和控制。學習型個人、學習型組織和學習型社會才是推動復雜變革的真正動力,而新思想往往產生于多樣性的文化和在團體邊緣的人。
這一洞見非常新穎而深刻,也和我們在當前的教育生活中所感悟的相同。在我們身邊,正在出現越來越多這種微改革、微創新、微公益的成功實踐,例如,朱永新教授倡導的在全國范圍近千所學校開展的“新教育”實驗,大范圍推廣的李英強的“立人鄉村圖書館”計劃、真愛夢想基金會的“夢想課堂”、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的鄉村幼兒園實踐等等。基層學校的變革,以山東杜郎口中學的改革最為典型,這—在偏僻農村自發開展的學生主體課堂的教學改革不脛而走,影響遍及全國。這種自下而上的、局部的、零散的、個體的、非制度化、非主流模式的自主創新,強調每一個人的學習和參與,體現了去中心化學習模式和“互聯網精神”,不僅是互聯網時代知識生產的模式,也是知識經濟時代社會刨新的模式。
新時代的曙光已經隱約可見。由無數微改變凝聚的公民社會的力量,將會是實現整體性教育變革的基礎性力量。
學在民間,教育因你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