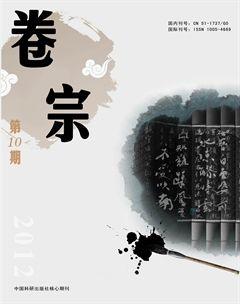刑罰制度對國情因素的理性回應
陳偉媛 賴隹文
摘要:當前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動的轉型期,社會總體上處于失序狀態;民眾樸素報應觀仍然強烈,與現代刑罰目的刑理念產生極大沖突。刑罰制度對國情因素的回應和吸納應以積極因素為限,止于消極因素。立足于刑罰目的,發揮刑罰功能,通過刑罰的合理配置和運用發揮刑法的行為規制和法益保護機能,以維護和穩定法秩序,培養國民的法規范意識,重塑國民失卻的規范信賴感,對于踐行我國刑罰制度的當代使命有著重要意義。
關鍵詞:刑罰制度國情因素刑罰目的刑罰使命
刑罰制度伴隨著人類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逐步擺脫了許多不文明因素和純報復式的非理性因素的主宰,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義和功利主義思想貫穿始終。刑罰是苛酷還是輕緩,一方面取決于特定時期人們對于刑法性質、功能和目的的認識,當然這在根本上又受制于政權的性質和國家觀、權利觀等的影響。建構一種既回應國情因素又能承載起刑罰當代使命的刑罰制度,應是一種優位選擇。
一、影響我國刑罰制度建構的國情因素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并處于急劇城市化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問題都是在建構刑罰制度時不得不考慮的現實側面。主要存在以下三點:
(一)處于轉型期的社會失序
一九九三年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在憲法層面的確立, 我國的城市化進程開始加快。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人口流動增加、資本流動加快、貧富差距加大、城鄉矛盾開始凸顯,再加上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相應的社會保險、福利措施建設的滯后,我國開始進入由鄉土熟人社會過渡到城市陌生人社會的轉型期。近年來,政府公信力尤其是司法公信力的缺失,使得社會矛盾的尖銳程度越來越呈現白熱化趨勢。為此,緩解轉型期的社會問題終究要依靠根本性地解決民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理順權力與權利及義務的關系來實現。面對這種復雜的社會狀況,刑法的法益保護、人權保障和行為規制機能的實現,離不開合理刑罰制度的設置。
(二)法治傳統的缺失
費孝通先生曾言,“人治與法治之別不在于人和法這兩字上,而是在維持秩序時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據的規范的性質。” 我國歷來沒有法治傳統,有法制而沒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這已經是獲得多數人共識的“老問題”。法治傳統在古代中國的缺失,直接塑造了中華民族“輕視法律”的民族性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我國著手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到二零一一年宣布已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在法律體系的完善程度方面跨越了一個階段,但是我們依舊只是一個法治國家而不是法制國家,那么重新審視當前我國司法公信力的缺失、腐敗案件頻出、各種領域的法外潛規則等現實,就不能不讓人產生憂慮。
(三)民眾樸素報應觀與現代刑罰目的之沖突
重刑優于輕刑和殺人償命的的觀念在普通民眾乃至于精英階層都仍處于主導地位。對于這一點,從劉涌案、藥家鑫案、李昌奎案等案件中普通民眾“一邊倒”的輿論攻勢和司法部門對民眾報應心理的迎合就可以得到驗證。非監禁刑之適用除了與制度相關的配套措施的完善外,其獲得民眾的認同和配合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這些都需要民眾摒棄非理性色彩濃厚的樸素報應觀,認識和接納綜合主義中的功利主義理念。
這是刑罰設置和運用不可忽視的因素,而這又是明顯與現代刑罰理念相沖突的消極因素,所以刑罰就不應一味地對其予以回應和滿足。但又如張明楷教授所言:“刑罰程度整體是否適當,必須以本國國情以及本國公民的平均價值觀念為依據進行考慮。” 問題是,如果本國國民的平均價值觀念明顯偏離現代刑罰理念,或者國民的情緒性沖動已經步入非理性軌道時,對刑罰程度適當與否的判斷標準就應該能夠包含一定的引導、糾偏導向和作用,否則刑罰就脫離不了殘酷與野蠻的氣息。
二、刑罰制度回應國情因素的界限
每個國家都有著各自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發展現狀,刑法的制定和實施也是為了在特定共同體內實現社會防衛,在此意義上,刑法必然是涂抹了特定民族、國家色彩的刑法,而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刑法。建構刑罰制度時不可避免地須對特定國情因素進行回應,但刑罰制度建構中是否存在回應的限度?
每個國家都存在扎根自身的特殊國情因素,根據其對刑罰制度的影響可以劃分為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積極因素指的是建構刑罰制度時予以考量可以較好發揮刑罰功能的情狀,是被刑罰制度所關注和吸納后,刑罰制度可以較好地發揮自身功能,維護社會秩序,而又不至于走入偏激道路的因素。
消極因素指的是明顯偏離理性軌道、反映的是民眾情緒化沖動,可能損害刑罰功能和刑法目的的情狀。國情中的消極因素很多,如前文所論述的我國民眾法規范意識不強、情緒化的樸素報應觀過于強烈,以及當前政治體制弊端所導致的系統性腐敗等。這些消極因素對于刑罰的要求將是:由于民眾法規范意識比較淡薄,所以對于法定犯不給予刑罰或者給予較輕刑罰,又或者通過可以重刑以樹立國民法規范意識;由于當前“殺人償命”等的樸素報應觀還很強烈,對于殺人等惡性案件必須判處極刑,否則難以平民憤,社會將會大亂等。由此可見,這些情緒性、非理性和沖動性的消極因素大多是以樸素的感性認識為基礎,過于迷信刑罰的震懾力,缺乏實踐根據和法理基礎。這些因素一旦被刑罰制度所吸收和回應,那么刑罰將淪為沒有自身品格和價值取向的“統治工具”。
所以,刑罰制度制度對國情因素是一種有限度的考量,考量界限應以積極國情因素為邊界,止步于消極國情因素。
三、回歸本質:刑罰制度的當代使命
如前所述,對國情因素的回應限度的差異背后折射的是刑罰理念的不同。而準確把握刑罰制度的理念的關鍵又與對刑罰制度在我國的當代使命的認識息息相關。行文至此,就觸及到了更為深層次的問題,即刑罰制度的當代使命是什么。
對刑罰制度使命的認識,必須以刑罰的功能和目的為基礎。刑罰制度對國情因素的回應是刑事政策的目的設定轉化為法律效力的過程,而這種轉化對于重新樹立社會的是非觀而言都是必要和重要的。 報應是刑罰所固有的內容,它是對社會譴責的聲音和懲罰的訴求的響應,同時也是對這種譴責聲音和懲罰訴求背后的價值觀念的支撐。這些價值觀念雖然存在著與刑罰的人道性、公平性相悖的部分,但是總體上是契合國民倫理和正義秩序要求的。從規范維護的強化的視角審視,刑罰對報應的吸納是刑法對國民相關價值觀念的肯定,認同承載這些價值觀念的社會秩序和倫理,這是刑罰和國民相互溝通的過程,通過兩者的溝通,刑罰不至于偏離社會大眾的基本道德觀念太遠,又使得國民從刑罰制度中領會國家對相應價值觀的維護,進而增強刑罰的國民認同感和適應力由此可見,報應和預防在功能論上殊途同歸,最終都是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穩定、維護和強化法規范。
刑法既要重視對合法權益的維護,又必須肯定規范的重要性,只不過在不同歷史時期側重點有所不同。對犯罪處以刑罰之目的不是保護已經遭受侵害的法益,而是通過刑罰適用產生威懾犯罪的效力,增強犯罪人和一般民眾的規范認同感,從而預防“法益在以后不再受侵害”。不同的刑法目的直接影響刑罰的制度建構,反之,刑法目的和機能的發揮依賴于刑罰合理的制度設置和有序、充分的施展,兩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決定刑罰制度配置時,必須強調社會一般民眾和受刑人的規范意識培養、重塑和強化。受刑人在這種積極的刑罰執行中重新建立起對法規范的忠誠和信賴,并且國民也從中體認到刑罰的良善性質和法規范的有效性,由此社會共同體的規范認同感增強,脫逸社會相當性的行為就會減少,國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得到提升。
結語
不同的歷史、傳統和背景,造就不同的民族生活和民族性格,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是根基性的。即使處于法律移植日益普遍化、不同法域不斷走向融合的今天,扎根于民族生活之上的刑罰制度也仍然散發著濃郁的民族氣息。在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開始步入后現代社會時,我國仍然處于社會結構急劇變動的轉型期,法治傳統的缺失和民眾樸素的報應心理,刑罰制度在建構時并不能完全超然于這些國情現實之外。否則,就會造成刑罰制度與社會同構性的喪失,刑罰的社會功能和價值就無法顯現。為此,刑罰制度在建構時必須對國情因素予以回應。同時,我國又處于一個社會秩序紊亂、權利關系不清、民眾法規范意識淡薄的時期,在這樣的時期,我國刑罰制度的使命就絕非對犯罪的懲罰,而是通過對犯罪適用刑罰彰顯法規范的有效性,培養國民的法規范意識,強化其規范信任感。在這種沉重的背景下,刑罰制度在回應國情因素時就不能過于盲目和隨意,祛除那些明顯與刑罰本質、目的的非理性因素的干擾,只有這樣,刑罰的價值才得以彰顯,刑罰的獨立品格才得以維持。
參考文獻
[1]一九九三年憲法修正案第七條將憲法第十五條修改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
[2]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49
[3]參見新浪網
http://news.sina.com.cn/c/2011-03-10/094222087376.shtml,2011.10.2日訪問。
[4]張明楷.刑法的基本立場.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369
[5]參見[德]克勞斯·羅克辛.刑事政策與刑法體系(第二版),蔡桂生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49
作者簡介:
陳偉媛(1983-),女,福建廈門人,福建天衡聯合(泉州)律師事務所律師,法學學士。
賴隹文(1986-),男,廣東茂名人,華僑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2010級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