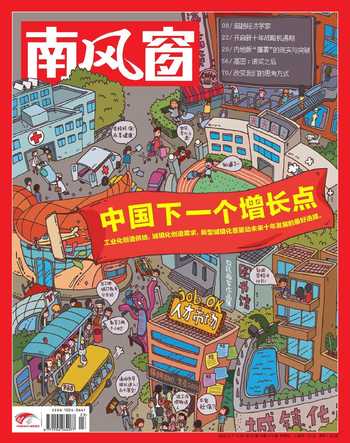中國式“影子銀行”
李威

10月初,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直言銀行理財產品是“影子銀行”,龐氏騙局,在業內外引發軒然大波,沒過幾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就警告中國“影子銀行”風險。
同樣在10月,中國央行副行長潘功勝撰文稱由于受目前統計范圍所限,“貨幣當局已無法全面評估金融體系的整體風險和貨幣政策調控效果”。
一時間“影子銀行”成為熱門話題,正如IMF在報告中所擔憂的:這個美國的舶來品在中國規模到底有多大?是什么推動了它的快速增長?如何監管風險?
巨大存量
在一切信用都集中于銀行的思維下,人們習慣于銀行高高在上的地位。年年政府考量貨幣信貸增長目標,以銀行為工具,調控宏觀經濟。
去年,央行推動了一個富有深意的變化,正式以社會融資規模統計口徑取代貨幣信貸總量,作為金融決策的主要參考。在央行網站不久前掛出來的就社會融資規模問題答記者問中,稱“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規模”。
據央行調查統計司最新數據,2002年到2011年,國內社會融資額由2萬億增至12.83萬億元(注:無特殊說明,單位均為人民幣),而銀行信貸占比卻由91.9%降至58%。
短短數年,資金瘋狂向其他平臺運動,股市、債市、信托公司、保險公司、基金、PE、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等等,蔚為壯觀,“影子銀行”大行其道。
盡管沒有官方定義,業界普遍認為行商業銀行之功能,未受嚴格監管的機構,即為“影子銀行”。小微金融人士王磊表示,目前國內的“影子銀行”,并非是有多少單獨的機構,更多的是闡釋一種規避監管的功能。如人人貸,不受監管,資金流向隱蔽,是“影子銀行”。幾乎受監管最嚴厲的銀行,其不計入信貸業務的銀信理財產品,也是“影子銀行”。
參與者非常多元,目前“影子銀行”整體資產規模只能靠猜。今年初到現在,就不斷有銀行人士或證券公司以自己的口徑測算,數值落在10萬億到33萬億的區間。資深銀行研究人士付兵濤表示:“單個市場機構或個人很難摸清真實規模,不過保守估計在10萬億左右,這兩三年尤其翻著跟頭增長。”
問題開始變得復雜了,今年中銀國際證券研究所一份報告稱目前“影子銀行”有三種最主要存在形式:銀行理財產品、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產品和民間借貸。信貸在社會融資規模占比大幅下降的背后是銀行理財產品的崛起,如以銀信合作為主的理財產品,2008年,資產規模大概1.2萬億,今年上半年已達5.54萬億。
慢牛投資公司董事長張化橋等認為,大量理財產品通過購買信托計劃,流向房地產等個別高利潤行業,風險相當集中,銀信合作是最大的“影子銀行”,也是最大的風險點。四川信托一位人士頗有同感,“公司項目是清一色的房地產,人少項目多,每個項目能派一個人過去看看就不錯了,風險控制可想而知。”
今年年中,鄂爾多斯樓市狂跌,9家信托公司20多億資金被套,相傳有數家中型商業銀行受牽連。肖鋼認為,銀行以資金池運作理財產品,產品期限錯配,發新品償付到期產品,本質上就是龐氏騙局,理財產品資金流向和透明度都有很大問題。他直言理財產品等“影子銀行”是金融業未來5年的最大風險,呼吁加強管理。
國情下的蛋
歷來很少有銀行業高管如此公開承認并抨擊行業風險,肖鋼數言,在業內外掀起軒然大波。不過,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則認為目前國內對風險所論大多流于表面。
“影子銀行”4年前出自美國一位投資家之口,他描述的對象是投行、對沖基金、保險公司等,這些機構針對各種標的,設計各種投資品種,吸引投資者掏腰包。如上世紀80年代,美國大量優質中小企業因評級低,幾乎無人問津,得不到銀行融資,投行家米爾肯尋找優質企業做標的,發行承銷它們的債券,并以高收益率回報投資人,托出了CNN等一大批后來的名企,名震華爾街。
米爾肯實質上完成了類似于銀行的存貸功能,所以“影子銀行”在美國又叫平行銀行,意為與商業銀行并存,又完全在商業銀行系統市場之外。國內卻大為不同,曾剛同樣認為“影子銀行”主要由銀行體系派生而來,這是國情下的蛋。
近年投資者貌似可選擇許多投資理財渠道,然而股市連年走熊,債市只有極少數品種對個人開放,今年違約集中爆發,民間借貸糾紛不斷,無論是直接投資還是通過這些市場上的機構投資,幾乎都沒什么好出處。到目前國內仍沒有任何一個系統或機構,能夠與銀行競爭,銀行依然牢牢控制著社會資金供給,它最大的競爭者在內部。“這就是為什么信托包括券商,會愿意讓銀行隨心所欲地拿來當通道用。”曾剛說。
銀行之所以如此熱衷于理財產品,曾剛認為有兩個原因:規避監管和同業競爭。國內銀行一直就像五花大綁的螃蟹,扛著10幾條監管紅線,其中資本充足率8%、存貸比75%、信貸額度等規定最有殺傷力。銀行理財產品不計入資產負債表,對以上3個指標均沒有負面影響,反而可通過信托、委托貸款等方式,變成不受信貸額度控制的貸款。
長期以來,銀行業同質化競爭相當慘烈,一家銀行推出理財產品,為穩住自己的儲戶,所有的銀行都得被迫陪著玩,除非被叫停,大家都退出。
這種“影子銀行”體制下的所謂風險,曾剛認為監管層“心里有數”:“我接觸的銀監會的人非常自信能夠控制銀信風險,現在每個理財產品規模、投向都要上報,監管層對池子規模、風險敞口有比較清楚的掌握。信托又在銀監會監管下,信托公司不會也不敢賴銀行的賬,信托公司不行了,還有它后面的大股東。”
而且按產品設計,理財產品風險投資者自擔,然而剛性兌付已是潛規則,如果理財產品出問題,銀行肯定來兜底,如果銀行包不住,肯定再由財政來兜底。
曾剛表示:“目前業界對風險程度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還有個有錢的政府保姆,風險應該不是高官們最關心的問題。有人出來喊清除‘影子銀行,最主要的原因我更傾向于認為是理財產品的同業競爭過于激烈,和其他同類大行差距越來越大,可能是撐不下去了。”
真正的地雷
風險并不最可怕,最可怕的是不知道的風險。“影子銀行”之所以能夠摧毀美國,就是因為投行兜售了多少個CDO(擔保債權憑證)、CDS(信用違約掉期),最后它自己都搞不清楚,何況監管機構。
在國內,盡管銀行理財產品被推到風口浪尖,但多位受訪者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認為“影子銀行”最大的風險地帶不在于此。王磊在北京一家知名投資顧問公司做副總,正準備離職,原先他被以百萬年薪招進公司,負責公司P2P(peer to peer),也被稱作人人貸,然而來了之后,發現這里自己實在玩不下去。
據他所知,在老式的北京民間拆借中,投資顧問公司、擔保公司等作為居間人需找出資人和借款人,一般是先有項目再找資金,合同是由雙方以個人名義簽訂,居間人不經手資金,只收介紹費。到目前雖然個人不允許放貸,但這種行為可以打擦邊球,因為最高人民法院有文件稱親朋好友同事之間的拆借合法。
像王磊所在的公司,也通過委托貸款的形式大量放貸,即公司確定借款方,經銀行發放委托貸款,公司老板為某實力雄厚的港商,所放資金大多是老板的自有資金。
這些方式安全卻以損害資本效率為代價,如居間人手中無資金,不可能具備銀行那樣的存貸匹配能力,也得不到相應的收益。近兩三年興起的P2P模式帶來了顛覆,王磊說,P2P原是以互聯網為平臺,個人自由對接,平臺撮合交易。到了國內,許多公司拿著這個牌子,卻從線上往線下發展,就相當于原先是淘寶,現在被改成了中國工商銀行。
P2P沒有門檻,只要是注冊登記的企業法人就能作業,完全無部門監管。摸熟套路后,不少公司就在吸收客戶存款,發放貸款,建造類似于銀行的資金池。王磊說,只要有滿意的收益率,能安全收回投資,并不太在意他的錢投給了誰。“很多公司就虛擬借款人,圈投資人的錢。”
而且有公司已經開始資產證券化,王磊知悉某家投資顧問公司在未告知客戶的情況下,將其債權收益打包,轉化為投資理財計劃,賣給公司的其他客戶,也賣給其他P2P公司,已形成批量業務,該公司再拿著融資來的錢去投資。
雖然完全是掛羊頭賣狗肉,卻非常熱火,據王磊了解,像行業領軍企業宜信,今年打算擴充員工至2萬人,而包商銀行才6000人。他所在的公司也四處擴張,連在當地營業執照都未拿到,老板已經要求去開拓業務了。
從業四五年,到現在王磊也不知道P2P公司有多少家,規模有多大,各家的操作模式如何,但他已經感到深深的恐懼。他說,目前公司大多放貸對象是中小企業,實際利率一個月多在3%,一年不算復利也是36%,很多借款人實際是很難承受的,資金以短快為主,短存長貸比銀行更為嚴重,現在公司僅有2%的壞賬撥備,連塞牙縫都不夠。
王磊說:“經濟大環境不好,P2P開發了資金池,甚至還有理財產品形式的債券,它的風控、資金盤子和銀行卻遠遠不是一個等量級。而且P2P存款額小,儲戶多,現在感覺一個風吹草動就可能引發擠兌,甚至是大規模的社會問題。”
何處監管
在目前一行三會體制下,分割監管改變了很多行業的命運。
和信托相當的工具多了去了,為什么銀行偏偏選中信托?曾剛表示銀行和信托像銀監會家里的兩兄弟,銀監會能夠輕松地控制住局面,在過去的幾年里,可以說是想叫停就立馬會被叫停,簡單易控。
但銀證合作監管就比較難,券商屬于證監會監管,兩個平行部門協調起來難度就大很多,銀監會會非常謹慎。現在券商也在做信托以前的通道業務,但能做多久很難說。原先信托資產規模還不如券商,今年已近券商的3倍,而小貸公司和典當行兩個行業加起來還不到信托資產的1/9,“在這種體制下主事方很難會從整個金融市場角度考慮,而只是自己一畝三分地的收成和風險。”曾剛說。
“影子銀行”橫跨證券、保險、信托等眾多行業,目前這種體制要監管住,猶如破網捕魚。
留下的空白越來越多,央行調控難度越來越大,就如一位學者所形容的,央行在被拿到火上烤。近期央行副行長潘功勝撰文呼吁盡快起草相關綜合統計法規。一開始情況其實并非如此,央行金融穩定局曾牽頭對“影子銀行”等做專門的監測研究,但因要協調銀監會、證監會等機構,最后不了了之。
央行如何協調監管的難題,并沒有人能夠給出一個清晰的藍圖。而此時“影子銀行”規模已占據半壁江山,如何制定合理的貨幣政策,對央行來說是一個新的課題。
其實“影子銀行”不是一個新話題,之所以浪潮一波接一波,許多市場人士認為醉翁之意不在酒。張化橋在去年底就開始強烈鄙視銀信合作,他所憤恨的莫過于利率管制和銀行壟斷。多年來,利率人為制定,銀行低廉拿著老百姓的資金,為國企、地方政府融資,中間藏匿了多少腐敗,犧牲了大量資本效率。
某對沖基金經理劉海影說:“‘影子銀行有風險,壟斷的銀行也有風險,目前是系統性風險,房地產等行業就像懸在頭頂的堰塞湖。見過幾個銀行的行長,他們都對自己的風險控制很有信心,但金融向來存在諸多未知和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