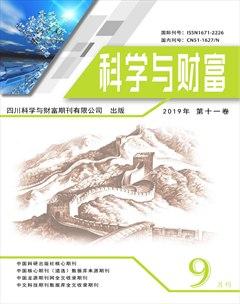簡析物聯網背景下智慧校園的應用
謝堅
摘 要:網絡科技與電子科技的迅速興起,促成了物聯網技術的產生,有效的體現了物與物、物與互聯網、物與人之間的有效結合,同是也是傳播信號進步的一種體現。在物聯網時代的背景下,學校也應與時俱進,把便捷的物聯網技術作用到校園生活與教學中,來提升校園管理能力、提高日常教學水平,真正的體現現代教育的意義。
關鍵詞:物聯網;智慧校園;互聯網技術;物與物;應用
引言:
近年來,物聯網在我國各個領域都被廣泛運用。智慧校園的產生也源于不斷發展的物聯網技術,這是科技進步的結果。目前,各大、中、小院校已經全面展開了智慧校園的管理。物聯網在教育中的應用,對推進智慧校園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同時也有效的提高的教學水平,對學生的綜合發展有著積極地影響意義。
一、物聯網的概述
物聯網是信息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代表,故其英文名為Internet of things。通俗點講就是利用互聯網技術,使兩個物體相互連接,一方作為采集者,進行信息采集,通過互聯網技術把信息進行信號傳遞,另一方作為展現者,把信號轉化為可供人類識別信號,然后顯示出來。
無論是信號采集,還是信號顯示都是電子科技進步的表現。因此,物聯網技術的產生,被稱為信息產業發展的第三次浪潮。
(一)物聯網的形成背景
最早的物聯網誕生標志是1990年網絡可樂販售機,但直到1999年,物聯網概念才真正被提出來,并使用射頻識別和無線通訊建立了信息采集與傳輸系統。然而,為物聯網進行正真定義的時間為2005年,是由國際電信聯盟提出的概念。我國在2008年就物聯網的概念展開研討會,把物聯網技術的發展提到了科技發展中。
(二)物聯網的優勢
物聯網的出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因人的因素而出現滯后性。因此,物聯網作為智慧服務系統,第一,可以減少相應的人工利用率,從而降低人工費用;第二,可以減少辦事等待的時間,極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另外,發達的電子科技設備為物聯網的信息采集系統,提供了更多的硬件與軟件服務,并且通過不斷改進增強了數據收集功能。因此,作為一種安全、科學、嚴密的設備,物聯網已經被運用到各個工作領域、生活領域與學習領域。
二、物聯網與智慧校園
“智慧”這個詞在2009年被麥特.王博士在《構建智慧的地球》中首次提出,同年,美國“圓桌會議”真正對智慧地球做了定義,并開始展開投資。
如今,“智慧”這個概念已經覆蓋了幾乎所有的領域,智慧窗口作為前臺服務窗口,已經被我國各政府機構、稅務機構、金融服務機構、各企業及教育領域應用,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人工智能化服務。
智慧概念的產生源于物聯網,因此,智慧校園的構建也要依靠物聯網。學校作為國家的教育機構,具有完整的管理體制,要想打造智慧校園,就要把物聯網技術充分的運用起來,從各方面改善管理環境,提高管理效率與教學手段,從而提升校園形象。
(一)智慧校園的形成背景
2010年,浙江大學在響應國家“二十五”中,提出了“智慧校園”的構建理念,這是智慧校園在我國的首次提出。近年來,隨著我國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2018年我國發布了《智慧校園總體框架》,這項標準的頒布更加促進了智慧校園的生成。
(二)物聯網對智慧校園的意義
1、實現可視化管理
學校作為教育系統,要對學生的安全負責,物聯網技術下的可視化管理代替了原來的人工管理,把監控管理合理的分布到學校的各個角落,分區、分時的對學生的安全進行監管。另外,可視化管理不僅體現在安全方面,也體現在對教師、學生的考勤管理中。實施物聯網技術,不僅節省了人員費用,也可以提高學校的安全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學校壓力。
2、豐富教學手段
以物聯網技術為依據,多媒體教學手段在各教育階段的學校中相繼展開,教師利用多媒體音頻、視頻以及圖片等形式,讓學生對知識的吸收角度更加直觀,把平面的理論知識變得立體化,有效的豐富了教學手段,極大的彌補了傳統教育中的不足。
3、為學生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傳統教育使學生的思想局限在了書本內,更加注重的是應試教育。現階段的教學目標是學生整體素質的培養。物聯網生成了智慧校園,智慧校園可以實現文本到實物的轉化,是為了更好的培養學生個性發展及興趣發展。利用物聯網進行輔助教育,可以開拓學生的眼界,拓展學生的思維,為學生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
三、物聯網技術在智慧校園中的應用
(一)物聯網技術在校園管理中的應用
物聯網技術可以有效的實現智慧校園的管理,這些管理包括安全管理、學生管理、教職工管理、工程管理、財務管理及后勤管理等。例如:把物聯網技術應用在門禁管理中,可以利用臉部識別技術進行教職工、學生及家長的臉部掃描,從而保證校園的安全性。利用電子圍籬的傳感設備及監控設備,可以防止學生與外來人員的隨便進出,并對學校周圍進行實時監控。
關于教職工人員管理、工程管理、財務管理等可以借鑒企業的管理形式來進行,這是全面實現專業化管理的一個重要手段,是體現智慧校園管理一體化的重要標志。
(二)物聯網技術在日常教學中的應用
物聯網技術為學生提供了更多的教學方式,多媒體在教學中的應用就是最常見的物聯網教學。此外,為了更好地提升學生的整體素質,學校應該加大模擬教學的力度,這樣可以使學生在身臨其境的環境中,以直觀的形式去領悟知識,從而更好地培養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有效的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更好的開發其主動思考的能力,完成自主學習。
未來教室的暢想是智慧校園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形成的產物,將徹底顛覆學校、教師、家長對教室的認識。在未來教室中,電子觸屏將代替黑板、粉筆及書本等傳統教學工具,把課本中的文本轉化為虛擬的立體形象,從而更好、更有效的培養學生的文化基礎知識,并拓展其學習領域,這其實就是把傳統教學向模擬課堂升級的一種表現形式。
(三)物聯網技術在學生管理中的應用
目前,我國部分學校已經開始利用物聯網技術進行學生管理。比如校園一卡通的出現,實現了學生在校園內的一卡消費,包括打飯、校園公交、校園消費等,這樣可以讓學生家長通過電子賬單,對學生的校園消費有更多了解,這樣做的好處是:有助于家長對學生生活管理,也有助于學校對學生的紀律管理。再例如:智能簽到工具,這是利用聲音識別進行的智能打卡工具,來驗證學生是否簽到,這樣不僅可以完成快速簽到過程,還可以避免出現學生之間代簽到現象的發生。
結束語:
智慧校園是物聯網發展下的產物,但智慧校園的發展同時也會為物聯網技術提出更高的難題,這促使了兩者之間的相互發展。現在的學校教育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現代科技的引領下,學校作為培養國家未來接班人的場所,無論從管理還是教學來說,都已經逐漸向智能化靠攏,讓教師和學生切身感受到了科技帶來的新事物、新思想,從而為培養現代化學生奠定了有力的基礎。
參考文獻:
[1]郭暉,高楊,孫震.物聯網背景下智慧校園的應用[J].電子技術與軟件工程,2018,146(24):1-1.
[2]李鵬飛.淺談物聯網技術在智慧校園中的應用[J].電腦迷,2018,112(11):62.
[3]朱俊波,張勇.物聯網技術在高校智慧校園中的應用[J].科技傳播,2018,v.10;No.208(7):98-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