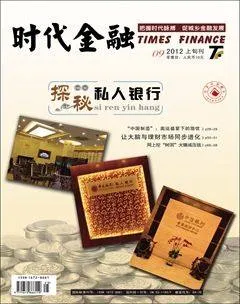中國醫(yī)改任重道遠
莊之蝶
2012年7月27日在貴陽舉行的“2012生態(tài)文明貴陽會議”上,衛(wèi)生部部長陳竺表示,我國基本醫(yī)保已覆蓋96%的人群,已跨入具有全民醫(yī)保制度國家行列。而在不久前的7月12日,北京男子廖丹因沒錢為患尿毒癥妻子治病,私刻醫(yī)院收費章,被檢方以詐騙罪提起公訴;幾個月前,求醫(yī)多年的安徽農(nóng)婦張艷在欠下30多萬元債務(wù)之后,在病房的衛(wèi)生間里了斷自己。從2009年開始的新一輪衛(wèi)生體制改革從“量”上看確實可喜,但在“質(zhì)”上確實有些名不副實,問題頗多。
中國的醫(yī)療衛(wèi)生體系到底要不要市場化
這個問題早在幾年前便在政府與學(xué)者中展開過激烈爭論,多年過去,爭論之聲仍不絕于耳。醫(yī)療服務(wù)的確有特殊之處:一方面,醫(yī)療不同于普通商品,醫(yī)療服務(wù)的供需雙方信息是嚴重不對稱的,一般病人缺少醫(yī)學(xué)知識,無所判斷自己得了什么病、該吃什么藥等等;病人到醫(yī)院看病只能被動的接受醫(yī)生的評估與治療。可以說這種不對稱既存在專業(yè)知識上的不對稱,又存在定價評估上的不對稱。在這種情況下,病人沒有能力評價醫(yī)生好壞,自愿選擇很難真正“自愿”。這就需要政府或權(quán)力機構(gòu)介入,降低信息不對稱帶來的病人被“宰”風險。另一方面,醫(yī)療又不屬于公共物品(在經(jīng)濟學(xué)上,公共物品指的是既沒有排他性也沒有競爭性的物品),因為醫(yī)生在給某一病人治病時,而另一病人就不能得到及時的醫(yī)療服務(wù)。所以它不屬于公共物品,具有排他性和競爭性,與普通商品有某種共性,需要市場機制的作用。
2012年7月1日,北京友誼醫(yī)院調(diào)整掛號費價格,實行新的醫(yī)事服務(wù)費。普通號42元,副主任醫(yī)師號60元,主任醫(yī)師號80元,知名專家號100元。其中,醫(yī)保報銷40元。也就是說,如果掛普通號,醫(yī)保患者只需自付2元;如果掛不同級別的專家號,分別需要自付20元、40元、60元。結(jié)果,普通號需求大增,而專家號出現(xiàn)剩余。
從經(jīng)濟學(xué)的角度看,價格決定著資源配置的方向和狀況。在過去,普通號5元,知名專家號14元。就性價比來看,專家號顯然比普通號更合算。作為理性經(jīng)濟人,患者自然愿意多花幾元錢掛個專家號,即使是感冒發(fā)燒這種小病。而價格調(diào)整后,由于知名專家號比普通號費用高很多,普通號能解決問題的,自然沒必要排隊去買專家號,因為此時買專家號性價比不大,這就把專家號自然地留給最需要的人,而重病患者對專家號是“剛性需求”。 這種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方式,使優(yōu)質(zhì)資源得到了更合理的配置。
目前中國的醫(yī)改過度強調(diào)政府主導(dǎo)(中國公立醫(yī)院還占醫(yī)療行業(yè)90%以上的份額,與美國民辦醫(yī)院占84%的份額正好倒過來),市場機制作用很小。政府醫(yī)療政策完全以低收入群體的承受力為導(dǎo)向,包括掛號費、藥價等都被管制。雖然政策的出發(fā)點是為保護普通病人,但是,這使整個醫(yī)療行業(yè)定位在低水平,大大抑制醫(yī)院、醫(yī)生的積極性,部分醫(yī)務(wù)人員要么靠紅包增收,要么靠亂開藥、多開藥從醫(yī)藥公司拿回扣。
隨著中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收入階層分化加劇,治病費用也今非昔比,醫(yī)療組織形式也應(yīng)該更復(fù)雜。因此,醫(yī)療行業(yè)已經(jīng)不再是一刀切“市場化”或“公辦醫(yī)療”這樣簡單的答案了。友誼醫(yī)院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在滿足基本醫(yī)療需求方面,政府應(yīng)突出體現(xiàn)公益性,維持較低價格,保證大多數(shù)人能夠公平享有資源,不讓窮人輸在健康起跑線上。而在滿足非基本醫(yī)療需求方面,則可以借助市場這個無形之手,讓有限的資源發(fā)揮最大的價值。另外,引入市場機制,放手向私人和機構(gòu)開放醫(yī)療服務(wù),采用針對性強的措施刺激醫(yī)療服務(wù)供給,還有更良性的社會效應(yīng):患者得到了價格更合理、更貼心的醫(yī)療服務(wù),滿意度會大大提高;醫(yī)生服務(wù)態(tài)度好轉(zhuǎn),醫(yī)療行業(yè)“門難進、臉難看、病難治”的形象也將有所改變。如此,“醫(yī)患對立”將得到根本緩解。
美國的醫(yī)改從肯尼迪政府到奧巴馬政府也經(jīng)歷了很長時間的跨度,最終走向了有監(jiān)管的市場化道路。中國發(fā)展營利性私人醫(yī)院,推行市場化改革,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雖然這個過程是漫長的,但是相比政府主導(dǎo)的“全民醫(yī)保”,推行真正的政府監(jiān)管下的市場改革,利用有形與無形之手的結(jié)合,以改變“不得不長期購買劣質(zhì)醫(yī)療服務(wù)”現(xiàn)狀,效果也許會好得多。
中國的醫(yī)改要著重從病人的利益出發(fā)
中國的醫(yī)改把大量的時間花在各個部門利益的協(xié)調(diào)、分配上,這就很可能導(dǎo)致忽視社會大眾群體的利益,發(fā)改委、衛(wèi)生、財政、社保是各省醫(yī)改領(lǐng)導(dǎo)小組中最重要的4個部門。發(fā)改委作為牽頭部門,這就與衛(wèi)生廳長期主管醫(yī)藥衛(wèi)生行業(yè)的現(xiàn)狀構(gòu)成了矛盾。衛(wèi)生廳對于行業(yè)狀況、基層情況、相關(guān)政策等掌握全面,醫(yī)改無疑會涉及衛(wèi)生部門的利益。在財政、社保與衛(wèi)生部門之間也會發(fā)生類似的沖突。衛(wèi)生部門常常希望財政能為衛(wèi)生投入更多支持,但是財政部門又不得不在一個更大盤子里精打細算。
我們觀察會發(fā)現(xiàn),人保部門和衛(wèi)生部門對城鎮(zhèn)居民醫(yī)療保險、城鎮(zhèn)職工醫(yī)療保險、新型農(nóng)村合作醫(yī)療的資金統(tǒng)籌和統(tǒng)一管理存在扯皮:新農(nóng)合是各級衛(wèi)生部門分管,城鎮(zhèn)居民醫(yī)保和城鎮(zhèn)職工醫(yī)保則是各級人保部門分管,如果這三個保險要合并,就必然涉及到這兩個部門之間的合并。因此如何限制部門利益,解決決策機制的瑕疵、問責制度的缺失等問題,保障社會公共利益是我國醫(yī)改亟需解決的問題。
另外,政府財政的醫(yī)療經(jīng)費開支傾斜方向很難充分體現(xiàn)病患利益。目前中國的財政經(jīng)費很多直接劃撥給公辦醫(yī)院,這必然造成付費方即政府與得到醫(yī)療服務(wù)的老百姓分離,使醫(yī)療受益方不掌握醫(yī)療定價權(quán)和付費權(quán),而掌握定價權(quán)和付費權(quán)的又是跟病人關(guān)系不大的政府部門。由此帶來的結(jié)果是:醫(yī)院為得到更多的經(jīng)費只顧討好、賄賂政府官員,而不是去改善醫(yī)療服務(wù)、滿足病人需求,間接導(dǎo)致腐敗的滋生。因此,醫(yī)療經(jīng)費應(yīng)向病患增加傾斜力度,病患根據(jù)自己要求對醫(yī)院做出選擇,這樣服務(wù)好、口碑佳的公立醫(yī)院不僅不會因為財政支持力度的減少而走下坡路,反而會因為受患者青睞發(fā)展得更快。
“空降”的藥品降價
2009年10月2日國家發(fā)改委發(fā)出通知,公布了國家基本藥物的零售指導(dǎo)價格。296種、2349個具體的劑型規(guī)格品中,45%的藥品降價,平均降幅12%。而三年過去了,中國以藥養(yǎng)醫(yī)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變,據(jù)統(tǒng)計,目前中國醫(yī)療服務(wù)收費掛號費為5~14元;住院費:28元/床/天;手術(shù)費:闌尾切除術(shù)304元,肺癌全肺切除術(shù)983元、心臟搭橋術(shù)2200元。在病人全部的醫(yī)療成本中,真正體現(xiàn)醫(yī)生價值的醫(yī)療服務(wù)費比例低于10%,90%由藥費、檢查費和醫(yī)療器械使用費構(gòu)成。在醫(yī)院的三大塊收入(財政補貼收入、藥品收入、醫(yī)療服務(wù)收入)來源中,財政補貼收入普遍低于10%,醫(yī)療服務(wù)收費與藥品貢獻的利潤依據(jù)各醫(yī)院情況不同而占據(jù)不同比例,但可以肯定的是,藥品依然是醫(yī)院最為重要的利潤來源。現(xiàn)有的醫(yī)療服務(wù)所能產(chǎn)生的利潤并不高,而且還是建立在嚴重壓低醫(yī)生正常勞動收入的基礎(chǔ)之上。這種情形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普通醫(yī)生的醫(yī)事服務(wù)費較低,“治病的不如算命的”,最終導(dǎo)致“紅包現(xiàn)象”嚴重;另一方面,對老百姓來說,因藥價過高,很容易因病返貧。
觀察可以發(fā)現(xiàn),以往發(fā)改委公布的“被降價”藥品,許多在市場上都很快會遇到“買不到”的現(xiàn)象,基本藥物目錄中都會減少一些藥品,稱之為“降價死”。隨后新藥層出不窮,價格也是一路躥高,藥品降價也最終成為“空降”。現(xiàn)在的情況是藥品流通秩序混亂,導(dǎo)致藥價貴;公立醫(yī)院“以藥補醫(yī)”,導(dǎo)致過度檢查和用藥。可以這樣說,降低病人醫(yī)療費用的關(guān)鍵就在于看大病的醫(yī)院能否把藥價真正降下來。
“醫(yī)保覆蓋”范圍存空白
早在2009年,《中共中央 國務(wù)院關(guān)于深化醫(yī)藥衛(wèi)生體制改革的意見 》便提出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基本醫(yī)療保障為主體,其他多種形式補充醫(yī)療保險和商業(yè)健康保險為補充,覆蓋城鄉(xiāng)居民的多層次醫(yī)療保障體系。目前中國的醫(yī)保覆蓋面雖然已超過96%,看似完成了意見的要求,但“醫(yī)保要你交,重病難報銷”的情況仍頻頻發(fā)生,前文提到的廖丹及張艷事件便是鮮明的案例。
2010年,人社部曾明確表示,“對自愿選擇參加城鎮(zhèn)居民醫(yī)保的靈活就業(yè)人員和農(nóng)民工,各地不得以戶籍等原因設(shè)置參保障礙”。事實上,類似廖丹妻子這樣在戶籍夾縫中被城市醫(yī)保遺漏的外來人員、農(nóng)民工并非少數(shù),而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有資料顯示,2011年全國農(nóng)民工總量25278萬人,但參加醫(yī)療保險的農(nóng)民工人數(shù)為4641萬人,這也就是說,在城鎮(zhèn)參加醫(yī)保的農(nóng)民工實際不足五分之一。雖然,除了城鎮(zhèn)醫(yī)保,農(nóng)民工在農(nóng)村原籍還能夠參加新農(nóng)合醫(yī)保,但由于新農(nóng)合醫(yī)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認、統(tǒng)籌層次低以及報銷水平不高等原因,對于生活在城市的外來務(wù)工人員來說,這樣的醫(yī)保顯然不可能起到事實上的救濟作用。也就是說我國的醫(yī)保只是形式上覆蓋13億人群,而實際上,“醫(yī)保覆蓋”范圍遠沒有這么樂觀。
“已跨入具有全民醫(yī)保制度國家行列”聽上去很美,但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醫(yī)保體制仍面臨巨大的漏洞:“偽市場化”讓醫(yī)療服務(wù)缺乏亮點;大病難覆蓋,一旦得病就陷入絕境;城鎮(zhèn)與農(nóng)村醫(yī)保體系分立等。可以說經(jīng)過三年的努力,在中國,“全民醫(yī)保”已經(jīng)在制度層面實現(xiàn),但這只是在醫(yī)改這條長征路上的一小步,未來的路可謂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