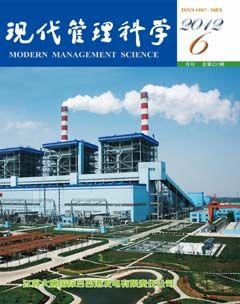連鎖商如何促進“加盟商公民行為”?
翟森競 高維和
摘要:在連鎖體系中,連鎖商可通過促進“加盟商公民行為”來進行關系管理。文章闡明了“加盟商公民行為”的內涵,指出了連鎖商信息傳遞對“加盟商公民行為”的影響,探討了兩類分配公平(雙邊交換公平、網絡分配公平)對此影響的調節作用,提出了相關研究假設。根據來源于服務型連鎖體系的數據對假設進行了檢驗、對結果進行了分析。研究結果有助學術界進一步深化對于交換中公平作用的認識,亦有助連鎖商更有效地管理關系。
關鍵詞:加盟商公民行為;雙邊交換公平;網絡分配公平;信息傳遞;連鎖商
一、 引言
商業型連鎖代表了一種獨特的組織間交換模式。兩個組織--連鎖商和加盟商,在法律上相互獨立,在交換中卻保持著高度的相互依賴。已在市場上占據一席之地的連鎖商不僅會引導加盟商進入市場,還會授權它使用自身品牌,指導它為終端消費者提供產品或服務(Grunbagen & Dorsch,2003)。近年來,商業型連鎖(以下簡稱為“連鎖”)在我國發展迅速。據中國連鎖經營協會統計,2010年我國連鎖體系已超過4 500個,覆蓋的行業業態超過70個,加盟店總數在40萬家以上,直接創造的就業崗位超過500萬個。其中,“特許經營連鎖120強”實現了超過3 300億元的銷售額,擁有著11萬家以上的加盟店數量。在此過程中,如何管理好自身與體系中加盟商的關系成為了連鎖商迫切關注的問題,也構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
組織進行關系管理,除了要促進雙方在交換過程中的合作、協同之外,更是為了實現其終極目標——獲得長期的經濟收益。連鎖商同樣如此。在連鎖體系中,連鎖商會向加盟商提供原材料、專有信息;加盟商吸收、整合它們,形成向終端消費者提供服務、產品的能力,從而獲取收益(Windsperger,2004)。加盟商再將收益中的一部分以費用的形式(初始加盟費、特許費用、廣告費用、培訓費用等)轉移給連鎖商,使連鎖商無需與終端消費者打交道便可獲益(Grunbagen & Dorsch,2003)。連鎖商擁有的加盟商越多、所獲收益就越大,維持和擴大加盟商數量因而成為了它進行關系管理的一個重要目標。本文提出連鎖商可以通過傳遞信息、踐行兩種分配公平(雙邊交換公平、網絡分配公平)來促進“正向口碑”、“留存意愿”這兩種“加盟商公民行為”,從而實現該目標。本文探討了以上變量之間的關系,提出并檢驗了相關研究假設,并對檢驗結果進行了討論。
二、 理論與研究假設
1. “加盟商公民行為”。“公民行為”(Citizenship Behavior)最早被用來分析員工針對所屬組織或組織內其他個體所展開的行為。它是“會在整體上促進組織有效地實現其功能,但卻未經正式獎賞體系明文規定、而是由組織內的個體憑其自由意志所做出的‘個體行為”(Organ, 1988)。“公民行為”不是組織正式要求員工必須履行的職能行為,但卻可以產生諸多正向效應,例如促使員工留在組織中、提高員工產出、促進組織績效的提升等等(Bolino et al.,2002)。隨著其他領域學者將此概念引入到各自研究之中,“公民行為”的應用逐漸突破了組織內外的界限。在營銷領域中,“組織內的”銷售人員針對“組織外的”顧客所展開的銷售產品、服務的行為也被視為“公民行為”(Hui et al.,2001)。進一步地,它還被用來描述組織外成員針對組織、組織內成員的行為。例如,Bove等(2009)提出了“顧客公民行為”,用它來描述顧客所從事的向他人推薦組織、對組織產生關系依附、向組織提供意見反饋、參加組織活動等行為。可見,從情境擴展的角度而言,用“公民行為”來表述商業組織(比如加盟商)在交換中的某些特定行為,是完全可行的。
在長期接觸中,交換雙方會締結起關系契約,展開有別于經濟交換的社會交換。本文認為,無論是組織內、還是組織外個體的公民行為,其本質是個體在關系契約作用下進行社會交換的一種方式。因而,雖未經明文規定,組織成員會對組織服從、忠誠,會幫助其他成員解決問題、對其工作中的不足予以容忍等;雖未被強制要求,顧客會從事有利于組織的各種行為。在連鎖體系中,連鎖商與加盟商在開展交換時雖會簽訂顯性契約(正式合同),但由于雙方無法預見到未來的所有可能情形,該顯性契約通常不足以應對交換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它們在交換中會建立起關系契約(Heide & John,1992),會從事超出顯性契約規定的行為,會展開超越純經濟交換的社會交換。由此,在內涵上,“公民行為”也可用來表述加盟商在交換中的某些特定關系行為,它們構成了“加盟商公民行為”。
在連鎖體系中,連鎖商擁有的加盟商越多,所獲收益越大。若現有加盟商向外界傳播出它的正向口碑,則可能有更多潛在加盟商選擇它,進而為其帶來更多收益。同時,若現有加盟商在合同期滿后依然選擇現有連鎖體系,則連鎖商的加盟商數量不會減少、其收益不會流失。“正向口碑”、“留存意愿”是超出了雙方顯性契約規定的、可在很大程度上由加盟商按其自由意志開展的行為,是連鎖商期望的兩種至關重要的“加盟商公民行為”。
2. 連鎖商信息傳遞對“加盟商公民行為”的影響。信息是“溝通的原料”,在任何交換中都是信息將雙方連接起來的(Duncan & Moriarty,1998);連鎖商與加盟商之間的交換也是如此。前者向后者提供的專有信息主要包括:加盟商開辦門店所需要的相關信息,加盟商能夠生產出合格產品、服務所需要的實際知識、訣竅等;有助于加盟商提升自身經營水平的管理準則等。
連鎖商專有信息的價值主要在于其有用性和易理解性兩個方面。有用性是指該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夠促進加盟商提升能力、獲得收益;易理解性是指該信息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加盟商完全理解(Perez-Nordtvedt et al.,2008)。加盟商從連鎖商處獲得的信息越有用、越易理解,培育出的為終端顧客提供服務或產品的能力就更強,獲益會更多,從而對雙方的整體關系越是滿意。消費者行為研究中的大量文獻表明,滿意會導致正向口碑傳播(Danaher & Rust,1996)。也有研究也表明加盟商滿意會增強它在加盟期滿后的留存意愿(Chiou et al.,2004)。由此,通過滿意,連鎖商的信息傳遞會影響到“正向口碑”、“留存意愿”這兩種加盟商公民行為。本文提出相應假設如下:
H1:連鎖商所傳遞信息越是有用,加盟商越會進行正向口碑傳播;
H2:連鎖商所傳遞信息越是有用,加盟商的留存意愿就越強;
H3:連鎖商所傳遞信息越易理解,加盟商越會進行正向口碑傳播;
H4:連鎖商所傳遞信息越易理解,加盟商的留存意愿就越強。
3. 兩類分配公平的調節作用。兩類分配公平指的是雙邊交換公平、網絡分配公平。如前所述,加盟商從連鎖商處獲得的信息越有用、越易理解,為顧客提供服務或產品的能力就更強,獲益會更多。然而,加盟商必須以費用的形式將部分收益轉移給連鎖商,剩余部分才是加盟商最終的經濟收益。在此過程中,加盟商會將自身的(收益 / 付出比值)與連鎖商的(收益/付出比值)進行比較,判斷它們之間的收益分配是否實現了雙邊交換公平(Fair Exchange)(Cook & Hegtvedt,1983)。對于加盟商而言,前者小于后者,則為不公平;反之,則是加盟商眼中的公平。雙邊交換越是公平,加盟商在同等付出下所獲得的最終經濟收益就越多,它對自身與連鎖商關系的滿意程度越會增強。事實上,已有的實證研究也顯示雙邊交換公平確實會對組織的滿意產生影響(Kumar et al.,1995)。綜上,本文提出假設如下:
H5:雙邊交換公平會增強信息有用性對正向口碑傳播的影響;
H6:雙邊交換公平會增強信息有用性對留存意愿的影響;
H7:雙邊交換公平會增強信息易理解性對正向口碑傳播的影響;
H8:雙邊交換公平會增強信息易理解性對留存意愿的影響。
連鎖體系是由1個連鎖商與多個加盟商構成的網絡。加盟商也會將自身的(收益 / 付出比值)與其它加盟商相對比,判斷連鎖商是否做到了網絡分配公平(Fair Allocation)(Cook & Hegtvedt,1983)。連鎖商在資源分配上越是公平,加盟商越對其產生好感,對其更加滿意,更愿意從事公民行為。因而有:
H9:網絡分配公平會增強信息有用性對正向口碑傳播的影響;
H10:網絡分配公平會增強信息有用性對留存意愿的影響;
H11:網絡分配公平會增強信息易理解性對正向口碑傳播的影響;
H12:網絡分配公平會增強信息易理解性對留存意愿的影響。
三、 樣本與變量度量
1. 樣本。本文以中國市場上極具代表性的房產中介連鎖作為研究情境。為了避免內部不一致性問題的出現,我們從同一體系中抽取樣本。應對方要求,我們隱去該連鎖實名。截至2011年3月,該連鎖體系在中國32個城市擁有的加盟店數量位居市場前列;在企業規模和成交額兩個指標上,它在正式運營的90%的區域中都位于當地市場前三名。我們選取了上海、杭州、天津、青島、武漢等五個代表性城市的加盟商進行調研。2011年1月到3月,共發出問卷總計228份,回收有效問卷156份,回收率為68%,高于20%的可接受水平(Kumar et al.,1995)。
2. 變量的度量項目。它們主要來源于已有文獻,其中“信息有用性”、“信息易理解性”分別包含3個項目,調整來自于Perez-Nordtvedt等(2008);“正向口碑”、“留存意愿”均由1個項目度量,分別來自于Danaher和Rust(1996)、Chiou等 (2004)。參考Kumar等(1995)的分配公平度量項目以及“雙邊交換公平”、“網絡分配公平”的含義,本文分別采用“加盟商(自身)與連鎖商之間(收益 / 付出)的公平程度”、“加盟商(自身)與其它加盟商之間(收益 / 付出)的公平程度”來度量它們。
四、 數據分析與假設檢驗
1. 信度及效度。在本文中,“信息有用性”、“信息易理解性”這兩個變量需要進行信度、效度分析。信度包括度量項目信度和變量信度;本文根據單個項目在所屬變量上的載荷考量前者,根據組合信度系數(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考量后者。變量效度包括匯聚效度和區別效度;采用平均抽取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衡量前者,根據某個變量AVE的平方根與它和其它變量之間相關系數的對比結果衡量后者。
Amos7.0軟件進行的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顯示:相關項目在其度量變量上的載荷都在0.7以上,大于0.4的要求;變量的CR系數超過了可接受標準0.7,這表明數據擁有良好的信度。變量AVE超過了50%的標準,數據的匯聚效度可以滿足;變量AVE的平方根大于它們與其它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保證了數據的區別效度(Fornell & Larcker,1981)。
2.假設檢驗結果。本文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artial Least Square,PLS),通過SmartPLS2.0軟件對假設進行了檢驗。PLS分析主要報告結構模型中內生變量方差被解釋比例的R2值,以及指向變量預測作用大小的f2值;R2的三個值0.19、0.33、0.67被分別視為小、中等、大;f2的三個值0.02、0.15、0.35可被分別視為小、中等、大(Karim,2009)。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正向口碑”、“留存意愿”的R2值分別為0.59、0.65;“信息有用性”指向“正向口碑”的f2值為0.21、指向“留存意愿”的f2值為0.23;“信息易理解性”指向它們的分別為0.22、0.25;“信息有用性”與“雙邊交換公平”、“網絡分配公平”交叉項指向它們的分別為0.24、0.27,“信息可理解性”與“雙邊交換公平”、“網絡分配公平”交叉項指向它們的分別為0.26、0.29。以上結果表明結構模型整體擬合良好。
在本文所提出的12個假設中,假設H1~H10的T值大于2,得到了支持;H11、H12的T值分別為1.87、1.65,沒有得到支持。而且,H1、H2對應的標準回歸系數(0.23、0.20)分別大于H3、H4對應的回歸系數(0.16、0.13),表明連鎖商的信息有用性比信息易理解性對加盟商的“正向口碑”傳遞、“留存意愿”影響更大。H5、H7對應的標準回歸系數(0.17、0.15)分別大于H6、H8對應的回歸系數(0.13、0.12),表明“雙邊交換公平”對加盟商“正向口碑”傳遞的促進作用大于它對其“留存意愿”的增強作用。H9、H10的標準回歸系數分別為0.11、0.10,而H11、H12則沒有得到支持,表明“網絡分配公平”在增強信息有用性方面更有效,不能顯著增加信息易理解性的效應。“雙邊交換公平”、“網絡分配公平”不僅本身不同,所發揮出的影響也有差別,這是已有研究不曾探討過和認識到的。
五、 結語
在連鎖體系中,連鎖商進行關系管理的的一個重要目標是維持和擴大加盟商數量。本文指出,連鎖商與加盟商在開展交換時雖會簽訂顯性契約,但會在交換中建立起關系契約,展開超越純經濟交換的社會交換。本文進而提出,加盟商的某些特定關系行為構成了“加盟商公民行為”,且傳播“正向口碑”、擁有強烈“留存意愿”這兩種公民行為將有助連鎖商維持、擴大加盟商數量。為了促進這兩種公民行為,連鎖商要保證投入充足的資源來搜集消費者信息、開展市場形勢分析,不斷充實和完善已有信息,增強所傳遞信息的有用性。連鎖商還要始終與加盟商保持密切溝通,加強對加盟店工作人員、尤其是經營負責人的培訓,從而確保所傳遞信息能被完全理解。不僅如此,連鎖商還要避免給加盟商分攤過多費用,要讓加盟商感到它們之間的收益分配是比較公平的。連鎖商要避免基于某些因素,比如私人關系,給予某些連鎖商特別待遇,要盡量“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加盟商。以上做法將促使連鎖商在關系管理中獲得長期經濟收益。
參考文獻:
1. Bolino, M. C., et 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Orga- nization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2, 27(4):505-522.
2. Bove, L. L., et al. Service Worker Role in Encouraging Customer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9,62: 698-705.
3.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 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1,18(1):39-50.
4. Cook, K.S., Hegtvedt, K.A. Distributive Ju- stice, Equity, and Equal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3,(9):217-241.
5. Grunbagen, M., Dorsch, M. J. Does the Fr- anchisor Provide Value to Franchisees?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Value Assessments of Two Franchisee Types.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2003,41(4):366-384.
6. Heide, J. B., John G.. Do Norms Matter in Marketing Relationships? The Journal of Marketing, 1992,56(April):32-44.
7. Hui, C., S. S. K. Lam, et al. Can Good Citizens Lend the Way in Providing Quality Service? A Field Experi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1,(44):988-995.
8. Karim, J. Emotional Labor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esting the Mediatory Role of Work-Family Confli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2009,11(4):584-598.
9. Perez-Nordtvedt, L., Kedia, B. L., Datta, D. K., Rasheed, A. A.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Cross-Border Knowledge Transfer: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8, 45(4):714-744.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青年基金(項目號:71002031);上海教委科研創新基金(項目號:12ZS073)。
作者簡介:翟森競,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高維和,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2012-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