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張居正的兩本觀點對立的史著
○岳金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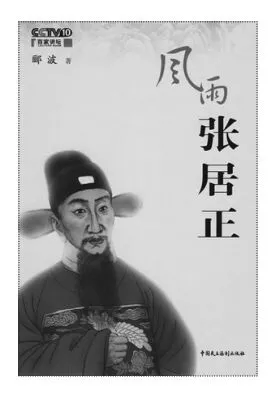
《風雨張居正》,酈波著,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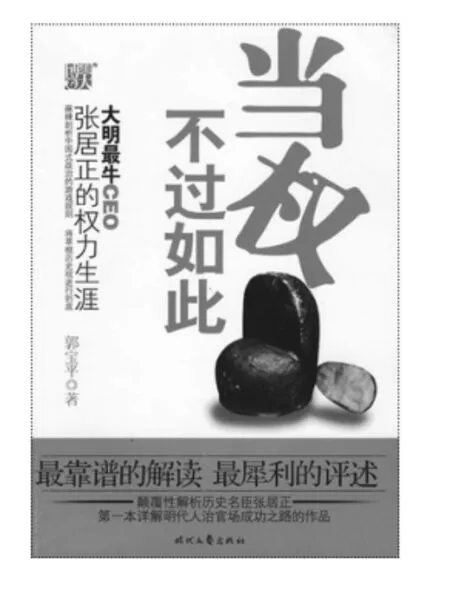
《張居正的權力生涯》,郭寶平著,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兩本有關張居正的史著幾乎同時面世:一本是酈波在央視“百家講壇”講述的史傳《風雨張居正》(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另一本是郭寶平撰寫的史評《當權不過如此:張居正的權力生涯》(時代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經過仔細品讀和反復思考,我覺得兩書的共同特點是通俗易懂,可讀性強,但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分歧乃至對立。
歷史定位的差異
張居正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沒有一個準確的歷史定位。到“文革”時期“評法批儒”,張居正被授以政治家和改革家的頭銜。改革開放后,十所高校編寫的《中國古代史》教材正式把張居正定位為與商鞅、王安石并駕齊驅的改革家,由此成為主流觀點。酈著進而把張居正定位為超過王安石的“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家”。該書從吏治、考成、國防、馭將、清丈、條鞭、整頓驛遞等方面加以肯定和頌美,認為張居正“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唯一一次徹頭徹尾的成功的改革家”,“明朝276年的歷史,這尾巴上的76年都是靠張居正一人之力才賴以延續的”。而“王安石變法卻是以徹底的失敗而告終的”,“宋代之所以滅亡,根源都在于王安石那場失敗的改革”。張居正是超過王安石的真正改革家。
與酈著不同,郭著認為張居正是整頓派。張居正“施政基本上是以整頓為基調的。他的立足點不是改革,而是整飭紀律,恢復祖制的活力”。該書對改革和整頓作了嚴格的區分:改革是制度的創新,整頓是祖制的恢復。由此肯定王安石變法是突破祖制、創制新法的真正改革;而張居正推行萬歷新政的諸多內容,都是祖制的恢復和整頓,“不應列入改革范疇”。有的連整頓也說不上,如禁講學、毀書院,則是“對時代潮流的反動”。唯一有新意的是考成法和條鞭法。考成法擴張和強化了閣權,“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但消除了科官“對政府的監察職能”,破壞了祖制“小大相維”的制衡原則,“這是政治上的倒退”。一條鞭法“不是張居正的發明”,在張居正還是五歲孩童的時候,就由桂萼創始并由傅漢臣等人推行了。在隆慶、萬歷時,一些地方官員如龐尚鵬、王宗沐、劉光濟、海瑞等多人在所轄地區以至全省范圍內的推行,一條鞭法漸次盛行。但是張居正在執政后的七八年間,一直持猶豫、搖擺甚至壓制的態度,萬歷九年(1581)方才明令全國推廣,十年(1582)張居正死后,直到明末仍在持續推廣。清丈田土同推行條鞭基本上是同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而且兩項措施的作用也是有限的。由此可見,張居正只有推廣之勞,并無創始之功,所以不能稱為改革家。
明史專家毛佩琦認為:“張居正是明朝歷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卻夠不上一位改革家。”因為他“沒有制定具有變革意義的新法”,“只是對舊制度修修補補,使其得到加固,延緩了它的壽命”。(《張居正改革,一個神話:為張居正正名》,《晉陽學刊》2010年第4期)臺灣學者柏楊早就指出:推行萬歷新政的張居正,“他沒有公孫鞅當時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聲望,更沒有觸及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過像一個只鋸箭桿的外科醫生一樣,只對外在的已廢弛了的紀律加以整飭”。(《中國人史綱》中冊,同心出版社,2005年,P100)。在當前張居正的一片頌揚聲中,這些觀點無疑是引人深思的一副清醒劑。
高拱評價之分歧
大凡有關張居正的研究,無不涉及前任首輔高拱,兩書也不例外。酈著提出高拱“雖然做了不少事,但因為個人的眼光問題,他做的事基本上都是‘就事做事’,在制度上的變革力度并不大”。他“往往是拆東墻補西墻,許多方面都沒有解決根本問題”。因此,該書三處提到高拱留給張居正的是一個“內憂外患的爛攤子”。他罷職之時,“國庫空虛到了極點,戶部連國家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了,每年財政赤字就有200萬兩到300萬兩”。隆慶后期的俺答封貢,“方案的提出、步驟的細化、問題的解決思路,無一不出自張居正的手筆”。“張居正是策劃者,高拱是支持者”,高的功勞“不宜過分夸大”。這是酈著對高拱的總體評價。
而郭著不同,認為“高拱的人品操守、膽識才干、改革意識,都是張居正所不及的”。在他執政的兩年半里,創行了吏治、司法、軍制、邊防、水利、漕運、海運等全方位的改革。他不僅有《除八弊疏》的施政綱領,而且還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只,開海運,“實行對外貿易”。高拱“特別重視發展工商業”:“親自到市場調查研究”,“了解實情”。他還大力支持和推行丈田均糧和一條鞭法的賦役制度改革。而張居正執政的十年,“并沒有完全繼承高拱的改革方向”。特別是他“對高拱的開海運、開放對外貿易主張暗自抵制”,重新恢復海禁,推行閉關鎖國的基本國策。郭著的評價是“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張居正是官僚、政客,實用的保守主義者”,“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張居正基本上屬于整頓派”。至于改革的效果,以經濟改革為例,高拱罷官前的隆慶五年(1571),太倉銀庫歲入310萬兩,歲出320萬兩,歲虧只有10萬兩,比隆慶元年至四年(1567-1570)平均歲虧206.6萬兩,減少了196.6萬兩(參見樊樹志《萬歷傳》,人民出版社,1993年,P118)。這就為張居正執政時期國庫盈余奠定良好基礎。張執政后繼承了高拱的與俺答維和的局面,有其功勞和貢獻。“但是,他享受的和平‘紅利’,超過了他的貢獻”。張居正接手的不是一個“爛攤子”,而是“坐享了高拱遺下的和平‘紅利’”。
所持價值觀的差別
歷史研究不能為研究而研究,總要有個目的,服務于現實。酈著提出:從萬歷新政的全局來看,“張居正的整體思路,是以推行清丈田畝和推行一條鞭法的經濟改革為中心的,另外再以穩定北部邊防和施行考成法為兩個基本點”。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提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顯然,這是牽強附會,是為嚴謹的學者所不取的。
與酈著不同,郭著的價值分析更貼近現實、貼近生活。全書把張居正作為人治典型,對其專制獨裁政治進行了猛烈抨擊。張居正迷信、崇拜、濫用權力,精諳牌理卻不按牌理出牌,“玩上司兼好友于股掌中”,一舉奪得首輔大權,登上了權力巔峰,“連皇帝也敬他三分怕他七分”。他執政十年所發生的諸多政治事件,都是他一人說了算,把人治推向了巔峰。郭著提出:“在人治官場,專制社會,權力、地位與其所受的監督程度成反比。權力越大,地位越高,受到的硬約束、剛性監督越少。”劉臺曾指控張居正以權謀私、鉗制言路、排斥異己、擅權專斷,上臺不幾年,老家富甲全楚,府邸建得豪華無比,揭露他“貪污受賄,不在文臣,而在武將;不在中央,而在邊防”。該書認為“掌握不受監督、無所不能的權力”,必然陷入權力的誤區,即“不受監督的權力必然腐敗”。郭著對張居正執掌絕對權力,實行專制政治的深刻批判,具有現實意義。
秉持歷史觀的對峙
酈著崇尚英雄史觀,把張居正作為理想化的英雄化身來歌頌和拔高的,將其塑造成“高大全”、“偉光正”的英雄偶像和精神標桿。為了塑造英雄:一是公然宣揚英雄創造歷史,認為晚明社會60多年的歷史“都是靠張居正一人之力才賴以延續的”。其實,張居正最后十年的所作所為恰恰加速了明朝滅亡的到來。歷史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張居正推行萬歷新政中對荒政、邊政、黨爭和海禁等幾個方面存在有大的失誤(參見南炳文《“盛世”下的潛藏危機:張居正改革研究》,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導致了明朝滅亡的加速到來,明亡的直接原因是荒政引起的饑民起義和對女真族政策的失誤。二是否定歷史事實,否定張居正勾結馮保驅逐高拱,否定在王大臣案中張居正謀劃陷害高拱的陰謀,等等。三是編造歷史,如張居正曾參與徐階推倒嚴嵩的“政治大決戰”,并起“領導作用”;編造高、張曾在“香山盟誓”;精心描繪高、殷(士儋)“兩宰相打架事件”;大講徐瑛(徐階之子)霸占趙小蘭,使其家破人亡的京戲虛構故事。四是對張居正失律失德失誤,加以辯護。另外,酈著硬傷迭見,漏洞百出,說明作者對明朝制度缺乏整體把握,對相關人物缺乏基本了解。總之,該書是一本張揚美化英雄主義的作品。
與英雄史觀相反,郭著堅持草根史觀,正如該書封面所載要“將草根歷史觀進行到底”。草根史觀就是平民史觀。這種史觀的核心理論是,草根平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的主體;民意是解釋歷史的基礎,民利是評價歷史的價值標尺。這種歷史觀的特點是由下而上地來研究歷史人物,因此總是堅持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的,既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至于肯定多少和否定多少,那是由歷史人物的活動對社會發展的作用所決定的。郭著從草根史觀出發,在掌握大量可靠史料的基礎上,從歷史與政治相結合的視角,對張居正的權力生涯、功過是非進行了多側面、多層次、全方位的麻辣剖析和精當評述。該書并沒有否定張居正的事功,認為他是歷史上最成功的讀書人,從一個出身低微的寒門之后,躍上國家權力巔峰,并“以個人的手腕和力量推動銹跡斑斑的國家機器運轉起來,確實很不容易”;張居正有能力,很勤政,“他以富國強兵為職志,對國家有相當貢獻”。但是,他在取得重大成就的過程中,也做了不少“別人不敢干的壞事”。張居正“獨掌中樞后,又專權獨斷,驕盈自用,順昌逆亡,集中體現了人治官場高官顯貴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分裂人格,集高尚與卑鄙于一身”:“一邊高喊反腐倡廉,一邊卻大肆收受賄賂;一邊高喊節儉,一邊卻奢靡無度;一邊高喊節操,一邊卻忘情于美女裙釵間——他對一切敢于挑戰其權威者都無情打擊,但自己身后也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場。”郭著揭開了張居正權力生涯的歷史真相,不是為了要貶低他,而是為了要揭示崇尚公平、正義的草根史觀。
在當今頌揚張居正的熱潮中,郭著以不同聲音、對立觀點面世,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只有不同甚至對立觀點的出現,才能凸顯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也才能將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