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揚后抑40年
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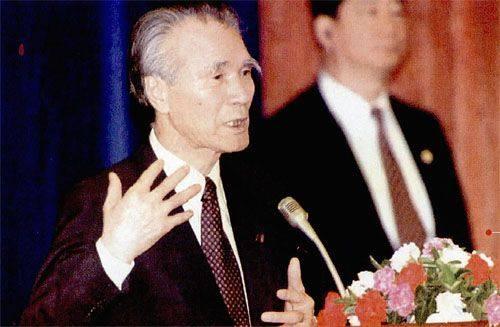
現在的日本政治家,不論是在野黨還是執政黨,已經找不出一個有田中角榮這種氣概的人。小試鋒芒便見好就收,甚至稍遇逆風,便撒手不干了。
直到9月14日筆者登上去日本的飛機前,雖然也感覺中日關系可能會因為日本民主黨內閣在9月11日將釣魚島“國有化”出現較大的后退,但沒有想到會變得如此尖銳對立。
“日中關系出現這么大的變化,該拿什么方法來處理,我們也是一籌莫展。”南村志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南村志郎1957年開始和中國做貿易,后來追隨政治家西園寺公一,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過重要貢獻,建交后一直活躍在日中友好第一線。二戰前,西園寺公一曾經支持過軍國主義,戰后為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率全家移居中國,南村志郎是西園寺辦事處的主要負責人。
1972年9月29日,在兩國官方和民間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實現了邦交正常化,算起來至今已經有40年。
按理說“四十不惑”,但中日關系并沒有因為有了四十年邦交正常化的歷史,就成熟起來。兩國該如何處理相互關系,還處于摸索之中。
我自己是從1972年開始學習日語的,通過日語看到了一個我們完全不知道的日本。上大學學習日本文學,之后是從事日本問題的報道,去東京留學,在那里工作了數年后,再回到中國當記者,經歷中日關系中的主要變化。
中日友好的熱潮、日本向中國投資轉移技術的往事歷歷在目,我在親眼看到中日經濟關系走向緊密的同時,也看到了兩國之間發生的教科書問題、日本首相參拜供奉了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艦艇撞擊中國漁船、釣魚島沖突等一系列事件。
曾有過80%以上的日本民眾支持并親身參與中日友好活動,但現在隨著日本媒體疾風暴雨般地長年以負面為主地報道中國,現在80%以上的民眾對中國沒有好感。如果近期進行民意測驗的話,這個數字可能會超過90%,打破交惡記錄已經確定無疑。
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年,成果來之不易,但在日本民主黨內閣、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對釣魚島問題的炒作后,今天的中日關系已經大大倒退。
從歷史上看,中日交往了3000多年,四十年也許算不上什么。走過四十年邦交正常化的中日兩國,發生一些曲折,也許在情理之中。
七八十年代的友好熱潮
1972年9月29日,報紙廣播中傳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消息。我那年在北京上中學。雖然從1966年就開始上小學,但好像沒有在教室里學過什么。1972年這年學校開始教書了,和過去的6年天天號召革命,時刻準備去游行,已經大不一樣。
我所在的中學,10個班中有5個學日語。并非是國家有特殊政策,是因為有幾位比我們大三、四歲的外語學校中專畢業生,分配到了我們這所中學,他們學的是日語。
在學校里學了幾個日語字母后,教學又開始變得斷斷續續的了。但也正是在1972年,北京開始有了日語廣播講座,可以跟著廣播學習。后來我才知道,北京的日語廣播講座是得到日本方面支持的。包括教材的編寫、日語發音訓練等等,播音員從日本專家那里學習了不少播音方法。
在大多數時候只能讀一些領導人語錄的時候,廣播講座中的一些小故事,偶爾播放的一首外國歌曲,和我們日常接觸的宣傳是那么的不同,我自己主要聽廣播講座,竟然把日語學了下來。
中日友好在1970年代是主流,我常常能從報紙上看到黨和國家的領導會見日本政治家、企業家。每次會見都是放在頭版,非常醒目。
大學畢業工作了7年后,我在1989年去日本留學。曾經和我的導師、慶應大學經濟學教授井村喜代子談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北京開設的日語廣播講座。井村喜代子則是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就參加了恢復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國民運動。
“中日永不打仗,與中國結成統一戰線,幫中國建設新社會,這些是我們從事邦交正常化的動力。”井村喜代子回憶說。作為在二戰中親眼看到過美軍對東京的地毯式轟炸的人,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反對戰爭是二戰后年輕人共同的奮斗目標。中日邦交正常化,有這些人的熱情支持。
邦交正常化以后,有數次日本工業品展會在北京展覽館等地舉行,有太多的人從展會上看到了中日工業上的差距。向日本學習,首先從學習日語開始的。1970年代文革尚未結束,但學習日語蔚然成風,那其中有不少是為了了解日本,盡快讓中國也走上經濟強國的強烈愿望。
中日間的團結意識,在1970年代、1980年代十分強烈。共同的戰爭體驗,實現工業現代化的愿望,是這個時代的特點。我記得在學習日語的廣播講座中,就有不少是談戰爭、談科技的內容。從中日友好的熱潮可以看出,中日雙方互相敬重對方,有種建立新東亞經濟社會的愿望。
1970年代,中蘇關系非常緊張,而中美關系已經走向緩和,中日關系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發展得非常順利。
改革開放與日本資金技術
在東京新橋車站不遠處,有一棟不太高、外表已經有些破舊的樓房。很多曾在中國監獄中長期服刑的日本舊軍人,他們回到日本后參加了一個組織:“國際善鄰協會”。現任理事長是古海建一。
古海建一的父親古海忠之是中國撫順監獄中最高級別的日本戰犯。1941年古海忠之接下了岸信介手中的偽滿洲國總務廳次長的職位,在1945年主要官僚逃回日本時,他負責在東北地方與蘇聯紅軍作戰,后被蘇聯紅軍逮捕,并在1950年交給了新中國。到1963年為止,被監禁在撫順監獄。
“我從英國留學回到日本后,進入東京銀行工作。到了1963年才見到被釋放回來的父親。那時父親已經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四處奔走,呼吁日中邦交正常化。”古海建一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中國將監禁在撫順監獄的最高戰犯,改造成了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四處呼吁的友好人士。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后,由于東京銀行是日本最大的外匯銀行,“我開始處理大量的中國業務。”古海建一說。那時他已經是東京銀行的高管,負責著大量中國方面的業務。父親古海忠之深深地影響了古海建一。
日本從這一年開始對中國提供低息貸款(ODA,政府開發援助),支持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政府款項經過東京銀行匯到中方銀行來。
“我去山西看過那里的煤礦,去湖南內陸看過水庫建設的狀況。年輕一些的銀行職員,會深入到更遠的地方去具體考察項目的可行性,他們提交報告后,日本的款項便以很低的利息融資到中國來。”古海建一說。
“從1978年到2008年,30年中有3萬多億日元以低息貸款的方式來到了中國。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中國外匯奇缺的時候,這些外匯緩解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燃眉之急。”擔任過ODA項目翻譯工作,現任國家發展銀行高級局長的袁英華在8月31日的中日美經濟論壇的主旨演說中說。
在北京,北京機場、中日友好醫院、中日青少年活動中心等等的建設,都和ODA有關。大量的港口、鐵路、機場、水壩的建設,使用了ODA貸款。在基礎設施建設好了以后,才有了1990年代以后日本企業對華投資的熱潮。
從“不忘”到篡改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二戰剛剛過去20余年,人們對戰爭的記憶尤為深刻。
“該如何總結戰爭給日中兩國帶來的沉痛教訓,兩國的外交家都拿出了自己的智慧。特別是中方,周恩來總理多次談到,對于過去的那場侵略戰爭,中國方面可以不多說,但日本方面不該忘卻。這是邦交正常化能夠順利推進下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南村志郎說。
當年,丁民擔任中國外交部日本科科長,參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周恩來總理提出了中日兩國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原則,后來還有了中日不再戰的說法。”丁民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
從事中日關系報道的日本老記者橫堀克己,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最早來中國的日本記者之一。他采訪過大量的相關人士,“那個時候的中國主要領導人,都直接參加過抗日戰爭,深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沉痛災難。日本的政治家、外交官也對戰爭有著自己的深刻體驗,不再戰等說法,很快就能得到大家的同意。”橫堀克己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但是日本方面很快發生了變化。
1982年,日本一些出版社出版的歷史教科書,開始將侵略華北改成了日本軍隊“進出華北”,欲將侵略的事實掩蓋起來,中日間的教科書事件成了一件大事。日本一些學者要公開否定戰爭的性質,中國方面開始向日本方面提出嚴正交涉。
今年9月,我在東京見了國立高中的歷史教師小原高久,聽他講了高中歷史教育的現狀。小原高久在自己的歷史課程中,積極地加入了南京大屠殺等內容,他自己也多次來北京、去南京考察中日戰爭歷史。
“必須把真實的歷史告訴下一代。”小原高久說,不忘那段侵略史,是日本歷史教育的一大責任。
但是到了2001年小泉純一郎出任日本首相后,去參拜供奉了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成為了中日外交中的一個新問題。我當時還在東京工作,看到民眾對參拜有支持也有反對。日本不是不忘那場侵略戰爭的責任,而是用過去的戰爭來挑釁周邊國家的國民感情。
日本國家領導人以參拜靖國神社的形式,進一步否認日本的戰爭責任,中日相互信賴的前提,在日本那里已經逐步消失。
另一個邦交正常化時堅持的前提,領土問題的“擱置爭議”原則,也開始在這些年漸漸失去了作用。
日本研究中日關系的學者矢吹晉,找到了一些中日邦交正常化時,對領土問題的討論資料。他認為對于釣魚島問題,中日雙方有“擱置爭議”的默契。
日本外務省負責情報分析的原外交官孫崎享,分析了1975年的《中日漁業協定》和2000年版《中日漁業協定》。他認為,對北緯27度線以南地方的漁業規定,實際上就是中日兩國各自取締各自國家的漁船,日本發現違反漁業協定的中國漁船,將通知中國漁政取締,中方亦然。
但到了2010年,日本開始用“國內法”取締中國漁船,非法扣押中方船長。領土問題的擱置爭議論,也開始破裂。到了2012年9月11日,日本將釣魚島“國有化”,就更是不承認擱置爭議的默契了。政治上的互信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時候,以歷史問題開始,并通過讓領土問題尖銳化的方式最后幾乎喪失殆盡。
在政治上的互信消失后,經濟的互惠體制,今天正面臨著巨大挑戰。
中日經濟處于互補狀態。“我們對中日的相關企業做了大量的調查。中國擅長的制造內容與日本基本上不在同一個范圍內。中日產業之間的互補關系要大大超過兩國產業的競爭關系。”熟悉日本產業的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秘書長顏志剛說。
“日本必定會減少對中國的投資,讓中國本來已經開始下滑的GDP,出現更大的下滑。”一直積極支持釣魚島“國有化”政策的《讀賣新聞》,在9月23日的社論中擺出了在經濟上制約中國的態勢。邦交正常化以后,最先來中國投資辦廠、向中國轉移技術、耕耘出中國市場的日本,忽然開始強調從經濟上制約中國。
世界經濟在1975年前后走入低潮,歐洲及美國基本上沒有出現跳躍性的發展,但日本的發展一直持續到了1993年,比歐美長了將近20年。1993年日本經濟開始衰退,但民眾的生活并沒有出現明顯的質量降低,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日本有中國這個極大的市場。今天日本在經濟上也與中國的關系漸去漸遠。
民主黨的“卡拉OK政治”
筆者在東京上大學的1978年,大平正芳任日本首相,其后的34年中,除了中曾根康弘、小泉純一郎以外,能夠留下強烈影響的并不多。
日本政治評論家鹽田潮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到了自民黨末期,日本政治愈發卡拉OK化,基本上都是些非專業的政治家登臺獻歌、唱別人唱過的歌,并沒有自己的政治主張。”
我自己雖然一直從事日本問題的報道,但很難把這些年日本當過首相的人從頭到尾按順序數下來。民主黨大佬小澤一郎在一次演講會上,談到日本政治時說,他自己也數不清楚這些年出了多少首相、大臣。你方唱罷我登場,看不出日本政治有哪些特色。
除了在2009年的大選中感受到了某些熱情外,這十幾年日本選舉都很冷清。那時鳩山由紀夫率領的民主黨,勢如破竹,奪取了自民黨掌管了54年的政權。“東亞共同體”概念,讓人們對日本有了新期待。
但現在看來,2009年以后的民主黨鳩山內閣也不過是卡拉OK政治中的一曲。
“卡拉OK最大的特點是唱一曲人們熟悉的歌曲,而不需要有自己獨到的地方。”鹽田潮說。
日本社會需要有政治家在保證現有福利、雇傭等體制的前提下,實現社會改革,讓社會重新具有活力。但是日本經濟的全球化,國內產業開始大量轉移到了國外,而泡沫經濟帶來的長期失落,讓日本不進行徹底的改革,不在改革中承受很大的痛苦,就不能尋找到新的發展道路。日本社會不愿意在承受痛苦的情況下進行改革。政治家只能唱一些選民聽慣了的曲子,用特別激烈的對外攻擊的方式,來滿足選民不承擔任何苦痛的改革。
“本來就缺少行政經驗,但要擺脫官僚對政治家的控制,推行一系列的改革,民主黨比自民黨更不靠譜。”日本一家上市大企業的高管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不斷提出迎合選民需求的口號,而政權并不能完成政策目標,民主黨和末期的自民黨內閣一樣,開始不斷替換新的黨首、首相。
1972年9月,田中角榮來中國前,一根一根地剪自己的胡子,他下定決心要在自己的內閣期間,實現邦交正常化。“做好了回來后被右翼刺殺的準備。”邊剪胡子,田中角榮邊說。
現在的日本政治家,不論是在野黨還是執政黨,已經找不出一個有田中角榮這種氣概的人。小試鋒芒便見好就收,甚至稍遇逆風,便撒手不干了。在日本核電站問題上,民主黨提出了“零核電”政策沒有幾天,便正式宣布撤銷了。
只不過想唱首好聽的歌給選民聽聽,不可太過較真。今天的日本政治家在外交上,在內政上已經缺少了有大戰略的人才。看看在野的自民黨選舉,能得出同樣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