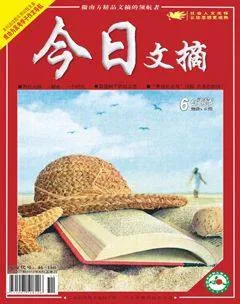兩位大師,一幅畫,一個時代
姜珂
1925年,徐悲鴻攜油畫數十幅參加田漢在上海舉行的“消寒會”展覽,與郭沫若相見于會場,均有恨晚之嘆。
歐債危機不知何時到頭,中國藝術市場則在大洋彼岸“占領華爾街”的呼聲中迎來了秋拍。在延安飯店舉行的北京保利秋拍預展,又讓我們看到了中國藝術市場強勁無比的勢頭。比如“中國近現代書畫十二大名家夜場”,已經是保利主打的專場,在業界有著良好的品牌效應。而此次以徐悲鴻創作于1951年的《九州無事樂耕耘》為重中之重。此作系徐悲鴻得知郭沫若出席“第三次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并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被授予“‘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金質獎章”之后,欣喜萬分,抱病為郭沫若所作的宏幅巨制,而且徐悲鴻利用畫中的人與景物,巧妙地將當時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歷史背景隱喻于畫面之中,有豐富的歷史與人文信息。
徐悲鴻出身貧寒,對農民的生活是有切身感受的。牛就成了徐悲鴻特別鐘愛的題材,在抗戰期間的顛沛流離中,他也多次借牧牛圖來表達對平靜生活的憧憬。呈現在我們眼前的這幅《九州無事樂耕耘》,以樸實的藝術語言表現對象的現實性和典型性,呈現普通生活中所流露出的情味,涵容大自然內在的生命律動。
農民和牛以寫生的手法描繪,三個農民均上了年歲,但仍不輟勞作。最前者牽牛犁地,其雙腳邁開,身軀前傾,手掌攥緊,正耗盡全部力氣驅牛犁地,臉部和手部的肌肉因凝聚力量而呈現出收緊之感,這個瞬間的動態生動逼真。后兩者為一農婦和一農夫,均在鋤地,一揮鋤,一彎腰,動作幅度并不大,表情亦平靜,與前者形成反差。使人在某種程度上感受到農民生活之辛苦、激烈的一面,以及平淡無奇、千篇一律的一面;使人體味到出普通生活中的偉大之處,從而對辛勤勞作的農民充滿敬意。整幅畫將西畫中的造型方法和中國畫的筆墨相結合,既有準確生動的造型,又有靈活多變的筆墨,乃為一幅結合中西畫法精髓的寫實主義佳作。
此幅作品還見證了徐悲鴻和郭沫若之間的友誼。據廖靜文回憶,徐悲鴻與郭沫若相識于1925年,當時徐悲鴻攜油畫數十幅參加田漢在上海舉行的“消寒會”展覽,而與郭沫若相見于會場,均有恨晚之嘆。展后徐悲鴻仍回巴黎繼續未完的學業,抗戰爆發后,郭沫若和徐悲鴻均遷居重慶,時相往來。
抗戰勝利后,郭沫若撰寫《陪都文化界對時局進言》一文,呼吁成立有共產黨在內的民主聯合政府,取消特務組織,給人民多項自由。成文后郭沫若請徐悲鴻一覽,徐立刻簽名表示支持。郭文在《新華日報》發表后,引起蔣介石震怒,郭徐二人同時受到特務威脅而不屈服。徐悲鴻和郭沫若的友誼也因此而加深。
1946年,徐悲鴻和廖靜文和在重慶結婚,郭沫若便是證婚人。1949年,第一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在布拉格召開,郭沫若是中國代表團團長,徐悲鴻和許多文藝界人士均出席了。1953年,徐悲鴻患腦溢血逝世,郭沫若書寫了“徐悲鴻紀念館”的牌匾和八寶山徐悲鴻的墓碑。
《九州無事樂耕耘》見證了這兩位愛國文人之間的珍貴友誼。1951年,這件作品完成后,徐悲鴻便立刻送給了郭沫若。郭沫若當時住在北京西城大院胡同,此后其一直將此畫掛在家里。郭沫若去世多年后,其家屬仍然珍藏著這幅畫,直到1996年從拍賣會上流入民間收藏。
(李新薦自《新民周刊》)
責編: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