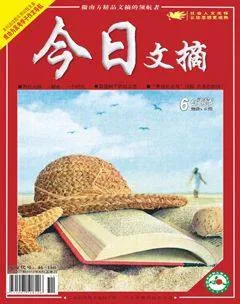北國紅豆
段華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唐代詩人王維的這首詩,千百年來打動著多少人的心啊。我每一次到南方,只要季節合適,都會找一棵紅豆樹,站在樹下凝望很久,讓思緒進入遼遠的空間。
印象中的紅豆,就在南國扎根了。
有一年,到長白山自然保護區出差,正是七八月份,因為乘坐汽車時間太長,車便停在路邊休息。我下車后,一邊活動手腳,一邊在路邊溜達。路兩側是茂密的森林,野黃花靜靜開放。這正是一年之中長白山最美的季節。我情不自禁地走下路基,到不遠處樹木稀疏的山坡上。林子很靜,松濤和偶爾的鳥叫聲更顯出寂靜。突然,在草叢之間,我發現叢叢鮮紅的如豆粒般大小的果子,顆顆圓潤晶瑩,在花草間,如同沉靜的少女。
我大著膽子摘了一顆,放進嘴里,酸甜適中,涼意可口,漿水充盈。我忍不住歡呼了一聲,又摘了一把放進嘴里。
聽到我的喊聲,陪同的自然保護區的人過來,告訴我這種紅色的小漿果叫紅豆,大家習慣上叫北國紅豆,長在灌木叢中的草上,而王維筆下的紅豆,都是長在樹上,雖然果實很相近,從植物學上差別卻很大。
我才明白,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從未踏足過東北大林海的王維,根本想不到這里的紅豆雖然與他筆下的紅豆不是一個品種,也有鮮紅的相思呢。
后來,到東北大森林里次數多了,我也向當地林業局人士多方請教,才弄明白北國紅豆是什么植物。北國紅豆學名蘿越橘,又名蔓越莓、小紅莓、紅豆越橘,為杜鵑花越橘屬,是一種抗寒性極強的常綠灌木,在我國只生長在長白山和大興安嶺地區,每年的六七月份開花,八月份結出小而圓、紅色的果實。
有一年我到大興安嶺,正趕上北國紅豆采摘的季節,這種野果子就成了我每走一處都能吃到的美味。林區人熱情,每天讓我喝醉酒;喝醉了酒,把一碗北國紅豆洗凈后,放上一些白糖,一勺一勺放進嘴里吃,立刻酒意全無,又可以面對森林,席地而坐,把酒臨風,海闊天空了。
然而,大興安嶺人并不叫它北國紅豆,他們稱它為“雅格達”,頗有點洋里洋氣的意思。其實,這是鄂倫春語,意思是“相思果”,這無意間正應了王維的那句詩意,使北國紅豆有了文化的意蘊。以后,看到綠草叢中的紅色果實十分的顯眼,林區又產生出一句歇后語:一枝紅豆出墻來——對外開放。真是十分有趣。北國紅豆營養十分豐富,特別是維C、維E比任何小果都高。冬季在深山中施業的林業工人,很大一部分營養就來自于它。
讓我對北國紅豆記憶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冬季我到大興安嶺。冬季的時候山上雪達一米多厚,山林肅殺,是真正的林海雪原風光。我來到角刀木林場,想去看一個正在施業的小工隊。
“角刀木”是鄂溫克語,意為河底布滿大石頭的河,從這也可以看出,那里的交通并不方便。出林場場部二十公里,車就不能開了,我們只好下車,冒著零下四十多攝氏度的嚴寒,沿著花道(林業俗語:山場中的集材道)步行去施業區。將近三個小時后,我才鉆進了工隊工人居住的工棚,躺到小桿鋪上(林業俗語:用小徑松或樺桿搭的簡陋的床鋪)幾乎起不來了,此時的我又累又餓。正在這時,一個老林業工人給我端過來半碗放了白糖的北國紅豆,熱情有加地說:“吃下去吧,過會兒就消除疲勞了。”我驚叫起來,啊,這時候還有北國紅豆?
老工人并不多說話,領我到工棚外邊,扒開一米多厚的雪,奇跡出現了:在這零下四十多攝氏度的深山老林,大雪覆蓋的林下,北國紅豆那綠色的葉子變紅了,而神奇的果子,竟然頑強地默默地生長著,在白雪的映襯下,更顯得紅艷和晶瑩!
現在,北京已是春意漸濃,花兒開始次第開放,而在遙遠的大興安嶺,我知道仍是零下三十來攝氏度,那些工人兄弟們仍在默默地、不為世人所知地工作著,奉獻著。想起了紅紅的山果“雅格達”,我就想起了正在深山老林里工作著的那些工人兄弟。
(余成興薦自《今晚報》)
責編:天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