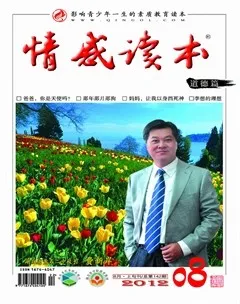血與真相
方亮
我們的任務是說出真相,通過揭露戰爭的可怕,我們絕對能夠、而且可以帶來改變!
——科爾文2010年在追悼殉職記者時發表的演說
2012年2月22日清晨,敘利亞霍姆斯市Baba Amr區,一顆敘利亞政府軍的火箭彈追上了正在撤離的英國《星期天泰晤士報》女記者瑪麗·科爾文,巨大的爆炸為她近30年的戰地記者生涯畫上了慘烈而光榮的句號。與她一起殉職的,還有自由攝影師雷米·奧奇力克,一位來自法國的28歲小伙子。
有一種生活,因為危險,讓人時時體驗腎上腺素激增的快感。就像同樣殉職于戰場上的著名戰地記者羅伯特·卡帕所言:“戰斗可以讓攝影師腎上腺素激增,極易上癮,飲酒、美女、吸毒都無法與它相比。”但因為神圣,這種生活也讓人倍感自豪,就像科爾文所言:“我相信,新聞報道能讓殘忍懂得收斂。”
1954年,卡帕誤踩地雷死在了越南戰場。死亡降臨的一瞬間,他本能地按下了快門,用最后一張照片祭奠自己戛然而止的精彩一生。而當科爾文在敘利亞被炸身亡的消息在微博空間中傳播開來,她那張獨眼遺像被一次次轉發,新聞圈的前輩們回憶著這位同行的點滴。我瀏覽著科爾文生前的一張張照片:在斯里蘭卡丟掉一只眼睛,在開羅解放廣場帶著眼罩海盜般地昂首站立,在利比亞與反抗軍戰士席地合影……
卡帕的愛人“火狐”塔羅曾有言:“有些極優秀的人,他們在戰場上死于非命。有時,我會產生一種荒誕的想法,覺得自己活在世上很不公平。”
面對卡帕和科爾文濃縮而崇高的一生,很多人確實會因為平庸而遺憾。
“拯救了一支軍隊的人”
同類相殘,這可謂是人類最丑陋的現實,戰爭則是這種丑陋的極端表現。當人們懂得反省這種丑陋,社會分工中便也相應地細化出了戰地記者這一行當。人類社會開始為戰爭而訂立公約始于19世紀中葉,而第一位戰地記者也正在此時誕生于克里米亞戰爭中,這當然不是一種巧合。
實際上,若無資本主義報業的發展,第一位記者威廉·拉塞爾恐怕也無法獲得隨英軍一同遠赴俄國克里米亞報道戰爭的機會。當時,拉塞爾所供職的《泰晤士報》在英國正如日中天,讓記者和編輯們成為了英國社會中不可忽視的一種力量。正在此時,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了,這家報紙當然不會放過這一絕佳的報道機會,盡管從來沒有過向戰爭前線派出專職記者的先例。
《泰晤士報》向軍方提出了申請,陸軍司令哈丁覺得不應得罪這家頗有聲勢的媒體。便表示了同意,第一位戰地記者拉塞爾準備好行裝,隨軍出征了。
在此之前,報道戰場上的事情從來都是職業軍人的事情,他們往往將戰報當做新聞發回國內。所以,當軍營中突然出現一個操著鋼筆而不是鋼槍的男人的時候,士兵們都投來輕蔑和懷疑的目光。一位旅長發現,他的軍營中居然住著一位記者,當即把拉塞爾的行頭扔了出去。所有這些蔑視和不配合都給拉塞爾的工作帶來了極大不便。
好在,拉塞爾并未將報道的重點放在戰爭的宏觀進程上,真正吸引他的是戰爭中的士兵和戰爭的種種細節。至于英軍勝了還是敗了?打到了哪里?戰況如何?官方的戰報里都不會少的。而恰恰是細節才能填補公眾腦海中有關戰爭想象的空白。
他仔細地對英軍的軍營進行了觀察,然后寫出這樣的報道:“軍營所在的這個城鎮,污穢、恐怖,到處都是生命垂危的土耳其人。擁擠的小巷,散發著惡臭的棚戶。死者被胡亂掩埋,有的甚至緊挨著活人堆放在一起。這里的醫療環境之差令人無法想象,醫院缺少最基本的設備,而且因為缺少照料,病人們只能相互幫助。”
他發回了一系列此類報道,并且在其中一篇文章中問道:“在英國就沒有愿意來幫助這些命苦的士兵的婦女嗎?”這篇報道引起了很大反響,當即便有一群女性醫護人員趕到了前線,照料傷員。她們中有一位叫做南丁格爾,正是她奠定了現代護理體系的基礎。
彈片與白金膝蓋
歷史上第一位戰地記者出色地完成了人類覺醒良心交給他的任務——揭露戰爭的罪惡與丑陋。功勛與榮耀的背后自然是傳奇的流傳。親歷戰爭,為了能夠將戰爭傳遞得分毫畢現,當所有人都在遠離戰爭時,戰地記者們卻要竭盡全力地靠近這只將一切吞噬的巨獸。有了這份勇敢,傳奇的流傳就是必然。
1917年,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厄內斯特·海明威正趕上美國參加一戰,擺在這個少年面前的有三條路:參軍、上大學、工作。他左眼有毛病,這堵死了參軍的道路。最終,他進入了當時美國最好的報紙之一《星報》,開始了自己的記者生涯。在報社工作半年后,他抑制不住對經歷戰火的渴望,只身前往意大利。身份是一名紅十字會員工,但戰場上的所見所聞最終還是成為了其作品的素材。
他與戰爭最初的一次接觸極為短暫,只有一個星期。在這個星期最后一天的下午,他帶著巧克力和香煙來到前沿陣地,把東西分發給士兵們,然后用蹩腳的意大利語把士兵們逗得大笑不止。
敵軍盤踞在對面,不時地向這里打槍、放炮。所有人都習慣了戰火中的日子,不為所動,接著聊天。但是到了夜里,敵人打得更歡了。一個不留神,一枚炮彈在海明威不遠處爆炸開來,一段枯木炸飛過來,直接擊中了他的腦袋,這位握著鋼筆而非鋼槍的戰士倒了下去。
他感到天旋地轉,但仍可目視四周。他看到一名戰士倒在離自己不遠的地方,似乎在大聲地哭泣。海明威費力摸過去,把這名戰士扶起來,用后背撐著他,向指揮所走去。他的一條腿已經沒有了知覺,只是機械地挪動著。敵人又是一陣掃射,一顆子彈打進了他的膝蓋,海明威又倒下了。
此時,距離指揮部只剩下了100多米。后來,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最后這100多米他是怎么完成的,反正他在將背上的戰士送到指揮部后便暈倒了。
當他醒來,已經躺在了后方的醫院里。把他炸傷的炮彈里包著大量的金屬顆粒,醫生從海明威的身體中取出了200多塊彈片和金屬物,有一些實在取不出來的干脆就留在了里面。他的膝蓋被打爛了,后來醫生不得不給他換上了一個白金的金屬殼,如果那可以被稱為膝蓋。
3個月后,動了十多次手術的海明威幸運地保住了一個還算比較完整的軀體。他挺過了這次中斷了其第一次戰爭生涯的劫難,此時,他再過幾天就將年滿19歲。
這次寶貴的戰爭記憶成就了海明威日后包括《太陽照常升起》和《永別了,武器》等多部作品。世界開始以一個作家的身份來看待海明威,但誰都無法否認,在戰地記者圈子里,他已然開始向殿堂級人物邁進。
當法西斯開始肆虐歐洲,海明威結束了他生命中難得的一段田園詩般的生活,趕赴西班牙戰場。在那里,他結識了另一段傳奇——羅伯特·卡帕。
張彥摘自《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