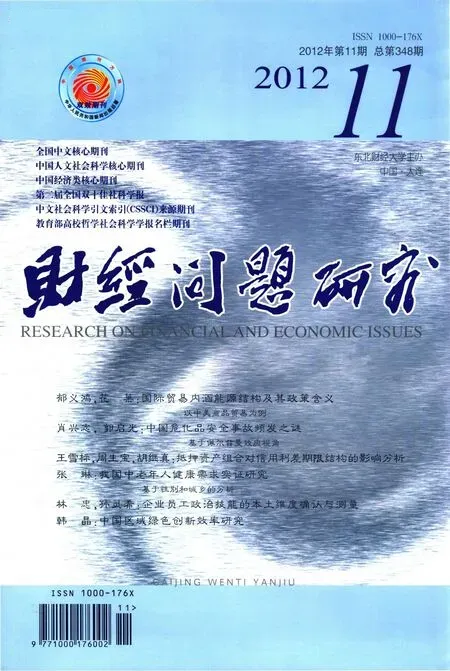中國危化品安全事故頻發(fā)之謎——基于佩爾茲曼效應(yīng)視角
肖興志,郭啟光
(東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產(chǎn)業(yè)組織與企業(yè)組織研究中心,遼寧 大連 116025)
一、引 言
關(guān)于安全規(guī)制的有效性問題,國外學(xué)者進(jìn)行了積極探索。在美國職業(yè)安全與衛(wèi)生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以下簡稱OSHA)建立之初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工人傷亡率穩(wěn)步下降,導(dǎo)致人們普遍認(rèn)為安全規(guī)制對(duì)安全水平產(chǎn)生積極作用[1]。然而有不少學(xué)者質(zhì)疑OSHA安全規(guī)制的有效性,例如,Viscusi使用1973—1983年面板數(shù)據(jù)對(duì)美國制造業(yè)的安全規(guī)制效果進(jìn)行實(shí)證研究發(fā)現(xiàn),規(guī)制并未顯著降低傷亡率[2]。之后的一些研究如 McCaffrey[3],Scholz和 Gray[4]以及Ruser和Smith[5]也支持上述觀點(diǎn),即安全規(guī)制在降低事故發(fā)生率和傷亡程度方面收效甚微。由此形成的“規(guī)制無效論”認(rèn)為政府規(guī)制并不是提高工作場所安全水平的“靈丹妙藥”,甚至可能對(duì)該行業(yè)的發(fā)展產(chǎn)生不利影響。然而也有學(xué)者對(duì)安全規(guī)制有效性持肯定態(tài)度,例如Gray和Scholz[6]利用1979—1985年間美國產(chǎn)業(yè)面板數(shù)據(jù)進(jìn)行實(shí)證分析,發(fā)現(xiàn)OSHA的安全規(guī)制將傷亡率水平平均降低了22%。后續(xù)研究如Gray和Scholz[7]、Weil[8]等也支持“規(guī)制有效論”的觀點(diǎn)。由此可見,對(duì)于安全規(guī)制是否有效在學(xué)術(shù)界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傳統(tǒng)的安全規(guī)制理論僅僅刻畫了從政府規(guī)制行為到規(guī)制效果的邏輯鏈條,而忽略了企業(yè)和工人理性行為這一重要環(huán)節(jié),即未深度剖析規(guī)制對(duì)企業(yè)安全投資以及工人安全努力的影響。事實(shí)上,安全規(guī)制并不直接作用于規(guī)制目標(biāo),而是通過影響企業(yè)和工人安全投入間接達(dá)到提高安全水平的目的。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學(xué)者如Peltzman[9]、Hause[10]以及Klick和Stratmann[11]開始注意到,工人的逆向行為對(duì)安全規(guī)制作用的發(fā)揮可能產(chǎn)生負(fù)面影響,最終使規(guī)制效果大打折扣,Klick和Stratmann將工人理性行為對(duì)規(guī)制效果的這種影響定義為佩爾茲曼效應(yīng)(Peltzman Effect)。考慮到工人違規(guī)操作、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等行為已經(jīng)成為引發(fā)我國危化品事故的主要原因,政府加強(qiáng)安全規(guī)制并未有效遏制事故的發(fā)生,這背后的邏輯是否是規(guī)制加強(qiáng)迫使企業(yè)增加安全投資后,工人對(duì)安全投資過度依賴,進(jìn)而減少自身安全努力 (例如現(xiàn)代化設(shè)備設(shè)施的引入導(dǎo)致工人對(duì)其過分依賴,從而降低風(fēng)險(xiǎn)防范意識(shí),導(dǎo)致違規(guī)操作、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等行為增加),最終導(dǎo)致危化品行業(yè)存在的佩爾茲曼效應(yīng)抵消了安全投資的效果?進(jìn)一步思考,政府規(guī)制加強(qiáng)下企業(yè)一定增加安全投資嗎?①可能存在這樣的情況:違規(guī)成本較低時(shí),企業(yè)寧愿交罰金也不愿承擔(dān)高昂的安全投資。由于工作場所安全水平由工人安全投入和企業(yè)安全投資共同決定,因此,只有深入挖掘規(guī)制加強(qiáng)對(duì)工人安全投入以及企業(yè)安全投資決策的影響,厘清安全規(guī)制作用的內(nèi)在機(jī)理,然后對(duì)癥下藥,才能達(dá)到改善我國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效果的目的。
當(dāng)前國內(nèi)從社會(huì)性規(guī)制理論角度進(jìn)行危化品的研究較為缺乏,僅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對(duì)危化品行業(yè)安全生產(chǎn)現(xiàn)狀、規(guī)制體制及規(guī)制政策等方面[12-13]。鑒于中國危化品行業(yè)發(fā)展過快,安全生產(chǎn)形勢嚴(yán)峻,本文選擇安全事故高發(fā)的民營危化品企業(yè)為切入點(diǎn),嘗試從佩爾茲曼效應(yīng)的角度研究中國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的真正效果。具體地,首先,本文在Klick和Stratmann[11]以及肖興志[14]研究的基礎(chǔ)上構(gòu)造工人期望效用函數(shù),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假設(shè)求出工人安全投入對(duì)企業(yè)安全投資的反應(yīng)函數(shù),分析安全規(guī)制加強(qiáng)導(dǎo)致企業(yè)安全投資增加時(shí),工人的最優(yōu)安全投入決策。其次,放松“規(guī)制加強(qiáng)促使企業(yè)安全投資增加”的假設(shè),將工人最優(yōu)反應(yīng)函數(shù)納入企業(yè)安全投資決策模型,利用比較靜態(tài)的方法構(gòu)造企業(yè)安全投資對(duì)安全規(guī)制的最優(yōu)反應(yīng)函數(shù),分析規(guī)制加強(qiáng)對(duì)企業(yè)安全投資的影響。最后,結(jié)合規(guī)制加強(qiáng)下工人的安全投入和企業(yè)的安全投資決策,梳理出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作用邏輯鏈條,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中國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效果進(jìn)行分析,并給出相應(yīng)的政策含義。
二、規(guī)制加強(qiáng)下工人的安全投入決策模型
Peltzman在其《汽車安全規(guī)制效果》一文中首次指出了佩爾茲曼效應(yīng)的存在:②Klick和Stratmann在其論文“Offsetting Behavior in the Workplace”中正式定義了“Peltzman Effect”。當(dāng)汽車安全措施的改善降低了事故損失的嚴(yán)重程度時(shí),為了實(shí)現(xiàn)效用最大化,司機(jī)往往會(huì)對(duì)風(fēng)險(xiǎn)放松警惕,加速行駛,最終抵消汽車安全規(guī)制部分甚至全部效果,反而提高了交通事故發(fā)生率[11]。在危化品行業(yè),同樣可能存在由工人逆向行為所產(chǎn)生的佩爾茲曼效應(yīng):企業(yè)安全投資 (指“硬”安全投資,即企業(yè)為保障安全作業(yè)而進(jìn)行的安全設(shè)備、設(shè)施和技術(shù)等方面的投入)的增加會(huì)給工人營造“安全幻覺”,使其形成對(duì)安全設(shè)備、設(shè)施的依賴,從而減少自身安全投入,③指重視相應(yīng)的安全培訓(xùn),遵守企業(yè)安全規(guī)章和安全行為準(zhǔn)則,正確使用防護(hù)用具,謹(jǐn)慎作業(yè)等。放松安全防范意識(shí)并引發(fā)違規(guī)操作、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等行為,最終導(dǎo)致人為因素 (如操作不當(dāng)、操作不慎)引發(fā)的危化品事故居高不下,影響企業(yè)安全水平與安全規(guī)制效果。由于企業(yè)“硬”安全投資屬于顯性投入,短期內(nèi)能“立竿見影”地營造“安全感覺”,且是規(guī)制機(jī)構(gòu)的主要監(jiān)察指標(biāo),增加“硬”安全投資短期內(nèi)符合企業(yè)利益。而“軟”安全投資 (指企業(yè)根據(jù)政府規(guī)制政策,制定安全作業(yè)的規(guī)章制度和安全行為細(xì)則并保障其實(shí)施,進(jìn)行安全培訓(xùn)、宣傳以及應(yīng)急預(yù)案等方面的投入)屬于隱性投入,一方面其效果具有時(shí)滯性,且因工人的主觀行為而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另一方面,其往往是規(guī)制機(jī)構(gòu)安全監(jiān)察的盲點(diǎn),從而導(dǎo)致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yè)喪失增加“軟”安全投資的動(dòng)力,因此本文假設(shè)危化品企業(yè)僅增加“硬”安全投資。
本部分通過構(gòu)造工人對(duì)企業(yè)安全投資的反應(yīng)函數(shù),分析規(guī)制加強(qiáng)下工人的安全投入決策及其對(duì)安全規(guī)制效果的影響。基本假設(shè)有:
H11安全規(guī)制加強(qiáng)促使企業(yè)安全投資增加。
H12危化品企業(yè)工人是風(fēng)險(xiǎn)中性的,事故發(fā)生和未發(fā)生情況下的效用函數(shù)分別為U1、U2,并假設(shè)效用函數(shù)具有良好性狀,即給定消費(fèi)量y,有(邊際效用遞減)。
H13設(shè)危化品安全事故發(fā)生率P是企業(yè)安全投資i和工人安全努力e的單調(diào)減函數(shù),即P=P( i,e),Pi<0,Pe<0,且 “邊際產(chǎn)量”①這里將P看做是i和e的生產(chǎn)函數(shù)。遞減:Pii>0,Pee>0。②可理解為,起初通過諸如維修已有的機(jī)器設(shè)備等較低的安全投資就能達(dá)到降低事故概率的效果,但隨著安全水平的提高,若要進(jìn)一步降低相同程度的事故概率,則必須進(jìn)行更加昂貴的安全投資,如全面革新企業(yè)的安全生產(chǎn)技術(shù)。進(jìn)一步地,企業(yè)安全投資對(duì)工人安全努力的“邊際產(chǎn)量”具有非增效應(yīng),即Pei≥0。
H14假設(shè)工人事故損失 C=C( i,e),且(與 H13類似);為了保證效用函數(shù)具有最大值 (二階求導(dǎo)為負(fù)),假設(shè) -1-Ce( )>0,即工人安全努力的邊際事故損失減少幅度大于1。
該假設(shè)旨在表明:在危化品生產(chǎn)企業(yè)中,工人稍稍增加自身安全努力如提高風(fēng)險(xiǎn)意識(shí)、謹(jǐn)慎操作機(jī)器設(shè)備,就能很大程度降低安全事故造成的損失。
H15假定工資率W為企業(yè)安全投資的減函數(shù)即Wi<0,③安全投資水平低的企業(yè)為了吸引和留住工人,會(huì)給予工人一定的工資差額來補(bǔ)償其所面臨的高風(fēng)險(xiǎn),這可理解為工人購買高安全水平工作條件的價(jià)格。目前很多民營化工企業(yè)生產(chǎn)條件惡劣,安全投資嚴(yán)重不足,因此以相對(duì)較高的工資水平來吸引勞動(dòng)力,表現(xiàn)為工資率是企業(yè)安全投資的減函數(shù)。且Wi-Ci≥0。④該假設(shè)意味著,風(fēng)險(xiǎn)補(bǔ)償性工資差額 (企業(yè)安全投資減少所帶來的工資率提高)應(yīng)大于工人事故損失,只有這樣才會(huì)使工人感受到企業(yè)給予的工資報(bào)酬級(jí)差能夠彌補(bǔ)工作風(fēng)險(xiǎn)可能造成的潛在損失,否則工人會(huì)選擇辭去工作。為了便于分析,假定工人安全努力e、企業(yè)安全投資i、事故損失C以及工資率W均已轉(zhuǎn)化為可比較的貨幣單位。
事故發(fā)生情況下工人效用:

事故未發(fā)生情況下工人效用:

則工人的期望效用:

在給定企業(yè)安全投資水平i外生的情況下,理性工人選擇安全努力e來實(shí)現(xiàn)期望效用最大化,即:

整理得:

式 (5)等號(hào)左右兩邊分別為工人增加安全努力的邊際收益MR和邊際成本MC,其中MR反映了工人每單位安全努力在降低事故發(fā)生率P和減輕事故損失C上獲得的收益;MC反映了工人安全努力增加所導(dǎo)致的邊際效用水平的降低。
給定企業(yè)最初安全投資水平,工人基于期望效用最大化選擇的安全努力水平為e*,顯然e*為邊際收益曲線MR和邊際成本曲線MC的交點(diǎn)。當(dāng)企業(yè)增加安全投資時(shí),工人的邊際收益曲線由MR降低至MR',邊際成本MC升高至MC',①簡單證明過程如下:由假設(shè)U2,y可得企業(yè)安全投入的增加會(huì)降低工人安全努力的邊際產(chǎn)量,即和均減少,從而使工人安全努力的邊際收益變小。由,可知企業(yè)安全投資的增加會(huì)降低工資率,從而降低工人的消費(fèi)水平和期望效用水平,進(jìn)而提高工人安全努力的邊際成本P。從而產(chǎn)生一個(gè)較低的安全努力水平e'。
現(xiàn)實(shí)中,從人員構(gòu)成角度分析,民營危化品企業(yè)充斥著較多農(nóng)民工、②據(jù)《國家安監(jiān)總局危化司王浩水司長講話摘要》(http://www.doc88.com/p-57986062211.html),在危化品從業(yè)人員中,農(nóng)民工的比例已經(jīng)達(dá)到了30%以上。臨時(shí)工,導(dǎo)致工人整體素質(zhì)較低。由于未受過正規(guī)安全培訓(xùn),工人安全操作技能差,安全意識(shí)淡薄,從而因人為操作不當(dāng)、操作不慎導(dǎo)致危化品安全事故頻頻發(fā)生。究其原因,民營危化品企業(yè)部分工人由于安全意識(shí)淡薄,往往憑直覺行動(dòng),企業(yè)安全投資增加會(huì)給其營造一種“安全幻覺”,使其形成對(duì)安全設(shè)備、設(shè)施的依賴,從而減少自身安全努力,易產(chǎn)生違規(guī)操作、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等行為,由此造成的佩爾茲曼效應(yīng)表現(xiàn)為危化品事故發(fā)生率 (Pe<0)的提高或者事故嚴(yán)重程度 (Ce<0)的增加,從而削弱安全規(guī)制效果。換言之,工人安全努力對(duì)企業(yè)安全投資在影響規(guī)制效果方面存在著“替代效應(yīng)”,如圖2所示。

圖1 企業(yè)安全投資增加引發(fā)工人逆向行為

圖2 “安全幻覺”與工人逆向行為產(chǎn)生的佩爾茲曼效應(yīng)
在最初的安全規(guī)制水平下,企業(yè)安全水平曲線用L0表示,當(dāng)工人基于效用最大化選擇安全努力e0時(shí),安全水平為S0,圖2中用A點(diǎn)表示。規(guī)制加強(qiáng)使安全水平曲線由L0上移至L1,此時(shí)若工人完全理性,將安全努力減少至e1,則仍能維持原有安全水平S0,用B點(diǎn)表示。但由于危化品工人素質(zhì)低,安全意識(shí)差,規(guī)制加強(qiáng)會(huì)給其造成“安全幻覺”,使其誤認(rèn)為安全水平曲線大幅上移至L2,出于期望效用最大化,工人會(huì)將安全努力減少至e2以維持原有安全水平S0,用C點(diǎn)表示。而此時(shí)真正的安全水平由曲線L1決定,即工人安全努力為e2時(shí),安全水平僅為S2,圖2中用D點(diǎn)表示。
三、規(guī)制加強(qiáng)下企業(yè)的安全投資決策模型
目前中國實(shí)施的是以加強(qiáng)企業(yè)安全投資為導(dǎo)向的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模式,即安全規(guī)制通過對(duì)企業(yè)安全投資施加約束而最終影響規(guī)制效果。具體地,規(guī)制的加強(qiáng)直接作用于企業(yè)安全投資,安全投資一方面直接對(duì)安全水平產(chǎn)生影響,另一方面通過工人逆向行為產(chǎn)生的佩爾茲曼效應(yīng)間接影響規(guī)制效果,因此分析規(guī)制加強(qiáng)下企業(yè)的安全投資決策便成為分析規(guī)制效果必不可少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此外,前文始終假設(shè)“規(guī)制加強(qiáng),企業(yè)安全投資一定增加”,該假設(shè)是否成立,有待于進(jìn)行數(shù)理證明。本部分利用比較靜態(tài)分析方法,將工人最優(yōu)反應(yīng)函數(shù)納入企業(yè)基于利潤最大化的安全投資決策模型,分析政府規(guī)制如何影響企業(yè)安全投資。基本假設(shè)有:
H21企業(yè)是風(fēng)險(xiǎn)中性的。
H22企業(yè)的安全水平S是企業(yè)安全投資i和工人安全努力e(i)的函數(shù),即
H23企業(yè)的產(chǎn)量是勞動(dòng)力投入L和安全水平S的增函數(shù),即危化品企業(yè)的生產(chǎn)函數(shù)為Q,且QL>0,QS>0。③高安全水平能夠減少事故引起的生產(chǎn)中斷和員工辭職率,提高生產(chǎn)連續(xù)性和勞動(dòng)力穩(wěn)定性,從而有利于提高企業(yè)產(chǎn)量。同樣,投入要素L和S的邊際產(chǎn)量遞減,即QLL<0,QSS<0。另外,為了便于分析,假設(shè)產(chǎn)品價(jià)格為1貨幣單位。
H24假設(shè)不遵守規(guī)制標(biāo)準(zhǔn) (i<i*,i*為規(guī)制標(biāo)準(zhǔn)要求的安全投資水平)的危化品企業(yè)承擔(dān)四類成本。第一類成本:勞動(dòng)力成本L·W( S( i)),且WS<0。第二類成本:安全投資成本i·c,其中c為企業(yè)每單位安全投資的機(jī)會(huì)成本,用資本租賃價(jià)格表示,并假定其固定不變。第三類成本:違規(guī)成本(主要指規(guī)制機(jī)構(gòu)罰款),并假定違規(guī)成本不會(huì)隨著違規(guī)程度的增加而減少,即Fi≤0,F(xiàn)i*≥0。r代表規(guī)制實(shí)施的程度,包括規(guī)制機(jī)構(gòu)安檢頻率和力度等。很明顯,r的增加會(huì)增加違規(guī)企業(yè)的違規(guī)成本,即Fr>0。最后,假定隨著r的增加,企業(yè)增加安全投資會(huì)降低其邊際違規(guī)成本,即Fir<0。第四類成本:事故損失成本G,一旦發(fā)生危化品安全事故,企業(yè)將承受工人事故賠償金,固定資產(chǎn) (如廠房,設(shè)備設(shè)施)損失,環(huán)境污染治理支出等一系列成本,并假設(shè)G為外生變量。
不遵守安全規(guī)制標(biāo)準(zhǔn)的危化品企業(yè) (i<i*)通過選擇勞動(dòng)力投入L和安全投資i來實(shí)現(xiàn)其利潤π最大化的目標(biāo),即:

企業(yè)利潤最大化的一階條件為:

對(duì)式 (7)和 (8)進(jìn)行全微分,再寫成矩陣形式有:


式 (10)表明,為了實(shí)現(xiàn)利潤最大化,政府安全規(guī)制加強(qiáng)會(huì)促使企業(yè)增加安全投資。企業(yè)安全投資一方面反映了安全規(guī)制強(qiáng)度;另一方面也在相當(dāng)程度上決定了安全規(guī)制效果。
四、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效果的理論闡釋
1.理論闡釋
將前文分析的規(guī)制加強(qiáng)下工人的最優(yōu)安全投入和企業(yè)的最優(yōu)安全投資決策綜合起來,分析規(guī)制對(duì)危化品企業(yè)安全水平的影響,如式 (11)所示:

工作場所安全水平主要由企業(yè)安全投資和工人安全投入所決定,由式 (11)可知,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通過影響企業(yè)安全投資和工人安全努力,最終作用于規(guī)制目標(biāo) (安全水平)。其作用路徑具體分為兩部分:一是安全規(guī)制通過作用于企業(yè)安全投資直接影響安全水平,即,將其定義為安全規(guī)制的直接效應(yīng)。由可知,當(dāng)安全規(guī)制加強(qiáng)時(shí),企業(yè)為了實(shí)現(xiàn)利潤最大化會(huì)相應(yīng)增加安全投資,結(jié)合可得>0,即安全規(guī)制的直接效應(yīng)為正。二是安全規(guī)制作用于企業(yè)安全投資的同時(shí),會(huì)影響工人的安全投入,通過佩爾茲曼效應(yīng)間接影響安全水平,即,將其定義為安全規(guī)制的間接效應(yīng)。由可知,企業(yè)安全投資增加導(dǎo)致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工人產(chǎn)生逆向行為,減少安全投入,結(jié)合,可得<0,安全規(guī)制的間接效應(yīng)即佩爾茲曼效應(yīng)為負(fù)。由于安全規(guī)制的直接效應(yīng)為正,間接效應(yīng)為負(fù),從而規(guī)制加強(qiáng)對(duì)安全水平的最終影響存在著不確定性,取決于直接效應(yīng)和間接效應(yīng)的相對(duì)大小。綜上所述,可得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作用機(jī)理如圖3所示。

圖3 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作用機(jī)理圖
在厘清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作用邏輯鏈條的基礎(chǔ)上,本文具體分析規(guī)制對(duì)安全水平存在的可能影響。由于安全規(guī)制直接作用于企業(yè),且>0為企業(yè)實(shí)現(xiàn)利潤最大化的必要條件,因此可從企業(yè)安全投資的角度衡量安全規(guī)制強(qiáng)度,進(jìn)而分析規(guī)制效果。換句話說,考察規(guī)制加強(qiáng)導(dǎo)致企業(yè)增加安全投資時(shí),安全水平的變化情況,即Si的符號(hào)判斷。將式 (8)改寫:

由于企業(yè)的目標(biāo)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其最優(yōu)安全投資決策一定滿足式 (12);由于因此,。對(duì)于不遵守規(guī)制標(biāo)準(zhǔn)的企業(yè),則安全投資的增加或者提高企業(yè)安全水平 (Si>0),或者降低企業(yè)安全水平 (Si<0),或者使企業(yè)安全水平保持不變 (Si=0)。
具體地,當(dāng)邊際安全投資成本大于邊際違規(guī)成本即c>-Fi時(shí),得Si>0,表明當(dāng)規(guī)制政策較溫和或規(guī)制懲罰力度不大時(shí),加強(qiáng)規(guī)制能夠提高危化品企業(yè)的安全水平。進(jìn)一步解釋,當(dāng)規(guī)制加強(qiáng)時(shí),企業(yè)安全投資增加對(duì)安全水平產(chǎn)生的正效應(yīng)大于工人逆向行為產(chǎn)生的佩爾茲曼效應(yīng),從而提高安全水平;當(dāng)邊際安全投資成本等于邊際違規(guī)成本即c=-Fi時(shí),得Si=0,此時(shí)加強(qiáng)安全規(guī)制,不會(huì)對(duì)企業(yè)安全水平產(chǎn)生任何影響。當(dāng)邊際安全投資成本小于邊際違規(guī)成本即c<-Fi時(shí),得Si<0,意味著當(dāng)安全規(guī)制政策較嚴(yán)厲或者規(guī)制強(qiáng)度過大時(shí),進(jìn)一步增強(qiáng)安全規(guī)制反而導(dǎo)致安全水平降低。此時(shí),安全投資增加對(duì)安全水平產(chǎn)生的正效應(yīng)會(huì)被工人逆向行為產(chǎn)生的佩爾茲曼效應(yīng)完全抵消,最終規(guī)制的加強(qiáng)反而會(huì)降低危化品企業(yè)安全水平。

圖4 不同規(guī)制強(qiáng)度下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效果示意圖
上述分析可知,為了達(dá)到預(yù)期的規(guī)制目標(biāo),政府在制定和實(shí)施安全規(guī)制時(shí),一定要把握好“適度原則”,即適度的安全規(guī)制有助于提高企業(yè)安全水平,達(dá)到最優(yōu)的安全效果;而過度的安全規(guī)制則很可能產(chǎn)生“反作用”——導(dǎo)致企業(yè)安全水平下降,從而與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的初衷背道而馳,如圖4所示。
綜上所述,規(guī)制機(jī)構(gòu)通過制定一系列安全法規(guī)、標(biāo)準(zhǔn)并加以實(shí)施來強(qiáng)制危化品企業(yè)進(jìn)行規(guī)定的安全投入,通過工人安全努力會(huì)進(jìn)一步影響安全規(guī)制效果。因此,危化品安全事故的發(fā)生是內(nèi)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結(jié)果,安全規(guī)制只是一種外部約束力量,這種外部約束是否能夠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解決危化品安全問題,還取決于規(guī)制對(duì)企業(yè)和工人安全投入的綜合影響。
2.佩爾茲曼效應(yīng)與中國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實(shí)踐剖析
中國的危化品企業(yè)中有86%是民營企業(yè)。①從產(chǎn)權(quán)的角度來看,中國民營危化品企業(yè)分為三類:由私營業(yè)主創(chuàng)辦的私營企業(yè);由國有和鄉(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改制而成的民營企業(yè);由自然人或私營企業(yè)承包、租賃和托管的公有企業(yè),即國有民營企業(yè)。危化品行業(yè)屬于高風(fēng)險(xiǎn)、高投入和高回報(bào)的行業(yè),民營企業(yè)對(duì)危化品行業(yè)的發(fā)展做出巨大貢獻(xiàn)的同時(shí),也面臨著事故多發(fā),安全隱患嚴(yán)峻等問題。根據(jù)2006—2010年中國危險(xiǎn)化學(xué)品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民營企業(yè)事故率和死亡人數(shù)分別占事故總數(shù)和死亡總數(shù)的86%、83%,中國的危化品安全事故主要發(fā)生在民營企業(yè)。統(tǒng)計(jì)資料表明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事故最多,死亡人數(shù)也最多,分別占81%、83%。這與危險(xiǎn)化學(xué)品生產(chǎn)流程長,生產(chǎn)工藝過程復(fù)雜,原料、半成品、副產(chǎn)品、產(chǎn)品及廢棄物大部分具有危險(xiǎn)特性有關(guān)。從事故原因的角度分析,在各種原因中,因工人違規(guī)操作、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等行為造成的事故最多,占事故總起數(shù)的51%,導(dǎo)致的人員傷亡最為嚴(yán)重,占事故全部死亡人數(shù)的50%[2]。回到引言部分提出的問題:為什么工人違規(guī)操作、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等行為是引發(fā)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為什么政府加強(qiáng)安全規(guī)制后危化品事故依然頻頻發(fā)生?目前以加強(qiáng)企業(yè)安全投資為主的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模式一定能夠提高安全水平嗎?利用本文結(jié)論進(jìn)行解釋:中國民營危化品企業(yè)中充斥著大量的農(nóng)民工和臨時(shí)工 (例如河北克爾化工有限責(zé)任公司“2·28”重大爆炸事故中,包括車間主任在內(nèi)的絕大部分員工均為初中文化水平)。這些工人大部分文化程度低,不懂化學(xué)生產(chǎn)技術(shù)和要求,缺乏安全技能和危化品專業(yè)知識(shí),加之民營企業(yè)缺少相應(yīng)的“軟”安全投資,即配套的安全操作規(guī)程,必要的安全教育、培訓(xùn),導(dǎo)致危化品工人普遍安全操作技能差,安全意識(shí)淡薄。當(dāng)政府以增加企業(yè)“硬”安全投資為導(dǎo)向的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加強(qiáng)時(shí),安全投資的增加會(huì)給工人造成“安全幻覺”,使其容易對(duì)企業(yè)安全投資形成依賴,進(jìn)而產(chǎn)生逆向行為,減少自身安全努力,表現(xiàn)為違規(guī)操作、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現(xiàn)象嚴(yán)重,導(dǎo)致“佩爾茲曼效應(yīng)”抵消了安全規(guī)制的效果,最終造成民營危化品企業(yè)事故居高不下,傷亡慘重。
五、結(jié)論與政策啟示
傳統(tǒng)的安全規(guī)制理論僅僅刻畫了從政府規(guī)制行為到規(guī)制效果的邏輯鏈條,存在重要的環(huán)節(jié)缺失,即忽略了安全規(guī)制對(duì)工人安全投入和企業(yè)安全投資決策的影響,而兩者又是決定規(guī)制效果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國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模式也僅停留在敦促企業(yè)增加“硬”安全投資這一表面上,而忽略了對(duì)工人行為的內(nèi)在約束。本文試圖為中國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分析建立一個(gè)新的理論框架,該框架涵蓋了安全規(guī)制完整的作用機(jī)理:規(guī)制通過影響企業(yè)安全投資以及工人安全投入,最終作用于規(guī)制目標(biāo);鑒于工人違規(guī)操作、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等行為是引發(fā)危化品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本文著重強(qiáng)調(diào)工人逆向行為產(chǎn)生的佩爾茲曼效應(yīng)對(duì)于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效果的潛在重要影響。由于危化品生產(chǎn)經(jīng)營具有高溫高壓、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的特點(diǎn),任何工作疏忽或個(gè)人違章行為都可能引發(fā)安全事故。中國危化品安全事故多發(fā)生在民營企業(yè),由于安全培訓(xùn)缺失,加之工人整體素質(zhì)低,導(dǎo)致工人普遍對(duì)作業(yè)場所存在的危險(xiǎn)性認(rèn)識(shí)不足,安全意識(shí)差。政府出臺(tái)嚴(yán)厲的規(guī)制政策,加強(qiáng)安全規(guī)制會(huì)促使企業(yè)增加“硬”安全投資,進(jìn)而給工人造成“安全幻覺”,使其產(chǎn)生逆向行為,減少安全投入,表現(xiàn)為違規(guī)操作、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現(xiàn)象嚴(yán)重,由此引發(fā)的佩爾茲曼效應(yīng)往往抵消安全規(guī)制部分甚至全部效果,最終達(dá)到的安全效果如何則存在不確定性。因此,如何在保證規(guī)制作用企業(yè)安全投資的前提下,有效引導(dǎo)工人增加安全投入是目前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需要關(guān)注的內(nèi)容,據(jù)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1.轉(zhuǎn)移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重點(diǎn),提高企業(yè)長期安全水平
目前,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工作重點(diǎn)主要落在促進(jìn)企業(yè)增加“硬”安全投資上,如增添安全設(shè)備設(shè)施工具、提高生產(chǎn)自動(dòng)化水平和及時(shí)更新安全技術(shù)等。雖然“硬”安全投資的增加短期內(nèi)會(huì)產(chǎn)生一定的效果,但不一定促進(jìn)企業(yè)長期安全水平的提高。由于工人違規(guī)操作和違反勞動(dòng)紀(jì)律是引發(fā)危化品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僅一味地增加“硬”安全投入不僅加重企業(yè)成本負(fù)擔(dān),迫使其為壓低成本而大量雇用廉價(jià)低素質(zhì)勞動(dòng)力,還會(huì)使安全意識(shí)差的工人產(chǎn)生逆向行為,反而不利于安全水平的提高。要想從根本上提高安全水平,就要在保證危化品企業(yè)進(jìn)行一定“硬”安全投資的基礎(chǔ)上適當(dāng)?shù)卦黾印败洝卑踩度耄缂哟蠊と说陌踩逃嘤?xùn),完善危化品安全操作規(guī)程,制定詳細(xì)的安全工作細(xì)則等,從而有效遏制人為因素造成的危化品事故,促進(jìn)企業(yè)長期安全水平的提高。
2.嚴(yán)格危化品企業(yè)員工準(zhǔn)入條件,提升從業(yè)人員整體素質(zhì)
工人的安全投入很大程度上受其自身素質(zhì)影響,因此企業(yè)要把好第一關(guān)——從業(yè)人員的招錄。針對(duì)危化品企業(yè)從業(yè)人員多為安全素質(zhì)較低的農(nóng)民工和臨時(shí)工,筆者認(rèn)為應(yīng)該嚴(yán)格從業(yè)人員的招錄條件,適度提高行業(yè)準(zhǔn)入門檻,嚴(yán)格執(zhí)行相關(guān)人員持證上崗制度,特別是在具有高風(fēng)險(xiǎn)、條件惡劣的工作崗位更應(yīng)配備具有危化品安全操作技能的專業(yè)人員;有能力的大型危化品企業(yè)可自主培養(yǎng)安全管理的技術(shù)人才,企業(yè)變招工為招生,通過各種形式的專業(yè)知識(shí)和技能培訓(xùn),培養(yǎng)懂化工、懂安全的專業(yè)人才,進(jìn)而提升危化品行業(yè)從業(yè)人員的整體素質(zhì)。
3.健全危化品企業(yè)安全教育培訓(xùn)制度,提高工人安全意識(shí)
民營危化品企業(yè)工人逆向行為普遍存在,因此企業(yè)要把好第二關(guān)——員工安全教育培訓(xùn)。工人安全投入是一種無主動(dòng)意識(shí)的行為,在對(duì)其引導(dǎo)過程中,應(yīng)主要從培養(yǎng)安全意識(shí)出發(fā),以期達(dá)到隱形地增加工人安全努力的效果。可從以下幾方面入手:健全企業(yè)安全教育培訓(xùn)制度,加強(qiáng)對(duì)危化品企業(yè)安全管理人員和作業(yè)人員的安全教育培訓(xùn),不斷強(qiáng)化員工安全意識(shí);加強(qiáng)危化品企業(yè)新錄用員工和轉(zhuǎn)崗人員的安全教育和培訓(xùn),使其意識(shí)到作業(yè)場所和工作崗位潛在的危險(xiǎn)因素,并掌握必要的安全常識(shí)與安全操作程序;建立危化品信息交流平臺(tái),普及安全防護(hù)、自救互救的基本知識(shí)和技能,加強(qiáng)應(yīng)急預(yù)案與演練,提高危化品企業(yè)員工的自我防護(hù)和自救互救能力。
4.實(shí)施強(qiáng)度適中的規(guī)制政策,強(qiáng)化危化品安全激勵(lì)機(jī)制設(shè)計(jì)
由于規(guī)制強(qiáng)度過大可能導(dǎo)致安全水平降低,筆者認(rèn)為規(guī)制機(jī)構(gòu)應(yīng)該制定實(shí)施強(qiáng)度適中的規(guī)制政策,并且政府規(guī)制不應(yīng)把注意力僅放在企業(yè)一方,應(yīng)當(dāng)“雙管齊下”,共同關(guān)注企業(yè)和工人雙方的安全投入。工作場所安全水平是企業(yè)安全投資和工人安全努力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在當(dāng)前形勢下,政府應(yīng)該強(qiáng)化危化品安全激勵(lì)機(jī)制設(shè)計(jì),以此彌補(bǔ)規(guī)制失靈的缺陷,修正工人的逆向行為。一方面,設(shè)計(jì)安全基金制度,調(diào)動(dòng)企業(yè)增加安全投入的積極性;另一方面,考慮到佩爾茲曼效應(yīng)的存在,可以督促企業(yè)對(duì)工人的安全生產(chǎn)給予一定的物質(zhì)獎(jiǎng)勵(lì),如添設(shè)安全績效工資,以激勵(lì)工人提高安全意識(shí),增加安全努力,最終改善危化品安全規(guī)制效果。
[1]Viscusi,W.K.,Joseph,E.H.Jr.,John,M.V.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M].MIT Press,1992.723-725.
[2]Viscusi,W.K.The Impact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Regulation,1973—1983[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86,17(4):567-580.
[3]McCaffrey,D.An Assessment of OSHA’s Recent Effects on Injury Rates[J].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83,18(1):131-146.
[4]Scholz,J.,Gray,W.OSHA Enforcement and Workplace Injuries: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Risk Assessment[J].The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1990,3(3):283-305.
[5]Ruser,J.,Smith,R.Re-Estimating OSHA’s Effects:Have the Data Changed[J].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1,26(2):212-235.
[6]Gray,W.B.,Scholz,J.T.Does Regulatory Enforcement Work?A Panel Analysis of OSHA Enforcement[J].Law and Society Review,1993,27(1):177-213.
[7]Gray,W.B.,Scholz,J.T.Can Government Facilitate Cooperation?An Informational Model of OSHA Enforcement[J].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1997,41(3):693-717.
[8]Weil,D.If OSHA Is so Bad,Why Is Compliance so Good?[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27(3):618-640.
[9]Peltzman,S.The Effects of Automobile Safety Regul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5,83(4):677-725.
[10]Hause,J.C.Offsetting Behavior and the Benefits of Safety Regulations[J].Economic Inquiry,2006,44(4):689-698.
[11]Klick,J.,Stratmann,T.Offsetting Behavior in the Workplace[DB/OL].Working Paper,School of Law,George Mason University,2003.
[12]劉宇.中國危險(xiǎn)化學(xué)品行業(yè)安全監(jiān)管研究[J].東北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8,(5):82-85.
[13]孫康,楊合嶺.中國危險(xiǎn)化學(xué)品安全規(guī)制的國際比較:比較制度分析的視角[J].產(chǎn)業(yè)組織評(píng)論,2011,(6).
[14]肖興志,齊鷹飛,李紅娟.中國煤礦安全規(guī)制效果實(shí)證研究[J].中國工業(yè)經(jīng)濟(jì),2008,(5):67-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