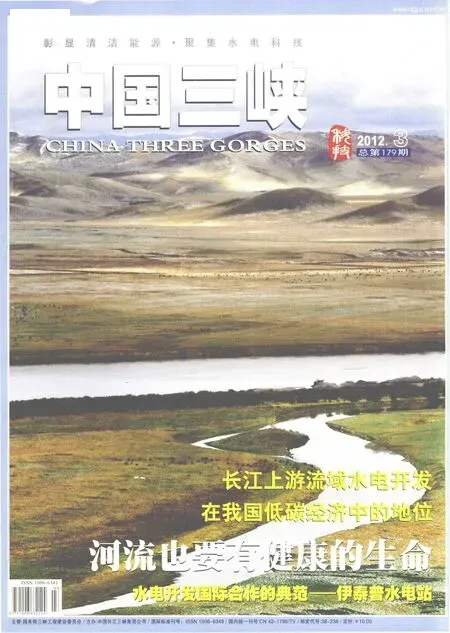三峽工程公共形象的反思與再認識
李 洋
三峽工程,一直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社會各界對三峽工程的認知和評價,形成了三峽工程公共形象。由于三峽工程的復雜性,三峽工程公共形象似乎是一個“多棱鏡”、“萬花筒”,莫衷一是。“民族工程”、“劣等工程”、“‘災星’工程”、“‘權力’工程”,不一而足。三峽工程公共形象始終處于一種變動、被“遮蔽”的狀態。
“(他者)形象的塑造雖然包含著塑造者的想象和欲望的折射,但又非不顧社會現實基礎的純粹想象之物,而且社會基礎還影響著形象塑造者的視角,影響著對待他者的態度和評價。”“形象作為一種文化隱喻或象征,是對某種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隨意性表現,其中混雜著認識的與情感的、意識的與無意識的、客觀的與主觀的、個人的與社會的內容。”(周寧,《跨文化研究∶以中國形象為方法》)而認同又是“個人與他人、群體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趨同的過程”(弗洛伊德語)。看來,社會對三峽工程的認同還有很大的距離。江河時空格局的改變、恢復、平衡,社會秩序的重構,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在短時期內三峽工程公共形象得到改變是不現實的。三峽工程公共形象建構,過于樂觀抑或過于悲觀都是不可取的。

三峽壩區已成為我國著名的旅游景區。 攝影/鄧立中
正確認識不同語境下三峽工程公共形象,是建構三峽工程公共形象的前提和基礎。將三峽工程公共形象生成的不同歷史背景、話語體系、主要表現形態等基本問題比較清晰地呈現出來,是非常必要的。
一 三峽工程與民族工程、民生工程的形象定位
中國歷史上,堪稱民族工程者并不多見。民族工程具有一些特質。其最根本的是,不管哪種政治派別在關涉民族和國家問題上,始終具有一些顯著的共同性。三峽工程作為“民族工程”、“民生工程”,其最重要之點就在于它始終與國家、民族命運聯系在一起。
著名新聞記者盧躍剛認為:“三峽問題不是個簡單的對錯問題,不是簡單地技術分析利益的問題,需要將三峽工程放到現代化的背景下,放到三峽的歷史背景下,放到中國社會特殊的體制背景下來看,才可能看清楚。”
1919年,孫中山先生提出:“由宜昌而上,……當以水閘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資其水力。”30至40年代,國民政府也曾著手三峽工程的勘測設計準備。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成立以后,20世紀60年代經濟困難時期,曾考慮分級開發或分期開發方案,想縮小規模爭取上馬。70年代初先建下游的葛洲壩工程,想以此促進三峽工程上馬。80年代初提出150米的低壩方案。后經過重新論證,最終確定為現在175米中壩方案。
顯然,不能把三峽工程僅簡單看成一個水利工程,也不能簡單地僅從某一個歷史階段來認識這項工程。三峽工程不僅關涉政治、經濟等諸多因素,更與國家發展、民族命運休戚相關。三峽工程的背后深刻地體現著國家和民族的意志。國共兩黨之所以都鐘情于三峽工程,原因也就在這里。因之我們可以說,三峽工程,是一定政治、經濟、技術條件下,中華民族治理長江的必然選擇,是千百年來歷朝歷代治江思想的延續和發展,是中華民族水利工程思想、水利工程科技、水利工程社會發展的歷史必然,是中華民族治理長江的里程碑。長江中下游水患,是中華民族的心腹大患。千百年來,根治長江水患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夢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峽工程是中華民族一項偉大的政治工程,是一項偉大的民族工程和民心工程。
三峽工程作為民族工程、民生工程的公共形象,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現實的選擇。這種形象貫穿于三峽工程科學論證、民主決策、建設管理、綜合效益發揮和科學運行的全過程。這種形象體現了三峽工程的歷史性和社會性,符合歷史與現實條件,具有科學性,應該是三峽工程科學發展和社會認識的主線與基調。
當然,此種形象還需要向縱深開掘,向歷史細節探尋,將視野和觸覺延伸到全世界,體現國際視野。治水,是一個歷史話題,也是一個國際話題。在治水與治國語境下,不同國家治水的模式如何,工程與國家、社會,工程與科技等不同維度之間的關系如何建構,需要從理論上進行深入闡釋,找出其中的邏輯關系和規律性。而不是依靠歷史進行印證式的說明。在一個更高的歷史起點、更宏大的歷史視野、更開闊的歷史場景來認識三峽工程的歷史地位及其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價值,將三峽工程與世界其他大壩聯系起來、對照起來,而不是就三峽工程談三峽工程,是現實的迫切需要。
二 “三門峽工程”、“阿斯旺大壩”與三峽工程公共形象
“三門峽工程”、“阿斯旺大壩”一直被視為水電工程建設中最為失敗的典型例子,但是在網上,也總有不少人將其與三峽工程聯系起來。
針對三門峽工程,我國著名水電專家潘家錚院士指出:“三門峽的歷史非常曲折。當初的規劃無疑未實現,原因是對黃河水沙運行規律認識不足,提出蓄水攔沙的治黃方略,搞高壩水庫,對水土保持的作用過于樂觀,對綜合利用要求急于求成,對移民工作的艱巨性也估計不足,以至造成失誤,被迫進行兩次改建,教訓是巨大的。”三門峽的教訓是深刻的。一是對自然規律研究和認識不夠,造成對決策對象沒有完全弄清楚的前提下就盲目建庫。二是政治對科學的干預,反對意見遭到壓制。政治決策,在那個年代,尤其是1955年之后,開始成為凌駕一切的價值與利益,削弱了技術論證上的科學氛圍與嚴謹態度。雖然水利樞紐在規劃和設計的時候,“大躍進”尚未正式拉開幃幕,但公共工程的“高大全”方案、“大上快上”思維,本著不可辜負這個時代的豪情噴涌而出,已經征服了眾人。

三峽工程全景圖。 攝影/黃正平
潘院士說:“通過三門峽工程的反復,我們對‘治黃’從認識水平到科技水平都有極大的提高。例如,整治含沙河流的基本思路,水庫如何能保持長期運行,蓄清排渾調水調沙合理運行方式的實踐,庫區泥沙沖淤的規律等等。泥沙學科從泥沙運行的基本理論、模型試驗技術、數學計算理論和方法、異重流排沙等以及高含沙的水力發電問題也都有了迅速發展。這為中國人民繼續整治大江大河帶來無比寶貴的知識和經驗。”潘院士談到的這些歷史與進步,可能是許多人沒有能夠認識到的。也可以這樣講,正是因為三門峽問題的出現,才更加引起了三峽工程論證、決策時期對泥沙問題的高度重視與研究,為不同意見提供充分表達的渠道和場所。
埃及阿斯旺大壩的“惡名”主要來自以下原因。第一,政治偏見。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并成功反抗了英法入侵,西方國家因此拒絕支援修建阿斯旺大壩。而埃及政府援請蘇聯去設計和修建,也為西方世界所不快。西方強大的輿論機器大肆鼓噪阿斯旺大壩的不利影響,給阿斯旺大壩“添黑加污”,制造“惡名”,影響了國際社會對阿斯旺大壩的正確認識和客觀評價。第二,詆毀宣傳的影響。詆毀水壩的宣傳,很容易在某些西方人士中產生共鳴。在他們看來,尼羅河是一條神性的神圣之河,全面改變尼羅河的面貌,攔阻泥沙,調節徑流,消滅洪水……這不僅是對古老神話的褻瀆,也是對上帝旨意的違抗。神秘主義思想在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社會大眾,并不對建壩持有惡感,但他們相信西方報道的“客觀”、“公正”。在“擬態環境”下,輿論被誤導了。第三,水壩本身帶來的影響。建水壩會帶來有形無形、有深有淺、有直接有間接、有長遠有短期的影響,但是,人們總是帶來一種高期望值。當高期望值與現實發生矛盾之時,也就是情緒爆發之時。
“(三峽工程的)輿論(注:輿論是公共形象最直接的反映)的形成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規律可循,其形成和消長與當今社會利益分配、社會心理演變、社會經濟發展以及社會矛盾激化等因素密不可分。”(尹鴻偉《三峽工程再成輿論熱點》)將三門峽、阿斯旺大壩與三峽工程對照起來,將三峽工程的負面影響與之等同起來,此種形象建構的社會基礎、心理基礎是三門峽、阿斯旺大壩給社會造成的嚴重心理陰影以及將兩大工程加諸于三峽工程的“集體無意識”,還有就是一些反壩人士有意而為之的結果。
三 特大自然災害與三峽工程公共形象
最近幾年,長江流域頻頻發生極端自然災害。無論是旱災、洪災、雪災還是地震,總有一些人將矛頭直指三峽工程。這些聯系是否具有科學性,是三峽工程公共形象認識的根本。這里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大壩與氣候,三峽工程對氣候有多大改變?第二,大壩與地震,三峽工程是否能誘發8級以上地震?
2011年長江中下游發生百年一遇的干旱。在此之前,還有重慶大旱、洪災,西南大旱等。所以,一時間關于三峽工程改變氣候的“輿論狂潮”不一而足。
在三峽工程興建之前,四川松潘曾發生8級地震,建設過程中2008年又發生了汶川地震。無論是松潘地震,還是汶川地震,都已經證明龍門山斷裂帶是地震活躍帶,與三峽工程并無關系。
將這些特大自然災害與三峽工程聯系起來,背后的深層原因還在于公眾認知層面。長期以來,我國有些忽視科技素養、工程素養的教育,科學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也處于缺失狀態,公民科學素養缺失必然導致對自然現象的成因“胡亂歸因”。外界一有“風吹草動”,社會立刻變得“驚若寒蟬”。古代社會,人們對自然認識不足,就從神話中尋求力量,從迷信中生成敬畏。整個社會對自然認知不足,導致的最直接后果是社會“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同時又加劇對科學的不信任,進而又會進一步加劇其內在矛盾。社會一旦進入這個認知的“怪圈”,即便是高層次的知識階層也會慢慢失去理性、“隨波逐流”。

中國三峽集團董事長曹廣晶在中央電視臺對話節目回答三峽工程熱點問題。攝影/鄭斌
如何面對一個“惡意”生長的世界?三峽工程公共形象既涉及到實踐范疇,也涉及到認識和觀念范疇。大壩與地震、大壩與氣候,是國際水利水電學界面臨的共同課題。實際上,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座水庫造成特大地震,也還沒有哪一座大壩改變了大氣環流。況且,從壩高來說,三峽工程在世界高壩中處于24位。水庫庫容也不算很大。大壩與地震、大壩與氣候問題,首先是一個科學問題。科學的問題,需要有持續的科學研究和科學論證。科學問題在大眾化社會容易被簡單化、情緒化和極端化,一定程度上還可能政治化。此種形象不僅是極端自然災害在三峽工程接近完建階段頻頻發生,還有媒體的“集體無意識”。而媒體策劃一些“無中生有”、“子虛烏有”的毫無科學依據的報道,則是科學素養和道德責任的雙重缺失。一些媒體有意無意將毫不相關的事物聯系起來,記者在提問時采取一種誘導的方式,預設前提,將干旱、洪災、地震加諸三峽工程,是極端不負責任的。媒體是如何采用這種邏輯進行議題設置的呢?約翰·漢尼根(John Hannigan)在《環境社會學》一書中集中探討了環境話語體系的建構特征和社會型塑方式。環境議題和有關環境的持續性爭論中,媒體發揮了極其重要的議程設置功能,議程設置是大眾傳播的重要社會功能和效果之一。簡言之,即媒體對一些問題給予集中強調,或者將之不相干的事物進行比照、聯系,最終將公眾引進媒介議程。這一點,在特大自然災害與三峽工程等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自然災害等議題之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斷。
四 “權力的奴婢”與三峽工程公共形象
有人把三峽工程看作是“權力的奴婢”。這里存在如何認識工程與民主關系的問題。三峽工程首先是科學問題。我國著名記者盧躍剛認為“治水問題在中國是直接關于國計民生的政治問題”、“最開始的反建派里,就有人擔心三峽建設周期很長,政治、經濟、社會、技術牽涉因素復雜,而體制運行效率太低,決策不透明,大型工程建設中常見的管理不善,浪費、建設質量差等。項目太大了,很難監督,容易失控。”三峽工程決策時期,是我國社會大型水利工程中的矛盾和問題高發期。人們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和憂慮,與這種客觀背景有關。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水利水電工程存在諸多難以克服的矛盾和問題。同樣,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三峽工程是否能解決這些問題,人們不免憂慮和擔心。而這種憂慮和擔心靠當時的體制是難以解決的。

中國三峽集團總經理陳飛在三峽壩區接受中央電視臺采訪,回答三峽工程熱點問題。 攝影/張偉國
如何科學決策是擺在新中國領導人面前的重大問題。無論是“林李之爭”(林一山、李銳圍繞三峽工程的辯論),還是因三門峽工程而聲名鵲起的黃萬里先生,也先后對三峽工程提出不同意見。20世紀80年代中期,三峽工程也再度進行“重新論證”,我們都可以看出三峽工程漫長決策的審慎性、艱巨性。
三峽工程是“權力的奴婢”,此種形象曲解了三峽工程科學化民主化的科學內涵,對于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技術民主、什么是精英民主、什么是專家民主、什么是公眾參與等基本問題存在認識上的偏頗,從而導致認識上的片面性。這里存在兩個最核心的問題,一是如何看待三峽工程決策過程中一般公眾參與的缺失?一般公眾參與的缺失,是否意味著缺乏民主?二是如何看待反對意見?反對意見是否被壓制?對此,我們需要深入分析上述兩個重大問題。
第一,三峽工程是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互動的結果,一般社會公眾參與決策過程缺失,這是整個決策論證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正因為三峽工程是政治精英和科技精英互動的結果,老百姓決策參與的主體地位缺失,導致了當前輿論的強烈反彈。”像三峽工程這樣一個復雜而專業的工程問題,如何讓老百姓參與到決策中來是一項政治難題。
針對三峽工程決策中的民主問題,不能使用簡單化的思維來考慮。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皮特在《技術思考——技術哲學的基礎》一書中專門提出了“技術、民主與變革”的關系問題。針對“技術是對民主的威脅”之主張,他強調:我們需要有相應的民主化標準”、“技術對民主構成威脅這種觀點使人難以理解。首先是民主自身的核心概念之中存在著大量難解之題。無論問題是否存在,它都難以理解在一個政治體系當中,還有什么比民主自身內在的不一致更能使它受到威脅。”約瑟夫·皮特認為:“如果改善人類命運的努力被破壞了,或為了實現進一步的目標而改進工具以求發展的努力也被破壞了,或者這兩種努力都被破壞了,那么就危及到了我們未來改善人類命運的能力。”約瑟夫·皮特最后指出,“在保護民主的名義下,我們卻偏偏將民主破壞了”“沒有簡單化的技術,也沒有簡單化的科學,更沒有簡單化的民主”。由此觀之,只有在具體的情形中,當人們理解了一個特殊的創新是如何挑戰了一種具體的價值的時候,我們才能夠明白威脅的本義是什么。因此,泛泛地談論技術和民主、工程和民主,幾乎不會闡明任何問題。有學者強調,在西方,類似三峽工程這樣非常專業的論證決策強調不具備相關專業知識的社會公眾參與,那么,中國是否可以呢?如何理解公眾參與在三峽工程決策中的地位、條件、機制,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還是一個頂層制度設計的問題。進一步研究三峽工程決策對推動我們重大工程項目決策體制、機制以及三峽工程決策體系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第二,反對意見推動了三峽工程決策論證的深度和廣度,使三峽工程決策更加優化,為三峽工程決策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民主基礎(民意基礎)和政治基礎。“林李之爭”奠定了成都會議上重大決議的出臺,“高壩低壩之爭”推動重新論證。反對意見的巨大貢獻和對科學決策、民主決策所產生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是值得珍視的。當前,爭論的焦點,依然沒有超越80年代重新論證時期所提出的各種看法和主張。
三峽工程民主決策表現出怎樣的獨特性?其獨特性很難用一般普適性的理論進行解釋。三峽工程決策過程對我國決策體制有哪些理論上的突破和貢獻,對我國民主決策有哪些發展,是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對于此種問題,我們需要警惕一些人將三峽工程的負面影響政治化、意識形態化。事實上,三峽工程負面影響與三峽工程決策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三峽工程負面影響不是由于三峽工程決策不科學不民主的結果。相反,三峽工程決策過程中高度重視三峽工程不利影響,最終經過近40年的漫長論證才得出“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的結論。不能因為三峽工程的不利影響就否定三峽工程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合法性。將三峽工程的負面影響政治化、意識形態化主要是借助三峽工程來映射共產黨的決策體制。一是對共產黨體制下的決策不信任。二是對權威進行消解,否定或不承認科學的存在。這是一種科學虛無主義的表現。也是后現代主義中的政治心理。
五 “詩意的想象”與三峽工程公共形象
文學是最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三峽,如詩如畫。三峽,是詩意棲居的地方。歷史上的文人墨客曾在此留下千古名篇。這些名篇所能展現的,不僅有自然的各種外在特征,而且有人與自然互動時產生的精神的、內在的感受。三峽文學,當屬于生態文學的范疇。它藝術地向人們展示自然的奧秘和神奇,使人產生強大的內心震撼,從而受到教育,而這一點恰恰是科學或其他手段難以做到的。

中國三峽集團投入巨資人工繁育中華鱘,長成后放歸長江。 攝影/肖佳法
著名生物學家法布爾在《昆蟲記》中也質疑科學方法的局限性,他說:“科學向我們講述它們的距離,它們的速度,它們的質量,它們的體積;科學將鋪天蓋地的數字向我們壓來,以無數、無垠和無止境,把我們驚得目瞪口呆。然而,科學卻怎么地感動不了我們一絲真情。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科學缺少那偉大的奧秘,也就是生命的奧秘。”當三峽工程改變了長江格局的時候,三峽工程公共形象又該如何得到社會認同呢?
“文學是人學。”三峽文化研究者吳衛華先生曾統計:自20世紀30、40年代伊始,陸續有一些電影與三峽產生了某種特定的聯系。逼近20世紀末的90年代,有關三峽地域的影視創作一時蔚為大觀,總數量達數百部(集)之多。“三峽題材的影視作品是現代科技與古老文化相遇合的產物,作為一種嶄新的審美文化,它以鏡像的方式和多樣化的創作形態豐富了三峽文化的內涵,同時也大大提升了三峽及其歷史文化、現代文化的地位和影響,構成了三峽地域文化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現當代人心目中的三峽是經過千百年詩詞歌賦熏染了的奇山異水。三峽雄渾、壯烈、瑰麗、神秘、浪漫,已成為中國文化一個具有獨特審美意義的符號——充滿野性、力量的悲壯美在這里得到最為集中的體現。國人因之向往三峽,三峽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的精神家園。現在,仍有不少人留戀昔日三峽那激流之奔騰、纖夫之彪悍、木船帆影、神秘野性……
三峽工程,橫空出世。因之而改變了千百年來人們的社會心理。現在三峽已是高峽平湖,靜若處子,雄奇一變而為秀美,隨著旅游的便利,其神秘感也在逐漸消失。
當下,三峽以綺麗的自然山水風光、古老的文化積淀與現代工業文明的偉大壯舉而享譽海內外。由于葛洲壩、隔河巖、三峽工程的建設,三峽區域的自然形態發生一定程度的改觀,人文景觀與自然景觀如何真正和諧統一,值得深思。
正因為如此,三峽工程被作為“文學的想象”而訴諸于人們的頭腦、訴諸于人們的心靈。三峽工程被放置在歷史的記憶里、文學想象的期待中。舍勒認為:“人是生命沖動的體現,又是精神活動的場所,人是生命沖動與精神之間的張力和運動的中介,他不棲居于某一邊。”(劉放桐,《新編現代西方哲學》)生命的沖動需要理性或精神來引導,精神的豐富與完美需要從生命的沖動和自然的律動中汲取源泉。自然,不再是想象中的自然。而自然中涌現出的人的精神、工程的價值、工程與人所生存的境遇之間的關系,比如,新的經濟關系、物質關系、社會關系需要建構,需要去填補逝去、彌合的文化、文學的虛空。三峽的“詩意的想象”需要重建。
如今,時代需要在工程世界中找到人的精神、人的靈魂、人的價值。千古如斯的三峽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化。隨著三峽流域的相繼開發,一個個工業文明的奇跡在這里出現,傳統的生活形態和現代化建設在同一時空下共生,古老文明與現代文明相互激蕩,歷史和現實交相輝映,搖曳多姿、異彩紛呈。這就是新時期三峽文學之生長點。工程文學需要來回答時代的期許。文學視野中的三峽工程,社會在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