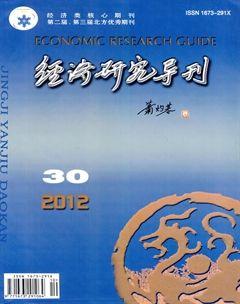基于Box—Cox模型的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實證分析
龔婷婷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處于年增長率高于8%的強大發展態勢,但因此也引來了來自各國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匯率到底該如何變化,歸根結底我們應該弄清匯率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將通過運用Stata軟件先對人民幣匯率進行Box-Cox轉換,再進行線性方程模擬,發現貨幣供給量、CPI均對其有正相關作用。最后提出幾點政策性建議。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Box-Cox轉換;正態性
中圖分類號:F82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2)30-0072-02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處于年增長率高于8%的強大發展態勢,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越高的經濟增長率將提高該國的實際工資增長率,從而使實際匯率上升地也越快。然而事實上,20世紀末東南亞金融危機后,盡管中國保持了高速增長,但是人民幣匯率跌幅超過了國內外通貨膨脹的差距,實際匯率仍大幅度的下跌,直至2005年匯改后才有所回升,但幅度也仍不明顯。故而日本于2002年最先提出了“中國威脅論”,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試圖說服其他國家向人民幣施壓,從而借以轉移國內持續了十多年的經濟低迷和通貨緊縮。而美國則在2010年初督促財政部在報告中將中國定位于“匯率操縱國”,認為由于人民幣被大幅度低估導致美國處于世界貿易競爭市場的不利地位,威脅將不惜一切代價對華進行嚴厲的貿易制裁。2012年5月的“第四輪中美戰略經濟論壇”上,美國更是再次急切敦促中國,要求人民幣必須加速升值的步伐。面對各方面的輿論壓力,中國政府給予了強硬的回應。國家總理溫家寶在2010年的兩會中表示,人民幣沒有被低估,強迫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匯率改革,況且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對世界經濟復蘇做出了重要貢獻。可見,目前各界對于人民幣升值的辯論非但沒有緩解,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匯率到底該如何變化?歸根結底,我們應該要弄清楚人民幣匯率到底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因此,本文將就這一問題在Box-Cox的基礎上做實證研究,不僅有利于中國對匯率制度的選擇與完善,更是在當今金融危機形勢下緩解中國對外貿易矛盾、緩和對外緊張外交關系的重要途徑,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匯率決定理論有很多。追溯至14世紀出現的國際借貸學說盛行于金本位制度時期,它認為,匯率是由外匯市場上的供求關系決定的,而外匯供求又源于國際借貸。它的缺陷在于沒有說清楚哪些因素是具體影響到外匯的供求。隨后的購買力平價學說認為,兩者貨幣間的匯率決定于兩國貨幣各自所具有的購買力之比,匯率的變動也取決于兩國貨幣購買力的變動。接著是1923年凱恩斯系統闡述的利率平價學說,該理論分析了兩國間的即期匯率與遠期匯率的關系與兩國的利率有密切的聯系。其主要出發點為投資者投資于國內所得到的短期利率收益應該與按即期匯率折成外匯在國外投資并按遠期匯率買回本國貨幣所得到的短期投資收益相等。一旦出現由于兩國利率之差所引起的投資收益的差異,投資者就會進行套利活動,直至遠期匯率固定在某一特定的均衡水平。在1944—1973年布雷登森林體系實行期間,各國采用固定匯率制度,期間的匯率決定理論也主要從國際收支均衡的角度來闡述匯率的調節,比如彈性論,只要符合馬歇爾—勒那條件貨幣貶值就會改善國際收支。而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后資本市場說成為了匯率理論的主流,更加強調資本流動在匯率決定理論中的作用,匯率被看作為資產的價格,由資產的供求決定。
當然關于匯率決定因素的實證研究也有很多。如Edward(1997)利用十二個發展中國家(巴西、哥倫比亞、薩爾瓦多、希臘、印度、以色列、馬來西亞、菲律賓、南非、斯里蘭卡、泰國和南斯拉夫)從1982—1995年的綜合數據,發現財政赤字對全部貨幣存量的比率、反映外匯短缺和出口價格對進口價格的比率表示的貿易條件的均衡市場匯率的差距等將導致實際匯率的增值,而名義匯率的貶值和產出的增長可使實際匯率貶值。Towe(1989)認為,1982—1987年間黎巴嫩鎊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受到居民手中擁有的流動的名義國內貨幣和國外貨幣、未來預期匯率和國庫債券擁有量的影響。謝杰(2010)通過對“巴拉薩—薩繆爾森”假說的擴展以及引入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的結論是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壓低了中國的實際匯率。陳伯云、萬家友(2008)選擇開放度、外國直接投資、勞動生產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因子組合,利用協整分析方法,得出前兩者與之負相關,后兩者與之正相關。
二、實證分析
(一)模型選擇:
從貨幣因素的角度來建立模型,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Y)為因變量,選用貨幣供給量(X1)、居民消費價格指數(X2)為自變量,得到擬合的模型方程:
Y =β+β1* X1 +β2*X2
其中,Y表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以直接標價法表示),X1表示中國的貨幣供給量M1,X2表示中國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理論上,X1上升使中國貨幣供大于求,貨幣對內貶值即國內物價上漲,使出口產品競爭能力下降,外國消費者對人民幣的需求下降,從而人民幣貶值,故預期β1為正;X2上升同理導致本幣貶值,預期β2為正。
(二)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對各變量均采取了2003年1月至2012年3月的月度數據。其中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數據、貨幣供給量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數據庫網站,CPI數據來自CCER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并且為了降低數據出現異方差的可能以及避開數據單位不統一的干擾,對數據統一取了log值。
(三)模型分析:
本文將運用10.0版的Stata軟件進行模型模擬。回歸得到如下結果:
Y = 1.925582 + 0.2102504 *X1 + 0.0140797 *X2
(29.57)(2.12)
發現R2=0.9008,表明這一方程可解釋匯率90.08%的部分,擬合性很好。兩個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水平為5%的t檢驗。X1的系數為0.21,表明貨幣供給量每增加1%,匯率貶值0.21%;X2的系數為0.014,表明CPI每增加1%,匯率貶值0.014%。均符合理論上的預期。
但是李志斌、劉園在《基于ARCH類模型的人民幣匯率波動特性分析》中使用ARCH類模型研究人民幣匯率波動特征,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波動劇烈,具有明顯的尖峰、厚尾、波動率聚類特征。而經典的回歸方法要求回歸的殘差符合正態分布,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回歸得到的結果才是無偏、有效和一致的。基于此考慮,本文將對上述模型進行Box-Cox轉換。
首先對其殘差進行正態分布的檢驗,其偏度和峰度得到如下結果:P值為0.0032,小于0.05,說明其偏度和峰度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不符合正態分布。因此本文考慮用Box-Cox變換,可能會得到更好的結果。
在Stata中運用Box-Cox變換得到如下方程
Y = 0.4724775 + 0.1030717 * X1 + 0.0157026 * X2
在方程解釋前須對轉換后的殘差再次進行正態分布的檢驗,發現P=0.1023遠大于0.05,滿足正態分布,表明了對此模型進行Box-Cox轉換的有效性。
而根據轉換后的方程,發現經過變換,貨幣供給量對匯率的影響大大降低,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影響則為微有上升,但依然不高。這種微弱的傳遞作用可能與中國不完善的貨幣市場以及不健全的價格監督體制有關。
三、政策性建議
基于上述對于中國人民幣匯率決定因素的分析,提出以下幾點建議:(1)完善貨幣市場,加強貨幣市場效率。比如增強貨幣市場的信息傳遞,可避免當前各個市場參差不齊的反應靈敏性,提高政策變動的靈敏性和連續性。否則由于信息的阻滯和失真,使其價格不能及時準確的反映市場的供求波動狀況。因而急需建立一套規范、有效地信息收集和披露制度。(2)加強物價監管,尤其是“菜籃子”價格。比如,政府應做好豬肉等主要副食品價格日監測和原材料的生產、屠宰和銷售情況的調查工作,做好防患于未然。嚴格打擊搭車漲價、串通漲價、哄抬價格等擾亂市場價格秩序的違法行為,準確把握市場價格走勢。(3)在金融危機影響依然存在的背景下,國際貿易的收益不確定性增加,貿易風險隨之增大,這將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對外貿易的增長,此時貿易風險的降低顯得很重要,尤其是匯率風險。作為政府,應當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保持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擴大人民幣的浮動幅度,適當放松外匯管制,但仍需要從整體上掌握一個“度”。
參考文獻:
[1]陳伯云,萬家友.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J].時代金融,2008,(6).
[2]裴平,等.國際金融學[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陶莊.Box-Cox變換及其在STATA軟件中的實現[J].數理醫藥學雜志,2007,(3).
[4]謝杰.人民幣實際匯率決定性因素研究——“Balassa-Samuelson”假說的擴展與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分析[J].南方金融,
2010,(6).
[5]Edwords S.Real and Monetary Determinants of Real Exchange Rate Behavior: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J].
NBER Working Papers Series No.2721,1987.
[責任編輯 陳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