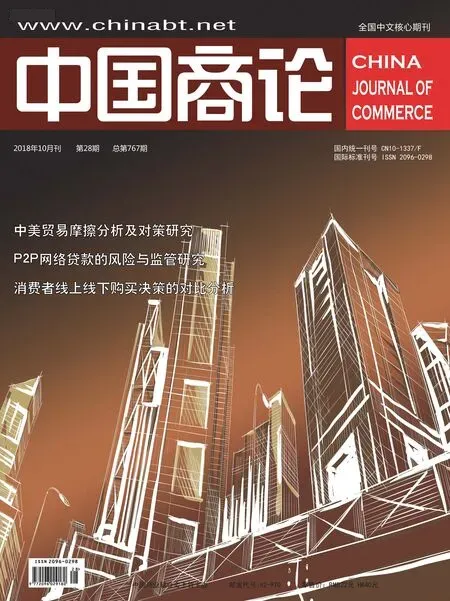預防性保護對商業秘密之必要性研究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 周琳
1 預防性保護是商業秘密秘密性的必然需要
商業秘密(Trade Secret),又稱秘密信息,世界貿易組織于《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稱之為未披露信息。現今各國大都將商業秘密作為一種法律術語對待,但由于各國在法律傳統等情況上的不同,各國對商業秘密的概念界定也采用不同的模式,因此在概念表述上會有所不同。如美國將商業秘密界定為“由于未能被可以從其披露或使用中獲取經濟價值的他人所公知、且未能使用正當手段即已經可以確定,因而具有實際或潛在的獨立經濟價值,同時在特定情勢下已盡合理保密努力的對象。”日本《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第2條第4款中將商業秘密界定為“作為秘密管理的生產方法、銷售方法以及其他對經營活動有用的技術上或經營上未被公知的情報”。我國對商業秘密的保護較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使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首次對商業秘密做出了列舉式的解釋,隨后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0條第3款中對商業秘密做了界定,“商業秘密是指不為公眾所知悉,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具有實用性并經權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術信息和經營信息”。雖然各國對商業秘密的表述不盡相同,但秘密性、價值性、保密性應是上述概念界定中的共同點。
相較于專利的公開性,商業秘密所有人可以在其領域或行業內獨享該信息的價值性源于其的秘密性。美國商業秘密法學家Melvin F.Jager認為,法律對商業秘密的惟一的、最重要的要求,即該商業秘密在事實上是秘密的,除卻這一先決條件,其他的條件也就毫無意義了。TRIP協議第39條第2款中,將秘密性界定為,該信息或整體上或要素上或要素的組合上“未被通常涉及該信息有關范圍的人普遍所知或者容易獲得”。在對秘密性的闡釋上,各國的做法大都與上述TRIPS協議相一致,但都不要求絕對秘密,只是一種相對秘密即可。具體說來,由于現今社會生產規模的擴大,商業秘密所有人必須將包含有商業秘密的工作任務授權或委托他人來予以完成,即在商業秘密的使用和管理中,一定程度的公開是無法避免的,所以從這一角度理解,要求信息的絕對秘密性是不可能的,因此該商業秘密只要不被同行業、相關領域或企業的人所知曉即可,在本企業內一定范圍的公開不視為秘密性的喪失。
商業秘密的秘密性具有難以恢復的特點,即其一旦泄露或使用其的秘密性將就此滅失,這也將給所有人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貓已經跑了出去,我們又如何能知道損失的程度及大小呢”。加之,商業秘密的非排他性,其又不能如專利般在被公開之后還享有法律賦予的一定時期的壟斷權。可見,商業秘密本身是一項脆弱的權利,對于商業秘密來說,最好的保護方式是使其永遠處于秘密的狀態,但法律又不要求所有人給商業秘密提供過分的、不合理的保護措施,而且這種“針也插不進去”的保密措施于現實中也是不可能的,而這也就決定了單憑商業秘密所有人合理的保密措施和法律的事后救濟是遠遠不夠的,比較理想的做法應該是防止商業秘密有侵害之虞情形的發生,將因商業秘密被泄露或非法使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其的目的總是先封堵住壩的漏口,再估計它的損失”。因此,從商業秘密自身特性考慮,法律應對其予以預防性保護。
2 商業秘密預防性保護的現實原因
馬克思曾指出:“社會不是以法律為基礎,那是法學家們的幻想。相反地,法律應該以社會為基礎。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質生活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可見,法律的產生是基于社會生活的現實需要,對商業秘密予以預防性保護也源于侵犯商業秘密的現實因素大量增多。
2.1 社會化大生產使得知曉商業秘密的主體日益增多
在經濟一體化的當下,各國處于一個全球性大市場的角逐與合作中,無論國籍、無論地域、無論組織形式,各種主體之間的貿易、合作、交流、聯系日益頻繁、日益密切。由于社會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商業秘密所有人必須將包含有商業秘密的工作任務授權或委托他人來予以完成,即在商業秘密的使用和管理中,一定程度的公開是無法避免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上述交流合作促進了經濟增長、實現了資源的合理配置,但也使得商業秘密被更多的人掌握和知曉的可能性增加,這也使得商業秘密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尤其在互聯網商業化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商業秘密依賴網絡而存在和傳遞,這就使得侵害商業秘密的途徑又增加了許多,相應地通過上述渠道知曉商業秘密的主體則更多,而這些對商業秘密的知曉與記憶均為日后侵權埋下了伏筆,像一顆定時炸彈般讓商業秘密所有人心神不寧,這時預防性保護對于商業秘密的重要性就日益顯現。
2.2 競爭的加劇為商業秘密侵權提供了現實的土壤
現今,不同國家的主體之間、同一國家的主體之間在全球化這個大市場中的競爭日益激烈,而主體間競爭的核心已從資源、設備等有形資產向專利、商業秘密這類無形資產轉變,這就使得企業對競爭對手商業秘密不顧一切地攫取。最初的商業秘密侵權大多是采取相對較明顯的方式予以盜取,而后又發展至商業間諜等專業手段對商業秘密的竊取,直至今日對商業秘密的潛在侵害——如通過合作獲取所有人的商業秘密,隨后擅自使用或轉讓他人,再如從產業鏈上游的核心技術人員處獲得相關商業秘密以使得自己在采購談判中獲得主動和優勢,又如將與之相競爭公司的核心人員“挖”到自己的公司來,以充分利用其積累的經驗、獲得的技術知識等,以上這些既節約成本又縮短研究和開發新技術過程的竊取方法被很多企業所偏好。
3 商業秘密預防性保護的經濟分析
法律對商業秘密予以保護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價值性,即源于其是所有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及財力后的凝結。
商業秘密的價值性是指一信息或技術能帶給其所有人經濟利益或相對于競爭對手的比較優勢。各國在對價值性的認定上都各有一定的側重,如美國《統一商業秘密法》中將價值性界定為“實際的或潛在的獨立經濟價值”,而日本則更強調其的現實價值,德國對價值性的認定強調其中的正當性,我國對于價值性的解釋是能為權利人帶來經濟利益且具有實用性,由于一信息或技術具有價值性就一定能被運用于實踐,因此實用性可以看做是價值性的內在含義。由此可見,各國對商業秘密均要求具有一定的價值性,但這種要求并不是絕對的,只要具有相對價值性和相對優勢即可。在對價值性的認定上,傳統理論都是從正面角度來理解,即只有那些正面的、積極的信息才能認定為具有價值性,但上述對價值性的理解過于狹隘和局限。美國在此問題上的認定比較寬泛,消極的信息如對所有人或競爭者有使用價值,可為其避免經濟上的損失,也可被認定具有價值性。如一家醫藥公司經過多年耗費巨資研究開發一種新藥品,但幾年下來并不順利,按照傳統理論,這些研究新藥品失敗的資料應不具有價值性,但對于企業來說,這些失敗的資料可以成為其繼續研究開發的參考,可以排除那些不適宜的方法和思路,更接近最后的成功;另一方面對于企業的競爭對手而言,如果其獲得這些失敗的資料,其就可以避免那些不可能的開發路徑,縮小研究的范圍,節省研發支出,更為關鍵的是獲得時間上的優勢。所以說,只要一信息能為其所有人或競爭對手中的任一方帶來現實的或潛在的、積極正面的或消極負面的經濟價值或競爭優勢,都可認為具有價值性。
一方面,由于商業秘密的價值性,法律須對由其價值性而引發的利益關系予以規制;另一方面,從社會發展的整體角度看,如果不對個體的研發成果和具有經濟價值的信息予以法律保護,那么個體將不再致力于新科技的研究與現有科技的再創新,從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正如“專利就是給天才之火澆上利益之油”一樣,法律賦予所有人商業秘密權也是通過對所有人利益的保護來堅定其不斷創新的意志。另外,相對于商業秘密所有人付出的時間、金錢和精力等方面的努力,侵權行為人通過對他人商業秘密的盜用而獲得的利益則是無任何對價可言的。從這個角度說,對所有人投入后獲得的商業秘密予以保護也是公平原則的體現。
如果說,價值性是商業秘密保護的根本原因,則基于商業秘密的價值性,對其予以預防性保護則是源于經濟學上的理性經濟人原則。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是指作為經濟決策的主體都是理性的、利己的,在面臨兩個以上選擇時,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方案,這是西方經濟學家對人類經濟行為的一個假設,也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觀點。對于商業秘密所有人來說,在面對商業秘密預防性保護和商業秘密被侵權后的事后救濟這兩個選擇之時,由于商業秘密一經破壞即不復存在的脆弱性使得預防性保護是一個更經濟、利己的選擇,因此其會更傾向于事前的預防性保護這種理性的保護方式。
4 結語
商業秘密自身的法律屬性決定了其的脆弱性,社會化大生產下的委任則使得知曉商業秘密的主體逐漸增多,這些都為商業秘密侵權留下了隱患,而競爭的加劇又使得企業對競爭對手商業秘密不顧一切的攫取,對商業秘密侵權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對商業秘密予以預防性保護——將上述可能導致商業秘密侵權發生的可能性降至最小,從而將商業秘密權利人的損失降到最低,對于商業秘密所有人來說應是最經濟、最理性、最利己的優先選擇,也是基于商業秘密知識產權屬性的絕對性保護的當然內容之一,其與事后救濟共同構成了商業秘密的保護體系。
對于商業秘密所有人來說,其自身針對無處不在的侵害商業秘密的危險,在增強商業秘密保護意識的同時,要加強相關的制度建設,具體可包括有關商業秘密自身的管理制度和相關人員管理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具體而言,前者如門衛管理系統、密碼數據系統等,后者如聘任制度、員工獎勵機制等。除此之外,要善于運用保密合同和競業禁止合同來防止商業秘密侵權的發生,將可能導致商業秘密泄露或使用的可能性降至最小。
[1]白云飛,巴志成.商業秘密系列知識問答(九)[J].電子知識產權,1998(11),轉引自吳漢東:知識產權基本問題研究.
[2]張玉瑞.商業秘密法學[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
[3]Melvin F.Jager.Trade Secret Law.Clark Boardman Company Ltd., 1985.National Starch & Chem.Corp.V.Parker Chem Corp.,530A.2d 31,33(N.J.Super.Ct.App.Div.1987).
[4]李明德.杜邦公司訴克利斯托夫——美國商業秘密法研究[J].外國法評論,2003,34(3).
[5]R.Mark Halligan.Trade Secrets and The Inevitable Disclosure Doctrine.http://rmarkhalligan.com.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7]王洪亮.物上請求權的訴權與物權基礎[J].比較法研究,2006,26(5).
[8]王利明.民法侵權行為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