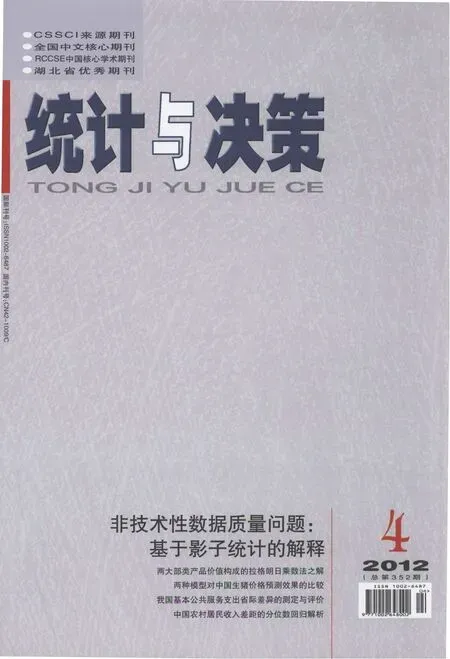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收斂性的實證研究
劉夢琴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武漢 430074)
0 引言
武漢城市圈成立于2004年,是以武漢為中心,由周邊100公里范圍內的黃石、鄂州、孝感、黃岡、咸寧、仙桃、潛江和天門8個城市構成的華中城市圈,又稱為1+8城市圈。武漢市城市圈地處中部六省“中部之中”,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有承東啟西,連南接北的優越區位優勢,是我國“兩橫兩縱”城市化戰略格局中長江橫軸和京廣縱軸交匯處,也是長江中游水陸交通重要樞紐;資源稟賦條件優越、人口和產業集聚程度較高、科技教育與智力資源優勢顯著,是中部崛起的戰略支撐。武漢城市圈是湖北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區域,是湖北省人口、產業最為密集的地區;從城市化角度看,武漢城市圈城市化進程較快,區域內聚集全省43%的城市,城市空間布局緊密。隨著“中部崛起”戰略的確立,以及“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建設的穩步推進,武漢城市圈的經濟發展快速提高,區域綜合經濟實力顯著增強。武漢城市圈正向集聚化發展,產業吸引力、集聚效應、輻射帶動能力正逐步顯現。在此背景下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問題就有一定的研究意義。
從經濟增長收斂性研究的成果來看,由于研究的視角、采用的分析方法以及考慮的經濟變量的不同,得到的結論也不盡相同,甚至有的結論相反。總體上看,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整體上不存在絕對收斂,地區內部之間可能存在條件收斂或者俱樂部收斂,但收斂的速度值的測算結果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結合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構建新的研究模型,分析武漢城市圈內部各城市之間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問題。
1 理論模型
經濟增長的收斂性是指在封閉的經濟條件下,對于一個有效經濟范圍內的不同經濟單位(國家、地區或城市)初期的靜態指標(人均產出、人均收入等)和其經濟增長速度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即落后經濟體比發達經濟體具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從而導致各經濟體初期的靜態指標差異逐步消失的過程。可以通過以下公式定義經濟增長的收斂性:

式(1)中yr為發達經濟體的人均產出(或人均收入);yp為落后經濟體的人均產出(或人均收入);>0保證經濟體得增長率為正;t為時間,t→∞的經濟意義為經濟收斂性實際測度的是較長時間段里經濟增長狀態。根據考察收斂性角度的不同,通常將經濟的收斂性分為三種假說:δ-收斂、β-收斂和俱樂部收斂。考慮到俱樂部收斂研究的是初期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經濟集團,內部不同經濟體之間在具有相識結構特征前提下區域收斂;而武漢城市圈內各城市間初期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且比較的對象為單個城市;因此本文只研究武漢城市圈經濟發展的δ-收斂和β-收斂。
1.1 δ-收斂
δ-收斂可以理解為橫截面經濟數據的收斂性假說,指的是各個經濟體之間人均收入水平或人均產出水平隨時間的推移而縮小的趨勢。但對于不同的經濟體來說,平均水平的值可能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根據各自的標準差,無法比較經濟的分散或收斂程度。此時可以通過變異系數對不同經濟體的發展趨勢進行相對比較。因此,變異系數可以檢驗不同經濟體經濟增長的δ-收斂性。變異系數(CV)表示為數據偏離均值的相對差異,計算公式如下:

1.2 β-收斂
β-收斂是指初期人均產出(或人均收入)較低的經濟體趨于在人均產出增長率、人均資本增長率等人均項目上比初期人均產出水平較高的經濟體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即不同經濟體間的人均產出增長率與初期人均產出水平負相關。β-收斂可分為β-絕對收斂和β-條件收斂,β-絕對收斂是指落后經濟體比發達經濟體有更快的發展速度,并最終達到相同的穩定均衡狀態;β-條件收斂是指經濟體的增長由于自身初始狀態不同而收斂到不同的穩定均衡狀態。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得到Solow-Swan[3]模型與R.J.Barro&X.Sala-I-Martin[4]的收斂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i為某一經濟體;t表示某一觀察期初的時間點;T為觀察期的長度;logYi,t+T為觀察期末的人均GDP的對數;logYi,t為觀察期初人均GDP對數;X*i為穩態條件下的人均產出增長率;Y*i為穩態的人均GDP;β為人均GDP向穩態人均GDP收斂的速度;μi,t表示隨機誤差項。如果β>0,地區經濟收斂,β值越大,收斂速度越快;反之,則發散。當收斂速度β>0一定時,如果地區經濟離其穩態水平越遠,那么該地區在T期內的年均增長率就會越高于穩態經濟增長率。經濟水平較低的地區的增長率高于經濟水平較高的地區,地區差距從長期看就會逐步縮小,區域經濟增長呈β-絕對收斂。對式(3)化簡可以得到:

2 實證研究
2.1 數據說明和模型選擇
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內生經濟增長理論,人口增長分別是影響經濟穩態均衡水平和經濟增長率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各城市的人口增長率衡量人口增長,記為n,單位為%;資本在不同區域的配置是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資本有兩種存在形態:物資資本和人力資本形態。本文選取各城市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衡量物資資本,記為,單位%;各城市人力資本水平用全社會就業人數和在校高等教育大學生人數之和表示,記為H,單位為萬人;外商直接投資直接通過資本形式和間接增加就業、出口等形式對經濟增長的產生影響。本文用FDI表示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資,單位為億元。人均GDP增長率衡量城市經濟增長。選取樣本區間為1999~2010年,除人口增長率和人力資本其他數據采用2000年為基期的不變價測算,以地區名義人均GDP計算出GDP平減指數,各城市實際地區GDP、人均GDP、固定資產投資、外商直接投資都用GDP平減指數調整得到。
原始數據來源于《湖北省統計年鑒》,各城市統計年鑒和《崛起之路——湖北輝煌60年1949~2009》。
根據經濟增長收斂理論,本文首先用式(4)所構建的模型檢驗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的β-絕對收斂性。若不存在β-絕對收斂,考慮到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構建以下模型檢驗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的β-條件收斂性。

其中,ni,t為各城市的人口增長率;表示各城市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H表示各城市人力資本水平,FDI表示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資。
2.2 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的δ-收斂性檢驗
本文采用變異系數來考察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的δ-收斂性,分別從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年人均純收入角度,對武漢城市圈經濟發展過程中δ-收斂進行檢驗。

圖1 武漢市城市圈經濟發展δ-收斂性檢驗
從總的趨勢來看,武漢城市圈1999~2009年的三種變異系數都是逐步降低的,表明在這期間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存在δ-收斂。從人均GDP的角度來看,人均GDP變異系數明顯比其他兩種變異系數大,從1999年的0.72緩慢下降到20004的0.59,再到2006年0.49,這兩年下降的幅度比較大,之后變異系數變化趨緩。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年純收入的變異系數在數值上相差不大,變化趨勢大體一致;從2002年開始農村人均年純收入的變異系數開始超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變異系數,差距也逐漸拉大,到2005年差距達到最大,為0.06,之后差距又逐步縮小,但農村人均年純收入的變異系數仍大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變異系數。綜合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武漢城市圈經濟發展具有δ-收斂特征,但是在總的存在收斂的前提下,三項指標有各自的變動情況。比較而言,人均GDP變異系數數值較大,下降幅度較大。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人均年純收入的變異系數數值較小,變動趨勢一致且幅度較小。
2.3 β-絕對收斂性檢驗
為了反映經濟收斂性的動態過程及充分利用數據信息,本文選擇觀察期為3(T=3)將1999~2010年數據劃分為5個時間段,即以1999~2003年分別為起始年份。利用面板數據對武漢城市圈經濟β-絕對收斂性做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武漢城市圈經濟發展β-絕對收斂性檢驗
由表1可得:各方程擬合優度在90%左右,DW值在2左右,說明各方程擬合的較好,不存在自相關;β系數都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所有的β<0,說明1999~2010年武漢城市圈經濟體間不存在顯著的β-絕對收斂性,各城市之間的經濟差距不能通過經濟自身絕對收斂而消除。從β取值來看,雖然β取負值但隨著基期的選擇接近于武漢城市圈成立的時間,β取值越來越大并接近0,存在β符號變正的可能性。隨著武漢城市圈一體化發展的進程,各城市間經濟發散的程度越來越小,經濟發展可能趨向于絕對收斂。
2.4 β-條件收斂性檢驗
武漢城市圈經濟發展不存在β-絕對收斂,是否存在β-條件收斂?根據前面的分析,采用式(5)所構建的模型,利用面板數據對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的β-條件收斂進行檢驗。本文以1999為基期,選擇觀察期為3(T=3),考慮到城市的人口增長率與人力資本水平,全社會固定資產
投資占GDP的比例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具有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特征,包含所有變量的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因此對檢驗模型采取逐步引入四個變量的研究方法,分別得到以下模型,檢驗結果見表2。


由表3的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所有模型擬合優度在0.4以上,整體可以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不存在自相關性,說明檢驗結果基本可信。但囿于統計資料的缺失和時間跨度較短,檢驗結果可能存在一定誤差,采用面板數據方法可部分改善檢驗結果。
檢驗模型Ⅵ包含了所有的解釋變量,雖然擬合優度相對較大,F值通過顯著性檢驗,但人力資本和FDI變量前的系數不再顯著,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系數的顯著性減小。說明檢驗方程存在多重共線性,采用逐步引入研究變量的方法是正確的。

表2 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β-條件收斂檢驗結果
檢驗模型Ⅰ—Ⅴ在絕對收斂檢驗模型的基礎上,逐步引入城市人口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例、城市人力資本和外商直接投資。所有檢驗結果表明:β>0,說明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存在條件收斂,并且收斂速度為2.2%~3.3%之間。人口增長率系數顯著為負,人口增長率增加,經濟增長速度下降,說明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起阻礙作用。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例、城市人力資本和外商直接投資系數都為正且數值依次減小,說明這三個變量對經濟增長起推動作用,但作用程度依次減弱。模型Ⅱ、Ⅲ考慮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系數大約為1.4,說明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貢獻,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主要還是通過投資來推動。模型Ⅲ、Ⅴ考慮城市人力資本的影響,兩個模型的系數差異較大,但數值都較少,說明人力資本對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大,這與武漢城市圈人口和智力資源優勢不相符,說明人力資源優勢效率還沒有充分發揮。未來武漢城市圈各城市應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尤其應該增加教育投入。模型Ⅳ和Ⅴ考慮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最小,約為8 E-06。這與武漢城市圈地處我國中部內陸有關,外商在此區域內除武漢市投資較大以外,其他8個城市的投資較少,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促進作用不明顯。
綜合以上分析的結果可以認為:在武漢城市圈的經濟增長中,加入人口增長、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例、人力資本、外商直接投資等變量后,城市間經濟增長存在比較明顯的β-條件收斂。人口增長對人均經濟增長的作用為負面的,較高的人口增長率盡管會增加經濟總量,但經濟總量的增長率小于人口增長率或者增加的實物資本滿足不了人口的增長,會降低人均經濟水平和人均資本積累,而人均資本積累是人均經濟增長的重要決定因素。人口增長率提高與人均經濟水平呈負向關,這和新古典經濟理論相一致。固定資產投資、人力資本、外商直接投資等變量對經濟增長都具有正向推動作用,但作用程度各不相同。這些因素都是促進經濟落后的城市快速發展,追趕經濟發達城市的必要條件。
3 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本文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從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年人均純收入角度來看,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過程存在δ-收斂。
(2)1999~2009年武漢城市圈經濟體間不存在顯著的β-絕對收斂性,但隨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的發散程度越來越小。
(3)在加入人口增長、固定資產投資、人力資本、外商直接投資等變量后,武漢城市圈經濟增長存在比較明顯的β-條件收斂,收斂速度為2.2%~3.3%之間。
以上研究表明:僅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無法將地區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如果區域經濟發展日益擴大,將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和諧因素,影響城市圈效率的發揮。為此,政府應結合城市圈發展階段因時制宜制定政策統籌區域發展,實現城市圈內經濟社會協調平衡發展。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控制人口增長,加大資本投入,有效引入外資。在城市化進程中,人口增長和聚集為城市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必要的勞動力,但人口增長也會降低人均資本積累,阻礙經濟增長。各政府應有計劃的控制人口增長率和人口結構,使之與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相一致,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武漢城市圈在依靠政府大量的物資資本投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更應注重人力資本的投資。各城市應根據實際需要,采取適宜的投資策略,不可只著眼與短期經濟效益,盲目進行大規模固定投資;同時充分發揮區域內教育與人才優勢,鼓勵高校和科研單位與企業聯合,加快產-學-研一體化進程。積極開展招商引資工作,建立統一的招商引資平臺,構建良好的招商引資機制,創造良好的招商引資環境,打響武漢城市圈整體招商品牌。
強化政府在平衡城市圈經濟發展的能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自身存在固有缺陷,需要政府通過宏觀調控來指導城市圈經濟的平衡發展,且武漢一城獨大,其他城市參差不齊的局面更需要政府在整個宏觀層面上予以協調。武漢城市圈在加強城市間政府服務職能協調溝通之上,各政府要積極支持和引導各類企業各自發揮區域優勢,同時進行跨行政區域優化配置資源,建立利益協調共享機制。突破行政體制障礙,以市場為導向、利益為紐帶,采取“市場主導、企業主體、政府推動”的模式,推動武漢城市圈建設。
加強城際交流和協作,推進城市圈一體化發展。城市圈的發展并不是以某一個中心城市規模與實力的增長來實現,而是通過一體化發展取得的。武漢城市圈建設存在的一大難題就是武漢首位度太高,其他城市發展不能與之協調。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充分發揮好武漢市核心城市職能和帶動效應的同時,加強城際交流和協作。其他城市的發展政策和定位以武漢為基準,突出各自優勢,注重產業配套協調有序發展,避免重復投資建設。即按照產業梯度分工和社會化大生產原則,以構建產業鏈為主線,加快武漢與周邊城市的產業對接,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多贏共贏。
[1]R.J.Barro,X.Sala-I_Martin.Technical Diffusion,Convergence and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7,(2).
[2]R.J.Barro,X.Sala-I-Martin.Technical Diffusion,Convergence and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997,(2).
[3]羅仁福,李小建等.中國省級經濟趨同的定量研究[J].地理科學進展,2004,(1).
[4]劉木平,舒元.我國地區經濟的收斂與增長決定力量:1978~1997[J].中山大學學報,2000,(5).
[5]Jian Chen,Belton M.Fleisher.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996,22(2).
[6]申海.中國區域經濟差異的收斂性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99,(8).
[7]胡鞍鋼.中國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研究[J].財經研究,1995,(10).
[8]劉強.中國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分析[J].經濟研究,2001,(6).
[9]李祥.從經濟收斂假說看增長理論[J].經濟科學,2005.
[10]蔡日方,都陽.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的趨同與差異[J].經濟研究,20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