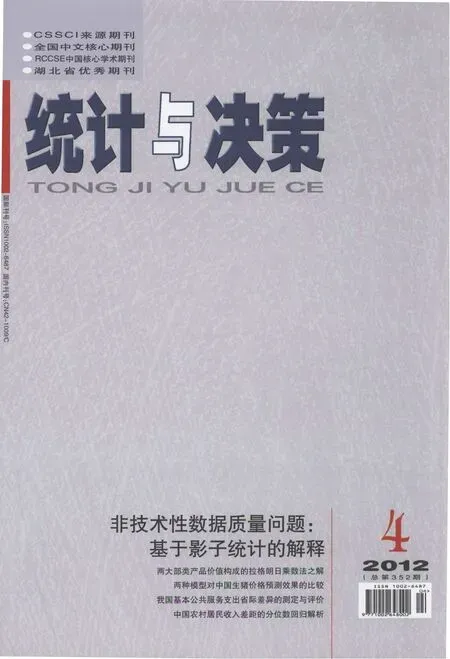境外高速鐵路商業模式的借鑒與啟示
錢桂楓
(河海大學 商學院,南京 210098)
0 引言
高速鐵路作為一種安全快捷、綠色環保、效率最高的旅客運輸方式已經成為共識[1][2]。伴隨著鐵路技術的變革,高速鐵路的供給方式,即投資建設和運營服務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經歷了從完全政府供給,到部分私有化、民營化的改革,形成了目前公私合作供給的主流模式[3][4]。
各國實踐表明,高速鐵路的高效供給,不僅要解決技術和投資的問題,而且還必須要創立一個符合本國國情的高效率實施的商業模式。盡管各國采用的商業模式各不相同,但是其核心內容包括了組織架構、所有權結構、使用費的制定(鐵路不是獨家經營的情況)及融資的資金來源。這些核心內容不僅決定了參與者所分擔風險的程度,而且還決定了高速鐵路公私合作供給機制的成敗。中國高速鐵路發展起步晚,要實現高速鐵路的高效供給,應該充分學習借鑒國外經驗,深入研究境外在高速鐵路公私合作中所實施的商業模式。
1 境外高速鐵路的主要商業模式
1.1 完全公營模式
高速鐵路的完全公營模式是指公營部門擁有高速鐵路的所有財產權和管理權,負責高速鐵路系統的設計、施工、車輛采購、基礎設施維護和運營服務,并制定價格和獲得票務收入等。在此模式下,公營部門承擔所有風險,并能夠在減少污染排放、減輕汽車擁堵、改善交通安全等方面承擔起社會責任,同時還要確保所制定的票價能夠使得公眾獲得最大的收益。這種完全公營模式通常是以滿足公共利益需要為主要目標,但其營業收入往往不能支付財務成本。因此,這種模式通常被許多國家用于市內大眾交通。但是,高速鐵路服務內容不同于市內公共交通,這種模式下的公營部門常常處于公營實體地位,與私營航空公司和公交公司及個人汽車用戶產生不公平的競爭,既不利于提高高速鐵路供給效率,也不利于促進整個交通行業的發展。
完全公營模式的典型案例是韓國高速鐵路。韓國新線高速鐵路分為三個階段建設和投入運營。第一階段首爾至大邱(224km)段于2004年完工。第二階段大邱至釜山(196公里)大部分路段于2010年11月通車。大田和大邱(41 km)的城區改造將于2014年完工。韓國高鐵由政府擁有的鐵路網機構——韓國鐵道施設公團建造,98%資金由政府貸款和撥款,2%為私營貸款資金;政府擁有的客貨運公司——韓國鐵道(Korail)成立韓國高速鐵道分支機構(KTX)負責高鐵運營,不存在互相競爭的運營商。由于韓國鐵道施設公團和韓國鐵道均為政府所有,除很少一部分私營貸款外,基本上所有施工、融資及經營業績風險由公營方承擔。目前該高速鐵路的運量需求比預測高,韓國高速鐵道(KTX)已產生運營盈余,但尚無確切數據表明其盈余是否能足夠支付高速鐵路的基本建設投資。
1.2 公私合作模式
1.2.1 管理承包模式。
管理承包模式是指公共部門負責規劃、建造和對整個系統提供融資,與私營實體單獨簽訂維護和運營管理合同。大量的美國鐵路客運系統的短途運輸按照這種模式運作,由美國鐵路公司作為獲得成本補償的運營商為各州提供服務。該模式也是歐盟使用的私營部門參與鐵路旅客運輸服務的一種新興模式。
這種模式適用于社會效益強、且通過管理合同競爭能產生更為有效運營的項目。為了保證社會利益,價格由公共部門制定。公共部門往往基本保留所有成本和需求風險,按照管理合同的約定可以向承包商或者特許管理者轉移一定的運營成本風險,也可以要求特許管理者給企業帶來商業和經營技術。根據營收及特許管理者被允許保留的營收份額,公營代理機構可以向特許管理者提供或不提供“運營補貼”。
1.2.2 “總成本”特許經營模式。
“總成本”特許經營模式是指公共部門負責規劃、建造和對整個系統提供融資,通過競爭將基礎設施維護和經營權特許給承包商。公共部門負責投資,承擔需求風險;特許權承包商承擔特許范圍內的經營成本風險。
該模式適用于公眾利益占主導、具有一定盈利能力的項目,如德國、瑞典等短途鐵路運輸采用此模式。特許運營商提供商業及運營專門服務,根據營運收入及特許經營者被允許保留的營運收入份額,確定公營部門是否提供“運營補貼”。
1.2.3 長期“凈成本”特許經營。
長期“凈成本”特許經營是指公共部門對一個系統進行規劃和建造,使其符合公共部門期待的基本運輸要求,向各潛在特許運營商進行該系統長期(15-30年)獨家運營的招標。特許運營商進行定價、開展需求預測及決定列車開行班次及運能(根據標書中確定的條件)、提供車輛及任何其它運營上的重要資產。根據系統的運營能力及票價的限定,特許運營商可能愿意向公營部門支付施工或運營款項。
運用該種模式的典型案例是英國HST-125高速鐵路的服務。英國三家長途特許運營商獲得該線路的特許經營,提供時速125英里的服務。第一大西部鐵道公司(First Great Western)取得倫敦到加的夫的特許經營,維珍西岸(Virgin West Coast)取得倫敦到格拉斯哥的特許經營,東海岸(Eastern)取得倫敦到愛丁堡的特許經營。這些特許運營商采取了“凈成本”方式,即在法規許可的“標準”票價范圍內,為取得特許權向政府支付費用,對部分需求和營收風險及包括應支付的使用費在內的運營成本風險負責。
這種模式適用于那些服務商業化、私營收益在整個收益中起較大作用的項目。該模式下,公營部門依然保留所有基礎設施建設成本風險,能轉移部分商業和運營成本風險,包括車輛相關成本及需求風險等。根據采用的特許支付方式(事先固定、總收入或凈收入分享),公營部門能夠收回部分或較大比例的基礎設施建設成本。
1.2.4 基礎設施分離模式。
基礎設施分離模式是指公營部門設計建造基礎設施,而后允許一家或數家高鐵運營商提供運營服務。公營部門根據運能和相關要素(備用列車運行線、列車運營里程、運營總噸英里等)收取使用費。該模式運用的典型案例是在歐盟各國。
在這種模式下,公營部門仍然基本保留包括維護在內的所有基本建設成本風險,并須就使用費等問題做出決策。同時,可以通過競爭途徑,實現高速鐵路運營的完全商業化,將一部分需求風險和營運成本風險轉移給運營商。
1.3 基本私營模式
基本私營模式是指公共部門發揮其職權獲取路權,制定系統規范,將獨家特許經營授予一家私營聯合體在規定的期限內(通常是30年以上)甚至是無限期,來設計、建造、融資、運營及維護高鐵系統。這一模式原則上能將全部成本和營收風險轉移給私營企業,并根據監管部門的政策,可以對公共部門的投入成本提供資金。截止目前的高鐵實踐,基本私營模式案例主要有,臺北至高雄的高速鐵路采用BOOT(建造擁有、運營移交);英法海底鐵路隧道采用BOO(獨家建造、運營擁有)模式。
臺北與高雄之間的高速鐵路最初的商業模式是按照完全私營模式設計的。BOT特許經營權由臺灣高鐵公司享有,該公司是5個股權人建立的聯合體,特許經營權為35年。期間,臺灣高鐵公司每年向當局支付10%的稅前利潤作為路權租賃費用,以用于鐵路發展。
然而,高鐵系統在運作中并沒有按照最初設想的那樣運行。由于在建設中車輛的設計問題及日本設計的車輛與歐洲設計的基礎設施之間的集成問題,出現了延期和成本超支的現象;同時,實際運輸需求比預計的低得多。截止2009年9月,當局不得不向臺灣高鐵公司投入資本,將股份提高至36.2%,而5家原始股東擁有27.9%股份。在債務需要由臺灣高鐵公司全部償還的特許經營約定下,當局將被迫在所有權和財務負擔方面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
臺灣高鐵的實例證明,高鐵風險分配的最初嘗試是不切實際的。一方面,建立私營聯合體的目標是由私營方承擔規劃及監管以外的幾乎所有的風險,但由于日本和歐洲設計理念差異產生集成問題造成工期延誤,且臺灣當局對使用日本而不使用歐洲車輛的決策施加影響,從而使自己處于工期延誤的風險中。另一方面,當初期需求明顯不能提供足夠運營收入來彌補還本付息時,當局不愿強迫臺灣高鐵公司宣布破產,并重新安排其責任,因此風險只能由政府負擔。
英法海底鐵路隧道是另一基本私營化運作的案例。英法海底鐵路隧道,即英吉利海峽隧道在拿破侖時代就開始了規劃和巖土分析,在英國政府(撒切爾)的堅持下,1986年將一個100年設計、施工、融資運營及維護(DBFOM)的特許授予了英法海底隧道集團,英法海底隧道集團由國際私營投資人支持的英法施工公司組成的聯合體來領導。原來預算約為47億英鎊,隧道最終的成本高出一倍,大部分成本是貸款融資。在開通后不久,因為需求遠遠低于預測,并遠遠低于償還債務需要的資金數額,隧道集團無法償還債務。2006年對公司進行了重組,降低了債務和利息。為了盡量多地收取使用費,英法海底隧道向所有列車運營商開放,包括歐洲之星(客運),歐洲隧道區間列車及貨運列車;同時還對往返客運汽車和帶拖車的卡車等實行了開放。與歐盟大部分鐵路相比,英法海底隧道使用費主要組成是固定的,因此將需求風險轉給了使用者。英法海底隧道似乎將基礎設施資本成本風險從政府轉向了私營商,但是原股東幾乎損失了所有投資,債券持有人成為股東。而且隧道使用費至少將一部分需求和運營成本風險轉給歐洲之星和貨運運營商。
在私營收益超過私營成本,且公營部門不干預工程的情況下,基本私營模式才具有可行性,這種模式下基本私營模式能將全部成本和營收風險轉移給私營企業。但是就臺灣高鐵實施來看,風險全部轉移的目標并沒有實現;英國海底隧道在實施過程中,也不得不通過重組和調整來維持運行。可見,在沒有政府支持,讓私營部門承擔高速鐵路的客流量和投資的全部風險,其可行性仍需充分論證。
1.4 其他組合模式
上述三大類模式的運用也有各種變化,有些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同一國家內對于不同的項目可以采取不同的組合模式。例如,地方政府可以對車站的施工和運營提供資助,以分享高鐵系統帶來的當地發展效益;電力公司可以對整個供電系統提供融資并進行建造,以獲得適當回報率的電費協議。另外,管理合同、總成本特許經營的界限并不很嚴密;隨著實際成本和需求經驗的取得,有可能將總成本特許經營轉換為凈成本特許經營;基礎設施分離模式可以與總成本或特許凈成本或者與非特許權下的私人運營方式組合使用。
日本新干線從初期建設、投入運營到完成私有化改革,實現了從完全公有模式到公私合作模式的轉變,經歷了經營模式及風險分配的根本變化。從1964年至1987年,新干線所有線路由政府擁有的日本國有鐵路負責修建、擁有、運營。全部資金由公共部門支持,所有風險均由公營方承擔。由于日本國有鐵路商業目標意識淡漠,逐漸演變成了高成本、不經濟的公營企業,年度虧損達150億美元、總債務達2500億美元。1987年開始政府決定實行私有化改革。老的日本國有鐵路被拆分為六個客運鐵路公司、一家貨運公司、一個新干線線路公司及一家結算公司。東日本鐵路,中日本鐵路、西日本鐵路(稱為日本鐵路)是本州島的三家主要客運公司,其股份在東京證交所出售,政府不再持有所有權股份。作為私營公司,日本鐵路擁有其全部基礎設施并負責運營,不需為此支付使用費。新干線線路公司擁有新干線,并將線路租賃給這三家主要客運公司。新的高鐵基礎設施由日本鐵路建設運輸技術署修建并擁有,將設施進行租賃,獲取年費。年費根據日本鐵路使用線路產生的預計的收益(利潤)確定。新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約80%的融資以出資和撥款的形式,日本鐵路也提供部分資金支持;新的車輛完全由日本鐵路出資支持。
改革的最后結果是經營模式和風險分配從典型的國有企業經營模式迅速轉換成至少“部分”PPP方式的經營模式。規劃、監管和路權取得的風險由政府部門承擔。建設成本風險由日本鐵路建設運輸技術署承擔,成本風險可傳遞給將要求增加成本的中央與地方政府。日本鐵路承擔基礎設施維護成本風險、車輛擁有權及維護風險。當需求高于預計、運能不足時,需求風險由日本鐵路建設運輸技術署承擔;當需求低于預計,車輛運能過高時,由日本鐵路承擔需求風險。大部分融資風險由公共機構承擔,車輛及房地產等其它投資風險由日本鐵路自主承擔。
2 各種商業模式比較分析
2.1 不同模式下公私營部門的作用比較
各國對高速鐵路實施商業模式的選用與其政治經濟體制、國家發展鐵路政策、以及市場化發展程度等關系密切,不同模式下所有權結構、公私營部門所起的作用不同。按照高速鐵路供給鏈主要業務進行分解,可以分為路權、軌道、電力與牽引、通信與信號、車輛及運營管理等。表1分析比較了不同模式下公私營部門控制和擁有高鐵系統相關業務和資產屬性。

表1 高速鐵路不同商業模式運作情況和資產屬性

表2 高速鐵路PPP模式特征與適用條件
2.2 高速鐵路公私合作模式適用條件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高速鐵路系統從規劃到設計、建造、運營、維護是個龐大的十分復雜的系統,各種模式下公私營部門所起的作用不同。各國對高速鐵路商業模式都予以了高度重視,原因在于希望所設計的模式能發揮公私部門的各自優勢,有利于籌集資金、降低風險、促進競爭,提高供給效率。隨著自然壟斷理論的發展,人們對鐵路完全公營模式存在弊端的認識逐步形成共識[5][6],公私合作共同承擔高速鐵路供給的責任成為主流模式。表2詳細分析高速鐵路公私合作(PPP)模式下的風險管理、融資責任和適用條件。
3 境外高速鐵路商業模式研究的啟示
(1)對境外高速鐵路實踐研究表明,高速鐵路實施可以采用不同的商業模式,模式的選用取決于國家政策及融資角色、高鐵系統發起者的風險轉移目標、參與者的收益和成本的預期。組織結構、所有權安排、清算辦法是公私合作實施高速鐵路的最為核心的問題,決定了風險在參與者之間的分配和模式運作的成敗。
(2)高速鐵路公私合作供給已逐步成為主流模式。政府在路網規劃、路權取得,項目推動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私營部門在高速鐵路中的作用越來越得到各國重視,但是私人資本的風險承擔能力是相對有限的,截止目前的全球高鐵實踐表明,尚沒有完全依靠私營部門融資和修建高鐵系統的成功案例。高鐵系統復雜,實施過程要應對各種風險,其中需求風險不能全部轉移,不論私營合作伙伴能提供什么樣的保證。
(3)從組織結構看,將基礎設施提供商和運營商分離、組建區域公司,以引進同類型業務競爭是高速鐵路的最為常用的形式,這種形式被高速鐵路發展起步較早的日本、法國、英國所采用,也為剛剛發展的韓國等國家所采用。歐盟為此制定了可供借鑒的總體政策框架,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均遵循此規定。
(4)從產權結構看,高速鐵路所有權結構有多種形式。包括完全國有形式,如韓國、瑞典、西班牙、德國(2008年上市計劃因故推遲);完全私營形式,如日本;完全公營和完全私營并存形式,如法國、英國、美國;混合所有制形式,即公私合營公私,如臺灣、意大利等。
(5)從使用費看,各國都有明確的使用費收取辦法。使用費既是使用權、經營權的體現,也是政府對鐵路屬性政策的調整、以及進一步分配或轉移規劃投資風險的渠道。例如法國、德國制定的基礎設施使用費機制,旨在從運營商方面收回約60%的基礎設施總成本,其余部分由政府資金承擔。意大利、瑞典基礎設施總使用費收入預計支付約18%的總財務成本。
[1]錢立新.世界高速鐵路技術[M].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2003.
[2]魏艷紅.世界高速鐵路發展趨勢[J].鐵道經濟研究,2005,(12).
[3]郭大為.國外高速鐵路建設與運營組織模式[J].鐵道運輸與經濟,2004,(8).
[4]吳昊.境外高速鐵路建設與運營組織模式[J].鐵道經濟研究,2003,(7).
[5]劉霞.我國鐵路行業外部資本進入壁壘研究[D].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
[6]胡濤.高速鐵路運營商組織模式、成本效益研究[D].北京交通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