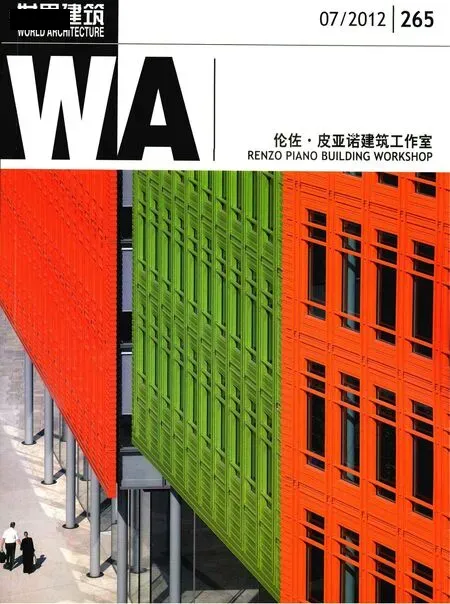我的建筑觀
倫佐·皮亞諾/Renzo Piano
孫晨光 譯/Translated by SUN Chenguang

本文是《倫佐·皮亞諾作品集》(Renzo Piano Logbook)的前言,是反映他本人對自己作品思想的集中論述。
古老的職業
建筑是一個充滿冒險的職業,建筑師總是處于“邊界”的一群人,游走于刀鋒之上。藝術與科學、創新與記憶、現代與傳統,這些分庭抗禮的元素都使得建筑師不得不與危險常伴。他們的工作中充滿了各種“材料”,我說的不只是混凝土、木頭、金屬,建筑師要每天打交道的還包括歷史、地理、數學以及自然科學、人類學、生態學、美學、技術、氣候條件與社會環境。
建筑師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因為無論地球已經被開發到怎樣的程度,“設計”仍然可能是一場場充滿未知的探險。隨著我們祖先對現實世界的探索,我們能探索的空間所剩無幾。哥倫布、麥哲倫、庫克、阿蒙森這些人已經發現了一切,留給我們的只是思維領域的冒險。而這些冒險所能帶來的焦慮、刺激和緊張感絲毫不亞于一場雪域遠征。
從某種程度上,每一次設計都是一場旅程:啟程、尋覓、發現。一旦膽怯,開始在那些溫暖怡人的巢穴里尋求庇護,滿足于那些已經被看見、被實踐的事物,那么,這就不再是一段旅程。然而,如果你敢于冒險,不逃避而選擇勇往直前,每一個項目都將是一個新的起點,都將打開一片未曾開拓的王土,你便是新時代的魯濱遜。
建筑是一個古老的行當——如同狩獵、捕魚、耕種和探險。與這些人類原始的活動相比,其他行當都顯得微不足道。尋找食物的訴求很快轉移到尋找住所,而隨著人類不能再滿足于自然創造的庇護,“建筑”便應運而生了。
那些建造房屋的人,為他們自己,也為他們的家族與人民提供蔭蔽。房屋的功能不僅僅局限在提供保護上,經過一代代手把手的傳承,房屋的基本功能向著美學方向發展,從一開始房屋就承載著人們對于美、尊嚴以及身份的訴求。人們用房屋表達自己對于歸屬感和標志性的渴望。
建造的過程不是僅限于技術層面的行為,它有自己的符號化意義。這種特點正是建筑專業區別于其他領域的重要特征。任何妄圖消解這一特性的做法都不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正確路徑——恰恰反是你即將繳械投降的預兆。
危機的職業
我曾經時常談及自己對于建筑專業正走向死亡的擔憂。和點街燈的燈夫或者礦工類似,建筑師的工作面臨消亡的危險。這也許是某種過慮:建筑業在今天較之以往更加必要。但建筑師能力的不足、缺乏責任感、盲目自大以及對于手工藝的蔑視,卻都在漸漸摧毀與瓦解我們的事業。我相信,這一職業正亟需一種全新的尊嚴,為此我們必須探索建筑的本質。
首先,建筑師是誰?建筑是一種服務:每當我們被潮流、形式、趨勢所蠱惑的時候,這便是我們需要時刻銘記于心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教條。這并不是什么格言,而更可能是一種謙遜:一種正確看待事物的方式。
第二,建筑師是了解如何為人建造房屋的人。他們知道該用哪種材料和結構,他們研究風向和潮汐,他們控制生產過程以及所需工具——換句話說,他們知道房屋、橋梁以及城市為何和應該怎樣被建造。
自大和放縱給這一職業帶來了危機。一些建筑師認為自己并不該承擔社會責任,這是一種常見的誤區,也恰恰成為了那些形式主義或高技派的借口。這些人對自己工匠的身份視而不見,而以藝術家自居——然后迅速地投身學院派。我并不只是在泛泛而談,建筑師游走于技術與藝術的刀鋒之上,而我認為,它就是應該立足于這樣的刃口。一旦你認同了將其分割開來,那結果必將是不幸墜落——無論是哪一邊。
當建筑只被當作技術——機械,組織運營,財力——它就喪失了所有的表現力、社會意義以及與生活的關聯。我們的城市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建筑又離不開技術。很多人堅持認為,技術應該服務于藝術,成為藝術的實現工具——這被許多人視為真理,而所有真理都會衍生出異端——相反的觀點認為,藝術本身就是技術。我個人不同意這兩者中的任何一種,但我更傾向于后者。我愿意把建筑比作一個人,他用技術創造情感,具體來說是藝術化的情感。當你聆聽偉大音樂家的作品時(我想到的是鋼琴家毛利齊奧·波里尼,或小提琴演奏家薩爾瓦托雷·阿卡多),你會發現,他們的技巧已經深入骨髓而轉化為藝術。“學習有關于音樂和你的樂器的所有知識,然后把它們統統忘掉并隨心所欲地演奏。”這句貌似出自查理·帕克之口的話,我認為對于建筑領域也同樣適用。
建筑的歷險
創造意味著在黑暗里沖鋒陷陣——要有韌性、堅持甚至是偏執,總會有一些懸念和等待惹人焦慮——而一旦你不接受這些挑戰,你將別無選擇地墨守成規、止步不前,學院派就是這么產生的。當你對一些看法堅定不移的時候,它們反而并不能成為你去思考的根基,反而成為惰于思考的借口,成為逃避恐懼的庇護。探險包含著錯誤的可能性,風險一直存在。你當然也可以選擇安全舒適的高速路,但這不是探索者應當做的。
當你進入一個漆黑的房間,你的眼睛需要一定時間適應黑暗——這是身體的特性。思想同樣需要時間適應,而這恰恰是創造的開端。設計的全部歷程都點綴著令人激動的瞬間,但是真正的創造性的時刻——如果它的確存在——只能在你的記憶里重構。當過了6個月或一年的時間,你再回首時才會體會到:那一天才是至關重要的轉折點。你會奇怪,為什么我不曾聽到鑼鼓喧天,甚至沒有過鼓瑟鳴琴?在現實之中,一個點子并不是毫無來由的神來之筆,更不會有繆思女神跟你悄悄訴說。它應當是你努力調查和試驗的結果,也就是伽利略所說的“不懈地嘗試”。點子是從過程中自然生發出來的,以至于當它出現的時候我們也許都沒有察覺。
這些想法幫助我從“創造”的神話中跳脫出來。藝術家并不是天資過人之輩,他們只是掌舵人,并且不懈地向著目的地前進——那就是藝術。
建筑師的職責
建筑是一門危險的藝術,因為它是強加于人的。你可以不去讀一本劣質的書籍,也沒有必要去聽一首糟糕的曲子,但是當一幢丑陋的公寓出現在你面前時你別無選擇,不得不去看它,它會讓使用者完全沉浸在其丑陋帶來的痛苦中。建筑是一個關系到未來世世代代的重大責任。這不僅僅是我的個人觀點,也能夠幫助我們拓寬反思的范圍。
那究竟什么是建筑師的職責呢?聶魯達說:如果一個人是詩人,那他或她會把想表達的東西寫進詩歌里,建筑師也是如此。作為建筑師,我不鼓吹說教倫理道德——而是把它設計和建造在我的作品里,試圖保持這個職業的博大精深和建筑作為服務事業的純粹性。
即便如此,建筑師的職業仍然有可能變得很危險,他們的烏托邦和別人想象中的烏托邦不一樣,是注定要成為現實的。因為是建筑師想象中的世界構成了這個最終的世界,所以他們可以將自己視為造物主,堅信自己被委以創造未來世界的重任。更謙虛地說,他們加快了世界建造的進程。
我相信我們的工作永遠是未完成的事業,因為這是人類關系中(當然也是城市)的本質,是一個永恒演化的過程。當建筑師開始建造某種建筑,它的未來當然是不可知的,這也是為什么出發點必須腳踏實地的理由——因為建筑本身就矗立在這里,宣揚和維護著建筑師的價值觀和道德觀。
實干文化
我生于建造者之家,我的祖父、父親、兄弟都是承包商,但是我卻選擇成為一名建筑師。我父親把這個消息看作家族進化過程中的小故障:對他而言,一個沒有念過大學的建造者的兒子們應該成為一個有學歷的工程師。因此,我的這個選擇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我很多后來的與眾不同之處。
有人曾說,我們了解的一切事情都是孩提時期得到的,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花費一生的時光去挖掘童年的記憶。因此,建造者這個家族歷代從事的職業對我也有很深的影響,就好像在馬戲團中成長起來的人一定生來就是一個雜技演員一樣。我的身體里從小就流著建造者的血,它賦予了我對建造的熱情,實干文化已經在我的工作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記。
從風格出發對年輕的建筑師來說是一個誘惑,但我卻選擇從實干開始:從建筑的選址,到研究建筑材料,再到建造施工的方法、傳統等等知識。我的建筑生涯從技術開始,再逐漸去了解建筑復雜的一面:空間、感染力和形式。從1964到1968年,在我剛畢業的時候(我稱之為我的史前時代),是我玩耍實驗的階段,這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階段,盡管在此期間我沒有建造出經典的建筑,但正是這接二連三的嘗試才讓我避免日后淪為形式主義的建筑師。
我還記得同父親第一次去建筑工地的經歷,那里對一個8歲左右的小男孩來說真是充滿奇跡的地方:頭一天你還只能看見一堆沙子和磚塊,第二天就發現一堵墻屹立在面前,隨后逐漸變成一棟可以給人們提供庇護的高大堅固的大樓。
在我的記憶中,對于父親還有另外的回憶,我和這個寡言的男人關系一向很牢固。在他80歲后,有一次我帶著他去我自己的施工現場,當時我們正在建造拉膜結構并且對其進行測試,他只是在一旁靜靜地抽著煙,看著我們。在回家的路上我問他覺得這一切怎么樣,他悶聲“嗯”了一下,好像他后面又說了句“誰知道它能不能保持得住”,總之很顯然他在仔細地思考著。
建筑工地的魔法
我對建筑工地依舊充滿了熱愛,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處在變化之中,風景每天都會不一樣,這實在是太奇妙了!這里上演著一場偉大的冒險,一場因為可以參與其中而讓我充滿自豪的冒險。建筑工地也總是充滿不同尋常的發現,因為并非所有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只有在現場你才能明白各種利害關系,才能決定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雖然那些在圖紙上看起來并無關緊要。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建造是一個永遠不會完成的過程,建筑和城市是永無止境的工廠。我們必須十分謹慎才能避免陷入完美主義的怪圈:因為每一件建筑作品都是隨著用途而不斷變化的生物,我們住在這些我們自己設計建造出來的生物體內,同它們連著的是充滿無盡冒險旅程的臍帶。
建造從來是未完成的,需要無休止的修建,這讓我更加相信建筑學是一門被污染的藝術,被人生中一切丑陋的東西所污染:金錢、權利以及所有草率的復雜的事物。但與此同時,它也會被附著美麗向上的光輝:事物的根源、創新、自然和人們的需要。
無論美丑,這些限制都是我們的職業強加給我們的。不過我更寧愿用“禮物”來形容這些所謂的“欺騙”,因為不論這些是污垢,限制或者職責,并不會成為我們的障礙,相反的,這些“禮物”讓建筑更加豐富多彩,它帶領我們領略傳統地域、科技、人類的歷史、品味和期望,應對這一切所帶來的影響。
好奇和倔強
海是地球的另一面,不為人知的另一面。我的好奇心總是來自于海邊漫步的時候,我是一個富有好奇心、不聽話的孩子。我不知道這是為什么,但上述兩者總是同時存在。事實上,我在學校時被認為是一個反面教材。
我認為,把反抗和獨立思想聯系起來是正確的。然而在我身上,是后者源于前者。它開始是一個非自愿的性格特質,隨后它轉變成了學者的態度,自然而然地在我的工作中反映出來。
例如蓬皮杜中心,是一種對城市的反思,代表了一種不甘于固步自封于一個被沉重的記憶壓迫的城市中的態度。但這種規模的對象,它的尺寸和外觀令人不安,擾亂了巴黎市中心(創造了一種有點類似于游船通過威尼斯的Giudecca運河的效果),這當然是對最保守的學院派的一種諷刺,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獲得一個近700個參與者的國際比賽的勝利后。這是蓬皮杜中心的一個缺點(或優點),在我作為建筑師的職業生涯中是一個很大的異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是一個棄兒,被協會、學校、學院列入了黑名單。作為一個真正的游手好閑的人,這種排擠始終是滿意的來源。在某種程度上,我現在已經被送往建筑的“神殿”,也許我之前更喜歡它。
我總是記得關于讓·普魯韋(Jean Prouve)的故事。他毫無疑問是勒·柯布西耶最后的繼承人和法國偉大的建筑師,但他完全處于學校之外的世界:他甚至沒有學位。有一天,我和一些朋友決定是時候去幫助他得到榮譽學位。在我們對他提出這個想法時,讓猶豫了很久,然后在某一天晚上答復我說:“倫佐,我很感激你,很感激你們,你們對我非常好,但我并不想要什么學位,就讓我無知地死去吧。”他想要以局外人的身份結束他的生命,就像他一直以來一樣。
熱那亞
有一些特定的片段和畫面一直縈繞在我的腦海里,它們被我稱之為“來自過去的明信片”。其中一些將我和我的家鄉熱那亞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對來自阿斯蒂(Asti)的 保羅·康提(Paolo Conte)來說,熱那亞是“一束灑在擋風玻璃上的光”,那里的海甚至晚上都在流動著,永遠不會靜止下來。對我來說,那束光和那片海,是這個港口的全部。
宏偉的和短暫的元素共同造就了這個港口美麗的風景:水中的倒影、懸在空中的載貨機,運轉的起重機、還有進進出出的船只,所有的一切都在不斷地變化。沒有人知道這些船只從哪里來又要到哪里去。很多年以前藝術評論家喬瓦尼·卡蘭登特(Giovanni Carandente)和我說蓬皮杜中心某種意義上說是一個給熱那亞的禮物。雖然我之前從來沒有這么認為過,但或許這就是真的。
另一張明信片來自于熱那亞那的歷史上的中心。佩利(Pegli),在我的記憶里,所有的一切都充滿著孩子夸張的想像力。媽媽經常會帶我去熱那亞,去那個古老而深沉的地方是很奇妙的際遇,那里正對著港口,聞上去像是鷹嘴豆的味道,充滿了母性的力量。
我對熱那亞總是又愛又恨,不論是在離開還是回去的時候。蒙塔萊(Montale)曾說:“去了解這土地到底留下了多深刻的印記是件好奇的事情。” 也許對我來說居住在巴黎或者倫敦更符合邏輯,但是我寧愿回到這里來,無論什么時候。
創作的環境
作為一名建筑師,我相信場所可以影響人的看法、情緒和活動。所以我曾問過自己工作的地方應該是什么樣子,應該有哪些特色。創造本來就已經很難,把自己放在合適的地方去創作會更難。這個地方需要安靜平和,也需要緊張敏感;需要冷靜又需要激情;需要時間但卻又要速度。正如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說過,創造者就像在記憶和遺忘之間的鋼絲上行走,我想我正是需要一個這樣的地方。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實驗室和工作室都建在熱那亞西海岸,棲息于巖石之上,被海水環繞著,像巖石又像船舶。這個地方叫做蓬殿(Punta Nave)。在這里,我找到了我工作中需要的一切要素——冷靜、安寧和專注。
我并不想給大家造成錯誤的印象,這個辦公室絲毫沒有避世的意思,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在這里工作,他們與外面的世界隨時進行溝通。我們的工作室在這里,同時也在大阪、努美阿和悉尼。人類一直希望能在同一時間身處不同的地方,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今天實現了這個目標,只不過這并不是指人的身體,而是通過技術的方式實現——那就是如今大家耳熟能詳的信息世界。
科技提供了我們同世界的聯系:這是一個先輩無緣體驗的方式,對我來說是極大的便利。電話、傳真、調制解調器和互聯網讓我居住在海邊,卻像身處社會的大鍋湯里一樣,技術將我們共同的心智連成網絡。正因為通信技術將這一切能變為可能,我才在這里修建了這個工作室,并且定居下來。
選擇在蓬殿工作當然和兒時的記憶有很大關系,但也有另外的原因:我愛這個地方,是因為它能提供出一個傳統工藝與現代科技、膽量與耐心、毅力與沉思、團隊合作和隱私之間完美結合的會議室。
與此同時,我也愛巴黎,愛我在馬雷(Marais)的工作室。我喜歡在星期天的清晨漫步其中:那是一個你四處逛逛就能遇見熟人,一個你能跟面包師傅和書店老板打招呼的地方。社交生活、會議、市井買賣,這一切都是必需的,就好像有些時候你需要的是一個避難所。因此,巴黎本身就是巨大的信息平臺,是一個高度社交性的地方,有時候甚至社交過度。而蓬殿則是沉思和孤寂的地方。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兩者缺一不可。
建筑是一場耐心的游戲
有兩種辦法來使用你的天賦:細水長流或者兇猛著力。而我則一直嘗試前者的方式。這并不是要訂一個計劃,也不是我的原則和宣言,而只是因為這種方式更加適合我。
建筑是一場需要耐心的游戲。我們的工作從來不會飛速開始。沒有人會說“就是這樣,這樣就會成功”。所有的觀點都要像酒一樣沉淀下來,只有這樣你才能真的發現好的想法。讓想法都沉淀下來意味著我們需要團隊合作,這樣才能讓最好的想法得以嶄露,不論這個想法是誰提出來的。
關于團隊合作有非常多的說法,但是如果這是一個一步一步發展的流水線:一個人把他做好的東西傳遞給下一個人,下一個人繼續去深入,不過自由度稍微小了一點。整個過程在不停地發展,但每一步的束縛都會變得更大,這就不是我所說的團隊合作。
團隊合作應該是當你拋出一個想法,別人就會回拋給你,就像在打乒乓球。4個人可以玩,6個人8個人也可以玩,伴隨著很多球不停地來來回回。所有的想法都混雜在一起,當最后的項目逐漸形成的時候,已經沒人能分得清哪些是誰做的了。
不斷嘗試
設計并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你有了想法,寫在紙上,執行它,然后就成功了。相反,它是一個循環的過程:你有了想法,嘗試它,重新考慮,返工,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原點。
在科學實驗中,你必須處理包含太多變量的方程。而在大自然中,變量幾乎是無限的。所以,你得用來源于直覺的經驗解決問題。如此一來,解出方程就有了可能。然后你測試所發現的結果,如果它是錯的,就需要重新開始,找到另一種假設,重復之前所做的,周而復始直到成功。在這個過程中,你縮小了范圍,像一只接近獵物的鷹。記住這個循環,這不只是一種方法,還甚至簡化了過程。夸張地說,這是一個學術理論。一遍又一遍的嘗試不僅是一種糾正錯誤的手段更是一種深入理解項目、材料、光線或者聲音的辦法,
實驗
在古代,設計的過程包括發明能夠使設計成為現實的工具。安東尼奧·馬內蒂(Antonio Manetti)講述了伯魯乃列斯基如何研究時鐘的機械原理以至后來成功運用到平衡系統中來的故事。這個系統后來被修建佛羅倫薩大教堂圓屋頂時提起它的橫梁時所用。這套方法和結果都是一次實驗的產物。
試驗的過程并非執行其他人已經直接寫下來的東西,那只是一種翻譯和表演,試驗是創造的一部分。當你在一個不斷往復的模式中工作的時候,技術就又回到了中心的地位,找回了本來的尊嚴。試驗讓想法和它的物質的結果聯系在一起。在我們設計德克薩斯的梅尼爾美術館項目時,發明了一樣被我們稱之為太陽機的裝置,它讓我們能夠在熱那亞就算出休斯頓太陽的位置。我們還制造了一個1:10的模型,把它放在花園里我們就能研究光的漫射。所有來自于這個工作室的項目都有相似的實驗過程。
知道如何做事不僅僅要靠腦袋,也要靠雙手。這也許看上去是一個假大空的目標,但其實不然。這是一種安全的尋求自由的方式。當你想要將一種材料、一種建造技術或是建筑上的元素用在特殊方面的時候,你總會自己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僅僅是因為之前沒有人嘗試過。但當你真正去嘗試并堅持下去之后就會發現自己獲得了別的方式無法企及的設計上的自由。
在我們修建蓬皮杜中心的時候,我們要創造一種非鑄造的金屬結構。當時整個法國的鋼鐵工業都公開反對,他們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們那樣的結構是不可能使房屋站立起來的。但我們卻深信不疑,彼得·萊斯(Peter Rice)首當其沖,就將訂單給了德國Krupp公司。因此蓬皮杜中心的主體結構都是在德國制造的,即便那些大梁都是在晚上秘密運送的。這是科技如何協助藝術的實例,我們對結構的理解解放了我們的表現能力。
30余年的工作
從我作品的變化中能看到一種發展:從個人制作和早期的結構到后來完整的建筑創作,從自說自話的建筑到適應場地文脈的建筑,從獨立建筑到一個城市建筑。
如果說冒險是我創作的一個特點,那另外一個特點就是頑強和倔強(Obstinacy and tenacity)。頑強和倔強是非常重要的品質,無論是在哪種行業或是哪個文化,這并不是一種自大的態度,而更多的是一種對于思想的誠實。我認為,建筑師的道德就是忠于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方法。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把這種道德意識轉化為一種方法論:如何在不固執己見、冥頑不化的條件下堅持自我。其實就如同我們使用自己的才干應該細水長流一樣,這種方法也應該是跬步千里的。
可持續建筑
建筑是建造在真實的自然環境上的“第二自然”。說到自然環境,從事我們建筑行業的人應該特別注意這點。我們生活在像房子這樣的庇護場所中,是因為絕大多數的人生活在這個一年里很多時候要么太冷要么太熱的星球上。照這樣看來,自然在某種程度上是殘酷不仁的:而建筑師就是它的對手。建筑師改造了自然使人類更舒適愉快地居住。如果“敬畏自然”意味著穿著拖鞋踩在草地上,那就興味索然了。
討論可持續建筑是完全必要的:它意味著認識自然,尊重動物和植物,合理地營建建筑和工廠,利用太陽能和風力。這正是我們如今在亞太地區努力去實現的兩個項目——新喀里多尼亞的吉巴烏文化中心和悉尼的混合功能大樓:建立一種能允許一定程度的人工與自然之間的緊密聯系(人工與自然的一種張力)的智能關系。
我發現一些對先進科技的質疑非常可笑,特別是這種懷疑在一些褒揚或貶損高科技的激烈學術論調中此起彼伏時。建筑師總是使用他們所在的時代所提供的工具來工作。即使是在15世紀,伯魯乃列斯基也是使用著他能使用的當時最先進的技術,來設計和建造坐落在佛羅倫薩的圣母百花大教堂。拒絕接受當代的物質文化是完全徒勞的,甚至是自虐的。我們來打一個這樣的比方:科技就像是一輛公交車,如果它能載你去想去的地方你就上車,如果它開往其他方向你不上車便是。就像在CD播放機上或是在手搖留聲機上來聽同一支曲子,對于曲子的意境完全沒有影響。
事實上,科技進步帶給我們的好處之一是提供了新的方式來利用傳統的材料。例如,在教士朝圣教堂中,多虧現代的計算機技術,我們用石頭實現了一個極度困難的結構。這個結果表明:科技的確被使用了,但它用在了“刀柄”上,并不喧賓奪主。科技的運用成為了建筑的一部分而不是取代建筑本身,這與跟某些具體領域的高科技完全相反。此外,根據我自身的親歷體會,梅尼爾美術館所使用的營建和服務的技術遠比蓬皮杜現代藝術博物館的更復雜,以至于是無形的。
局域性和普遍性
建筑是一個地域概念:它在詞源意義上是有地域性的,即它與地區相關,與當地的地形地貌相關。但是,建筑所包含的審美價值及其發展的住房模式是沒有地域限制的,是跨越國界為各國所共享的。建筑的全球化是一個由來已久的愿望。但與之相悖的是,建筑所傳達的“信息”的全球化依賴于語言的接受能力。建筑“應時而生”,并且必須能表現一個時代。因此,建筑必須運用所有可行的方法,站在我們正在生活的時代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語言的全球化不完全依賴于通信的速度,但它顯然受其影響。新科技讓民族與文化的交流前所未有的方便。而我相信,這種全球化的可能是積極的。
日本關西機場航站樓應一個日本客戶的需求而建成。但是該項目的CAD設計通過調制解調器中途走遍世界,工作的圖片也已被許多國家的電視頻道播出。某些部分在英國、法國或意大利,并通過海運或空運至日本。假如我在神戶工作,而美國可以提供一種特殊的焊接技術,那么我為何不使用它呢?
相反地,有一些在新喀里多尼亞或悉尼的人必須在世界的另一邊建造一個建筑,而剛巧他們的建筑師在熱那亞高地的蓬殿,這沒有問題:他們有電話,傳真機,調制解調器,網絡,如果必要的話幾個小時的飛機就能會面。這就是我們早先所說的“科技無處不在”,它顯示了當代生活質量的飛躍。
爭議性和復雜性
總之,我們不應該被我們專業目前所面臨的爭議嚇倒。一定程度的復雜性是不可避免的,過度簡化才是荒唐的。作為一個從業30年的建筑師,我越來越確信:一種不可調和的過去與現在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借鑒與原創之間的沖突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事實就是這樣。這些看似對立的概念其實并不矛盾。它們像是鹽對于生命的重要性一樣,是建筑的精髓。建筑師的工作是將這些矛盾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而不是把它們割裂。
我的建筑觀
即使我說的是一種方法——盡管平時經常被忽視,它仍可以適用于建筑學。通信技術的發展已經改變了我們對距離的感知,以至于在實際情況里熱那亞同紐約的距離已經不像100年前那樣遙遠。空間“收縮”了,并且以一種截然不同的方式呈現。我得重申:我在尋找一種現代的而不是傳統的方式來連結空間。
與此同時,局域性與普遍性的關系其實并不僅僅是一個邏輯問題:它同時關乎文化、審美和符號象征。肯尼斯·弗蘭姆普頓最近提出一種看待這個問題的新觀點,他在為這本書所寫的簡介中也有提到:他指出,建筑的張力是由場所形式和建筑形態二者共同創造出來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用以解釋地面與構造、環境與建筑、地域性與普遍性的相互關系。所有的問題都集中在這種相互關系,相互聯系,相互間的張力上。我最感興趣的課題是組合塑造好形式與產品:強有力地塑造土地,在原有環境或城市構造上留有深刻的印記;但同時使得建筑物成為一種襯托,與周圍的環境特點相得益彰。
我最新的作品都闡釋了一種存在于基體與建筑物之間強烈緊密的聯系。這些建筑所在的基體通常是原地取材建成,就像是浮雕一樣。這意味著每一個項目都會有當地的成分:事實上巴里的體育館和紐約的建筑物都是這樣,悉尼的建筑也將會如此。
再來解釋場所形式(Placeform)這個詞,每個項目都需要針對性的研究,需要對其歷史、地理、地質和氣候進行深入地了解。有時候這些因素的影響是相互的。在對羅馬大會堂的發掘過程中,我們發現一個公元前6世紀的別墅的地基。對于它,“topos”(topos一詞是拉丁語里“年齡”的派生詞)不僅僅是一種修辭,它是真實存在的。這個建筑的地基,就像河床一樣,散發出一種巖石般的歸屬感——它厚重、實在、不可磨滅。在這個羅馬詞語里有種永恒的東西。而相反的,那些構造,量輕,清透,而且轉瞬即逝——不是因為它會被拆除,而是因為它屬于另外一個層次,有不同的價值。
空間
我對于透明空間的堅持經常讓人誤解,并且讓建筑的空間變得不明確,在我們專業的判斷里,這是一種沒有空間感的表現。
創作透明空間的理由由來已久,“輕盈”(Lightness)這個概念一被提出來,就在和建筑最本質的概念矛盾著:我們潛意識里建筑應該是一個堅實的堡壘,我們本能地在尋找封閉和固定的空間。空間的概念一直在干擾我的創作,這讓我覺得像是在磚頭三明治里面塞東西一樣:一層墻壁圍繞的空氣。我覺得建筑空間不應該那么讓人窒息,建筑空間應該是一個小宇宙,是一個室內景觀,這沒什么不一樣的。
空間中非物質的元素
空間是由體積構成:大和小的體積,壓縮和擴張,平靜和緊張,水平面和斜面。它們是有意挑起情緒的所有元素,但它們不是唯一的。我相信和空間中的非物質元素一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對這項研究也非常迷戀。我覺得這是在我的建筑中主要的趨勢之一。
哥特式教堂那升入天空的空間感動了我們,它們讓罪人的靈魂升華。它那纖長的窗口,通過五彩的玻璃過濾、折射,將太陽的光芒射入陰暗的教堂,同樣激起我們心靈的顫動。我們需要創造戲劇性的空間、寧靜的空間、參與性的空間、幽靜的空間,去讓我們的職業回歸到激發人類情感的功能上。如果你正在設計一個博物館,你需要提供沉思的空間。僅僅讓光線完美是不夠的,你也需要和思索藝術作品相關的冷靜、沉著、甚至妖嬈的空間。
如果你正在建設一個音樂廳,僅僅提供完美的音響效果是不夠的:你必須鼓勵觀眾參與音樂。這就是為什么,在演唱會上,你欣賞一首交響樂,和在家里聽一個完美的音響系統播放的音樂相比,你不會覺得被冷落,因為你參與其中,和在指揮臺上的指揮,120多名樂團成員,還有其他數百、甚至數萬余在同一時刻經歷同樣的情感的人。
另一方面,蓋房子的目標是要有保護感,舒適感。你必須為它的居住者創造親近和隱私的感覺,但不隔絕外面的世界。
輕盈和透明
非物質的元素,比如輕盈感、透明、振動、質地、顏色等元素與空間相交互(在某些情況下,它們是空間組成的結果)。為了最充分利用非物質元素,我從一個天真的、甚至相當原始的方式展開工作。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大量的材料去建立,如果你做一個1m厚的墻壁,它當然會站得住。但從事物中做減法可以讓結構得以更加清晰的表達,用靈活取代死板。
有一次,我去巴黎觀看讓·普魯韋教學。他給學生一張紙,一張卡片,和一把剪刀。他說:“用這張紙,做一座橋,從這里到這里。”這個距離長于板材,所以必須要創造一種新的方法。有的學生裁切紙張,有的折疊,有的扭曲。這是一個發現結構美的方式。理論是不夠的,繪圖與它也沒有什么關系。你必須使用你的手來把握的原則,像人們一直做的那樣。
減少必要的結構意味著要通過減法工作,并打破傳統。做減法是一個挑戰、一個游戲。當完成刪減的時候,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正必要的。也許這就是為什么人們已經開始在音樂,文學,繪畫等別的領域接受了同樣的挑戰。
光
自然光一直是我研究的一部分內容。從我在熱那亞的第一個工作室到現在位于蓬殿的工作室,在做某些項目,例如IBM移動展亭和一些博物館項目時,我一直很重視光對周圍環境的影響,例如其與室內空間大小以及人的情感反應的關系。在梅尼爾美術館中,光被有意識地用于淡化空間背景,使得人們能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藝術陳列品上。在教士朝圣(Padre Pio)教堂里,我們從另一個角度試圖利用光的其他作用:通過直接把光打到圣壇上,來使得其間接擴散并照亮整個教堂。
為了利用光的潛力,我們設計了多個連續的垂直平面空間安置在梅尼爾美術館,這不是一個巨大的建筑,但它產生出一種無窮感。其原因在于疊加讓連續的平面產生了延伸視野空間的深度。類似做法也被用在關西機場航站樓中通向飛機的畫廊,你看不到結束的部分,部分原因是因為尺寸實在是大得令人難以置信,但也因為角度被扭曲:這個巨大的空間中間部分有20m高,但后面只有6m。
自然
我對自然材料和自然形狀的使用時常給人帶來一種誤解,即很多人相信我在我的作品中試圖模仿自然,但這不是我設計的初衷。自然是很美好的,對自然細致入微的觀察可以教會我們許多,可是模仿是非常天真和滑稽的。從我的作品中,至多可以識別出一些平常的、源于對于物理和機械的應用中的元素。
建筑的屋頂可能看起來像個殼,因為貝殼是一個非常精美的結構,是幾百萬年以來進化的成果,但是這個屋頂卻并不如此。教堂是教堂,貝殼是貝殼。如果二者間存在相似,我會稱其為暗指而不是模仿。
你可能會發現一些時常在音樂中找尋到的東西。你知道你發現了什么,但你并不知道這是什么。在這里,我們又一次在我作品的核心里發現了結構、空間和感覺之間的關聯。
風格
有人曾說我的工作室設計出來的作品很容易被識別。但是實際上我的作品其實并沒有統一的形式,因為并沒有一種永恒的整合設計的方法。當風格被刻意調整成一種標志,它也就成了設計師固步自封的牢籠。為了讓你的作品容易被認出來而對它做的任何刻意設計,都會把設計師自由發展的能力給扼殺掉。對作品的認可只會來源于你對挑戰的接受,而只有通過合理的設計方式,才能使其被識別出來。
或許我的風格存在于我對建筑的詮釋之中:我對于需求和期待,總是用截然相反的方式去回應,這便是我面臨的挑戰。赫拉克利特曾經說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萬物生于我們的指間,并隨其改變。經驗和記憶給我們帶來的便利并不是指可以將舊法用于新設計。
我想可能秘密就在于不要把你的夢想藏在腦海中,它們需要被實現、被挑戰。我不喜歡聽到人們說:我有一個很好的想法,但是客戶不想了解,所以這個想法只能是個想法。如果你對于一個設計的價值非常自信,你遲早會把它變成現實,因為你有再次提出、發展、改造它的耐心。當你完成的時候,你會繼續前進,提出一個新的想法,然后你的探險會一直持續下去。□(感謝喬周庶、唐濤、孫成偉、李格雷、王昊的校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