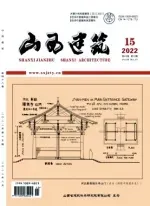城市邊緣區(qū)工業(yè)前景分析
羅詩(shī)丹 劉 琨
(四川大學(xué)建筑與環(huán)境學(xué)院,四川成都 610064)
1 概述
在城市化進(jìn)程加速擴(kuò)展的今天,那些位于城市邊緣地區(qū)卻又不在城市范圍內(nèi)的工業(yè)園區(qū)處在了一個(gè)非常微妙的位置。對(duì)于那些已經(jīng)被包含或是即將被包含在城市中的工業(yè)園區(qū)來(lái)說(shuō),未來(lái)的發(fā)展勢(shì)必會(huì)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如何把握好工業(yè)園區(qū)在城市中的地位以及其未來(lái)的發(fā)展方向,本文將做一個(gè)簡(jiǎn)單的分析。
2 城市邊緣區(qū)的定義
城市邊緣區(qū)作為城市與鄉(xiāng)村腹地之間一個(gè)連續(xù)的過(guò)渡帶,自然而然也充當(dāng)著承載城市由內(nèi)向外逐漸衰減的經(jīng)濟(jì)壓力的特殊區(qū)域。1975年,洛斯烏姆在《城市邊緣區(qū)和城市影響區(qū)》一文中描述了現(xiàn)代城市社會(huì)空間結(jié)構(gòu),明確的將城市核心區(qū)與城市最大通勤區(qū)之間的邊緣區(qū)分為兩個(gè)部分:內(nèi)緣區(qū)和外緣區(qū)。城市邊緣區(qū)同時(shí)也被認(rèn)同與城鄉(xiāng)邊緣帶這一概念相同。城鄉(xiāng)邊緣帶的基本概念是“位于中心城區(qū)連續(xù)建成區(qū)與外圍幾乎無(wú)城市居民住宅及非農(nóng)業(yè)土地利用至純農(nóng)業(yè)腹地之間,兼具城市與鄉(xiāng)村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區(qū)但高于周圍鄉(xiāng)村地區(qū)的一種土地利用、社會(huì)和人口特征的過(guò)渡地帶”[1]。洛斯烏姆區(qū)域的城市結(jié)構(gòu)見圖1。

城市邊緣區(qū)作為城市與鄉(xiāng)村的過(guò)渡區(qū)域,它不僅擁有著城市內(nèi)部所特有的活力與繁華,而且還不受城市內(nèi)相關(guān)政策的管轄和制約。這樣一個(gè)在時(shí)空動(dòng)態(tài)與城市相近的區(qū)域,土地利用、生活和生產(chǎn)等方面也有著不同于城市與鄉(xiāng)村的特殊性。特別是中國(guó)城市在發(fā)展層次上呈現(xiàn)出一種在時(shí)空上離心推移的發(fā)展模式[2],使得城市邊緣區(qū)在城市快速發(fā)展進(jìn)程上更顯敏感。其低于城市內(nèi)部生活成本的優(yōu)勢(shì),使得這一區(qū)域成為了因?yàn)槌鞘谢ネ恋氐拇迕褚约盁o(wú)力承擔(dān)高昂租住費(fèi)用的外來(lái)務(wù)工人員的聚居地;同時(shí)這里依托于城市內(nèi)部的便捷交通也成為了以當(dāng)?shù)刈匀毁Y源或是特有產(chǎn)品為主的工業(yè)生產(chǎn)廠家的集中地。簡(jiǎn)而言之,城市邊緣區(qū)成為了各界眼中的“香饃饃”,受到了來(lái)自于開發(fā)商、政府機(jī)構(gòu)以及村民各方的爭(zhēng)搶。但長(zhǎng)期以來(lái),非統(tǒng)一規(guī)劃建設(shè)的工業(yè)園區(qū)、聚居點(diǎn)也都有了相應(yīng)的規(guī)模,但對(duì)于在工業(yè)生產(chǎn)中具有高污染、高能耗、低回報(bào)的廠家,他們同時(shí)也在承擔(dān)著生態(tài)和環(huán)境等方面暴露出的嚴(yán)重問題。
3 工業(yè)園區(qū)的特點(diǎn)
城市的快速發(fā)展對(duì)城市邊緣區(qū)的用地性質(zhì)及其產(chǎn)業(yè)模式的改變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有研究統(tǒng)計(jì)得出:在城市化后期,以工業(yè)發(fā)展為基礎(chǔ)的服務(wù)業(yè)發(fā)展迅速,新型服務(wù)業(yè)不斷崛起并在城市中占據(jù)重要地位。在一些處于城市化后期的國(guó)家,服務(wù)業(yè)比重一般在50%以上,工業(yè)比重將至30%以下,農(nóng)業(yè)比重將至10%以下,如美國(guó)1970年城市化水平為74%,處于城市化后期,農(nóng)業(yè)、工業(yè)和服務(wù)業(yè)的比重為 3.2 ∶34.4 ∶62.4[3]。工業(yè)是城市發(fā)展過(guò)程中處于重要經(jīng)濟(jì)地位的基礎(chǔ)產(chǎn)業(yè)。簡(jiǎn)而言之,工業(yè)化發(fā)展是中國(guó)城市化進(jìn)程中絕大部分城市所需要經(jīng)過(guò)的一個(gè)必然過(guò)程之一。
在大部分城市的邊緣地區(qū)內(nèi)各類工業(yè)用地、鄉(xiāng)鎮(zhèn)居住用地和基本耕地零星的混雜在一起。除了必要的交通聯(lián)系外,用地和基礎(chǔ)市政設(shè)施均沒有統(tǒng)一規(guī)劃、配備,簡(jiǎn)單說(shuō)來(lái)在城市邊緣區(qū)這樣敏感的用地范圍內(nèi)無(wú)系統(tǒng)的規(guī)劃體系。城市邊緣區(qū)范圍內(nèi)土地分散使用的情況依舊嚴(yán)重,這是我國(guó)長(zhǎng)期發(fā)展中遺留下來(lái)的歷史性問題,并非能在一朝一夕之間得到解決。其中的工業(yè)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建設(shè)不具有形成完整性和合理性的工業(yè)園區(qū)的需求。由此簡(jiǎn)單總結(jié)一下,當(dāng)前社會(huì)工業(yè)企業(yè)存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diǎn):
1)土地利用分散。正如前文所言,對(duì)居民的聚居點(diǎn)安置、農(nóng)業(yè)用地的統(tǒng)一規(guī)劃布局以及工業(yè)和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用地的合理配置都對(duì)土地的利用、整合有著重要的意義。城市邊緣區(qū)特有的城市土地與農(nóng)村土地交界的區(qū)位特點(diǎn)確定這一區(qū)域范圍中土地利用類型的復(fù)雜性及多樣性,城市土地利用類型和農(nóng)村土地利用類型相互共存、相互制約。城市建成區(qū)與邊緣區(qū)和鄉(xiāng)村中的集中聚居點(diǎn)呈現(xiàn)出相互吸引的構(gòu)造特點(diǎn)。而對(duì)于工業(yè)園區(qū)而言,首先聚居點(diǎn)所擁有的便捷交通成為了貨物運(yùn)輸和工人通勤的優(yōu)勢(shì),特別是擁有大量運(yùn)輸能力的航空港、火車站附近等。其次,無(wú)論對(duì)于傳統(tǒng)制造工藝所需多層車間或是現(xiàn)代流水線所需的單層車間,邊緣區(qū)內(nèi)工業(yè)用地的費(fèi)用無(wú)疑將遠(yuǎn)低于城市內(nèi)部的用地費(fèi)用[4]。因此具有以上特點(diǎn)的城市邊緣區(qū)成為了工業(yè)園區(qū)發(fā)展的首選地。
2)基礎(chǔ)設(shè)施及管理系統(tǒng)不完善。正是由于以上土地利用分散的緣故,基礎(chǔ)的給排水、電信、燃?xì)獾仁姓O(shè)施不完善,缺乏一個(gè)地區(qū)內(nèi)部應(yīng)有的完善、簡(jiǎn)潔的體系模式。企業(yè)分散布置是對(duì)基礎(chǔ)設(shè)施的浪費(fèi),一部分企業(yè)形成規(guī)模后依照自身需求改善了應(yīng)有的市政設(shè)施,然而這一部分企業(yè)現(xiàn)在所需的設(shè)施卻將在未來(lái)成為累贅的資源占去大面積的土地。倘若在土地利用集中的前提之下,相應(yīng)設(shè)施所需資產(chǎn)將更容易集中和最大效率的使用。同時(shí)也會(huì)減輕企業(yè)內(nèi)部資金壓力和日后維護(hù)、管理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促進(jìn)資源的統(tǒng)一調(diào)配,減少無(wú)效過(guò)程、審批等程序,提高辦事效率。
3)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單一化。當(dāng)?shù)毓I(yè)企業(yè)的設(shè)立往往依賴于當(dāng)?shù)氐淖匀毁Y源和特色產(chǎn)品,從而形成了粗放型的工業(yè)生產(chǎn)模式。該種生產(chǎn)模式使得一個(gè)地域范圍內(nèi)都會(huì)以同一種產(chǎn)品作為主導(dǎo)商品,單一化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使得整個(gè)工業(yè)內(nèi)部壓力增大。單一化的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必定存在缺陷,正如同自然界食物鏈形成不能夠由單一的動(dòng)物或植物構(gòu)成,平衡的破壞不利于發(fā)展。所以,從規(guī)劃的產(chǎn)業(yè)鏈結(jié)構(gòu)上進(jìn)行調(diào)整和豐富,能夠?qū)I(yè)園區(qū)內(nèi)的產(chǎn)業(yè)進(jìn)行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及配置。不僅能夠達(dá)到優(yōu)化利潤(rùn)的目的,同時(shí),完整的產(chǎn)業(yè)鏈將對(duì)環(huán)境造成的污染也越小。由資源浪費(fèi)和環(huán)境破壞嚴(yán)重的產(chǎn)業(yè)向資源集約型產(chǎn)業(yè)進(jìn)行轉(zhuǎn)變是一個(gè)必要的過(guò)程。
4 工業(yè)園區(qū)與城市發(fā)展時(shí)序的關(guān)系
德國(guó)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勒施說(shuō)過(guò),“如果每件事情同時(shí)發(fā)生,就不會(huì)有發(fā)展。如果每件事情存在同一個(gè)地方,就不會(huì)有特殊性,只有空間才能使特殊性有可能,然后在時(shí)間中展開”[5]。城市空間作為城市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的載體與容器,自然是存在有一定規(guī)律的發(fā)展時(shí)序。若在發(fā)展時(shí)序上發(fā)展相對(duì)均衡,就像是“攤大餅”一樣,只是一種用地的簡(jiǎn)單疊加,而缺少用地的改造和更新活動(dòng),達(dá)到了“量”的優(yōu)勢(shì)而非“質(zhì)”的領(lǐng)先。而工業(yè)園區(qū)作為一個(gè)有規(guī)模并有良好管理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載體,自然也應(yīng)該遵循這個(gè)道理。正如我們之前所言,目前工業(yè)園區(qū)所遭遇的問題是現(xiàn)在或即將融入城市發(fā)展的范圍之內(nèi)的情況。倘若保持現(xiàn)在的狀態(tài),工業(yè)園區(qū)勢(shì)必會(huì)給城市帶來(lái)諸如空氣質(zhì)量、水源、噪聲污染等問題。
依照現(xiàn)有的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總結(jié),工業(yè)園區(qū)的發(fā)展情況可以分為兩種情況:1)園區(qū)已經(jīng)融入城市并且和居住小區(qū)、商業(yè)貿(mào)易等公建服務(wù)設(shè)施緊鄰;2)園區(qū)即將融入城市范圍之內(nèi)。根據(jù)這兩種情況,我們可以采取不同的手段來(lái)解決。
4.1 尚未融入城市的工業(yè)園區(qū)
在對(duì)現(xiàn)有園區(qū)進(jìn)行設(shè)計(jì)規(guī)劃時(shí),就應(yīng)該考慮到園區(qū)作為城市的一部分時(shí)應(yīng)該擁有的一些必要元素。特別是針對(duì)那些建成時(shí)間較長(zhǎng),初級(jí)配套設(shè)施較差的園區(qū)更應(yīng)該從生態(tài)產(chǎn)業(yè)園區(qū)的方面進(jìn)行考慮規(guī)劃,如體量、環(huán)境、公共服務(wù)設(shè)施、產(chǎn)業(yè)鏈循環(huán)等。在進(jìn)一步對(duì)工業(yè)園區(qū)開發(fā)時(shí),應(yīng)將原本存在的問題進(jìn)行改造。例如高壓線走廊由于缺少規(guī)劃,使得整個(gè)區(qū)域內(nèi)部大量土地被高壓線走廊形成的“蜘蛛網(wǎng)”分割,最后導(dǎo)致區(qū)域內(nèi)土地利用率低下等土地利用上的問題。在遇到這種問題時(shí),我們應(yīng)該從實(shí)際出發(fā),對(duì)線路進(jìn)行整合,處理好管線走向,以達(dá)到節(jié)約土地和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目的。
4.2 已經(jīng)融入城市的工業(yè)園區(qū)
當(dāng)然,園區(qū)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滲透入城市的主體部分時(shí)應(yīng)對(duì)園區(qū)進(jìn)行改建。這里提到的改建手段主要有兩種方法:改和遷。
在“改”的方面上可以有多種手段進(jìn)行思量:1)改周圍的用地的性質(zhì)。可以對(duì)園區(qū)周圍的環(huán)境進(jìn)行改善如加大防護(hù)綠地、對(duì)園區(qū)內(nèi)產(chǎn)業(yè)的性質(zhì)和結(jié)構(gòu)進(jìn)行改造,淘汰會(huì)造成較大污染的二三類工業(yè)和勞動(dòng)力密集型的工業(yè),改成具有高新技術(shù)、信息內(nèi)涵所支撐的產(chǎn)業(yè)園區(qū);2)改配套。將低級(jí)的、不符合城市未來(lái)發(fā)展的東西淘汰掉,對(duì)園區(qū)進(jìn)行系統(tǒng)的規(guī)劃。
而在“遷”的問題上從城市歷史文化保護(hù)的角度出發(fā),可以將園區(qū)內(nèi)的工廠、硬件設(shè)備等遷走,保留下的特屬于該地區(qū)工業(yè)園區(qū)建筑或標(biāo)志進(jìn)行再開發(fā)利用,如北京798和成都的工業(yè)博物館。為工業(yè)產(chǎn)業(yè)園區(qū)的未來(lái)預(yù)留出一定發(fā)展空間是十分必要的,這甚至能成為城市一個(gè)可持續(xù)利用的發(fā)展標(biāo)志。保持原有的工業(yè)文化脈絡(luò),以藝術(shù)的手法使其得到新生。
5 結(jié)語(yǔ)
工業(yè)園區(qū)作為城市的一部分,其低污染、低能耗、低干擾的目標(biāo)是始終不變的。而工業(yè)園區(qū)作為城市規(guī)劃中的一個(gè)部分,并且出于對(duì)城市規(guī)劃的整體考慮,工業(yè)園區(qū)并不一定需要從始至終都保持其單一的性質(zhì)不變,而應(yīng)該是隨著人們的需求以及城市發(fā)展的需要來(lái)對(duì)其進(jìn)行靈活的調(diào)整。同時(shí),這一點(diǎn)在我們?nèi)粘5某鞘幸?guī)劃與城市設(shè)計(jì)中將有所體現(xiàn)。
[1]Pryor R J.Defining the Rural Urban Fringe[J].Social Forces,1968,47(2):202-215.
[2]龔兆先,溫春陽(yáng),周永章.城鄉(xiāng)邊緣帶時(shí)空離心推移的約束及其方法[J].熱帶地理,2006,26(2):129-133.
[3]譚善勇,王德起.城市經(jīng)濟(jì)學(xué)[M].北京:中國(guó)建筑工業(yè)出版社,2009:28-29.
[4]許學(xué)強(qiáng),周一星,寧越敏.城市地理學(xu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79-80.
[5]奧古斯特·勒施.經(jīng)濟(jì)空間秩序——經(jīng)濟(jì)財(cái)貨與地理間的關(guān)系[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5:167.
[6]顧朝林.中國(guó)大城市邊緣區(qū)研究[M].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