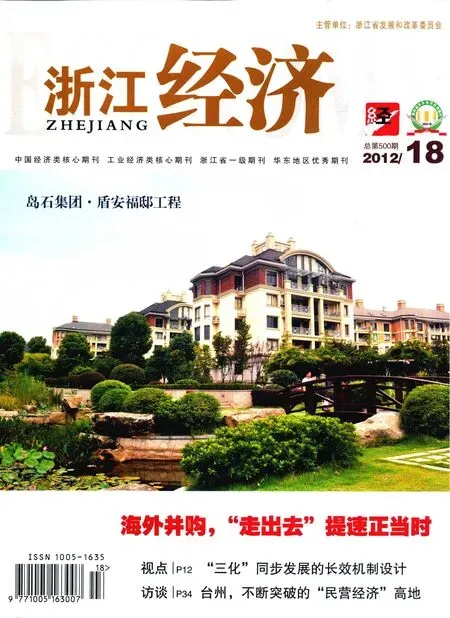破解城鄉收入差距之謎
□文/柳博雋
城鄉收入差距的癥結在于城鄉居民的權益不平等,需要從“賦權予民”這一基礎環節著手加以破解
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經濟領域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但一些結構性的社會問題仍然存在,最典型的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這突出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上——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6977元,城鄉收入差距十分懸殊。
眾所周知,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不僅會影響居民的福利水平,還會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甚至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為此,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采取各種措施努力縮小差距,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要求,著力推進新農村建設,實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深化農村稅費制度改革,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旨在提高農村居民收入水平。
而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最近十年的城鄉收入差距是“縮而不小”——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雖有所收縮,但差距仍然不小,2002年以來城鄉收入之比一直都高于3:1,遠遠高出大多數國家不到1.5:1的水平。種種措施已多管齊下,城鄉收入比緣何依舊居“高”不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收入差距長期累積,當然非一日之功就能消彌。然而,深入分析居民收入中的各種差距,卻發現了一些“端倪”——按照當前的統計口徑,居民收入主要由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四部分構成,其中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主要是勞動所得,財產性收入為資本、土地等可資產化要素的權益收益,轉移性收入主要是來自政府轉移支付的非要素收入。很顯然,列入初次分配范疇的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是以“效率”原則分配的,無論是工農產品價格,還是城鄉勞動力的工資水平,其差距之大導致城鄉收入的差距,早已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從財產性收入看,由于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目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不是很大,但城鄉之間的絕對差距還是比較大。更嚴重的是,城鎮居民的物權已基本權益化、市場化,最典型的就是住房產權的權益化,城鎮居民可憑借所擁有的財產權利的流轉而獲取溢出性收益;而農村居民仍然沒取得土地等要素和財產相關的明確權屬,無法享受充分的產權收益。隨著財產性收入所占比重的提高,在“馬太效應”作用下,城鄉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差距會持續拉大,從而進一步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鴻溝”。
而作為再分配領域的轉移性收入,由于城鄉居民享受的公共服務政策不同,城鄉差距也比較大。有數據顯示,轉移性收入占城鎮居民總收入達到1/4左右,而在農村居民總收入中的比重不到8%,盡管近幾年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推進,城鄉居民的轉移性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差距仍在10倍以上。這也表明,轉移性收入的再分配機制總體上擴大了城鄉收入差距,其再分配的逆向調節作用遠大于正向調節作用。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居民收入結構中的各種收入,城鄉之間都存在不小的差距。產生這些差距的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共同原因,那就是城鄉居民的權益不平等——由于城鄉居民的勞動權益不平等,導致其勞動所得的工資性收入差距巨大;由于城鄉居民的財產權益不平等,導致憑借物權而獲取的財產性收入也存在差距;由于城鄉居民的公共服務權益不平等,導致來自政府的轉移性收入差距懸殊。可以說,正是這些居民權益的城鄉不平等,造成了城鄉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日積月累、積重難返。
破解城鄉收入差距需要對癥下藥。既然城鄉收入差距的癥結在于城鄉居民的權益不平等,那就需要從“賦權予民”這一基礎環節著手,即賦予城鄉居民平等的勞動權益、財產權益、公共服務權益等,并在權益平等的理念下,加快推進城鄉二元體制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城鄉資源市場配置、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分享的一體化制度,從而在根本和實質上撬開“三農”問題的破解之門。
(供稿:浙江省發展規劃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