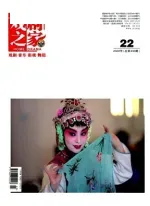中國(guó)古典舞身韻的審美特征
□劉忠欣
提起古典舞,人們腦海便會(huì)浮現(xiàn)出中國(guó)古典詩(shī)詞中大量有關(guān)的精彩描繪。如白居易對(duì)霓裳舞的偏愛(ài)就很值得回味:“千歌萬(wàn)舞不可數(shù),就中最?lèi)?ài)霓裳舞”;“飄然轉(zhuǎn)旋回雪輕,嫣然縱送游龍?bào)@”;“小垂手后柳無(wú)力,斜曳裙時(shí)云欲生”(《霓裳羽衣歌》)。從這些栩栩如生的描繪中,我們不難體會(huì)到舞者在旋轉(zhuǎn)時(shí)如雪的輕盈,跳躍時(shí)好似被驚動(dòng)的游龍的迅疾,垂手緩步時(shí)又似垂柳一樣的綿弱無(wú)力,斜甩舞裙時(shí)又風(fēng)起云涌般激蕩……
一、中國(guó)古典舞身韻的由來(lái)
欲談中國(guó)古典舞的審美特征,首先必須了解“身韻”這一關(guān)鍵的概念。身韻,即身法與韻律的總稱(chēng),涵蓋了外部表現(xiàn)技法與內(nèi)在氣韻兩個(gè)重要方面。身法屬于外部的技法范疇,韻律則屬于藝術(shù)的內(nèi)涵,二者有機(jī)結(jié)合,即藝術(shù)形式與內(nèi)容高度契合,才能真正體現(xiàn)中國(guó)古典舞之風(fēng)貌與審美精髓。身韻將身法與韻律結(jié)合,將結(jié)合點(diǎn)集中在形與神上,身心并用,內(nèi)外統(tǒng)一,在更高的文化層面上體現(xiàn)了中國(guó)古典舞的風(fēng)格特質(zhì)。
中國(guó)古典舞是從戲曲與武術(shù)中脫胎而出的具有相對(duì)獨(dú)立審美特征的舞蹈品種,因此它的身韻也源自于戲曲舞蹈與武術(shù),是站在中國(guó)豐厚傳統(tǒng)文化基礎(chǔ)之上,對(duì)武術(shù)、戲曲舞蹈通過(guò)象形取意而形成的審美特征進(jìn)行再提煉,并根據(jù)自身特定的內(nèi)容形式而形成了一系列獨(dú)具特色的形態(tài)運(yùn)動(dòng)。
二、中國(guó)古典舞身韻的特點(diǎn)
細(xì)究之下,可以發(fā)現(xiàn)身韻的特點(diǎn)主要可以概括為形、神、勁、律這四個(gè)不同而又不可分割的方面。
1、形
“形”是指形體外部的動(dòng)作,即一切直觀、外在的形形色色的體態(tài)和千變?nèi)f化的動(dòng)作及動(dòng)作間的連接。凡是一切看得見(jiàn)的形態(tài)與過(guò)程都可以稱(chēng)之為“形”。“形”是形象藝術(shù)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古典舞之美的傳達(dá)媒介。因此,“形”之把握,在中國(guó)古典舞中便顯得尤為重要。“擰、傾、圓、曲”正是中國(guó)古典舞對(duì)“形”(即體態(tài))的審美追求的基本法則。以腰部動(dòng)律元素為基礎(chǔ),以“劃圓”路線為主體,以傳統(tǒng)中優(yōu)秀的動(dòng)作為依據(jù),唯有此,才能真正掌握中國(guó)古典舞之形態(tài)美。
中國(guó)古典舞形態(tài)上的“擰、傾、圓、曲”,是由古至今一脈相承而不斷發(fā)展演變的,這一點(diǎn)從出土的墓俑和敦煌壁畫(huà)中不難看出:秦漢舞俑的塌腰撅臀,唐代的“三道彎”,戲曲舞蹈中的“子午相”、“陰陽(yáng)面”、“擰麻花”,中國(guó)民間舞膠州狹歌的“輾、擰、轉(zhuǎn)、韌”,海陽(yáng)秧歌的“攔、探、擰、波浪”,“花鼓燈”的“斜塔”,武術(shù)中的“龍形猿步”、“八卦”等無(wú)一不貫穿著人體的擰、傾、圓、曲之美。中國(guó)舞蹈的體勢(shì)總體呈現(xiàn)為一種回旋、圓轉(zhuǎn)的狀態(tài),擰、傾、圓、曲的體態(tài)和“劃圓”的動(dòng)作軌跡體現(xiàn)出周而復(fù)始與輪回的中國(guó)哲學(xué)精神。
2、神
任何藝術(shù)如果沒(méi)有神韻,就變成了沒(méi)有靈魂的軀殼。在古典舞中人體的運(yùn)動(dòng)方面,神韻是可以認(rèn)識(shí)、可以感知的。在中國(guó)古典舞中,我們將“神”泛指為內(nèi)涵、神采、韻律與氣質(zhì)。舞蹈中有句行話:“形三,勁六,心意八,無(wú)形者十。”即是指在舞蹈動(dòng)作姿態(tài)中,“形”只占三分,“勁”占六分,“神”占八分。“神”是舞蹈者心態(tài)與內(nèi)涵的表達(dá),單純模仿是毫無(wú)作用的。而當(dāng)掌握了“形”、“勁”,又領(lǐng)會(huì)到“神”之時(shí),便自然會(huì)將三者融會(huì)貫通,達(dá)到形神兼?zhèn)洹⑼昝澜y(tǒng)一之境界。這正是舞蹈藝術(shù)表演之真正追求。
3、勁
“勁”在中國(guó)古典舞中意為賦予外部動(dòng)作的內(nèi)在節(jié)奏和有層次、有對(duì)比的力度處理。中國(guó)古典舞的運(yùn)行節(jié)奏往往多是舒而不緩、緊而不亂、動(dòng)中有靜、靜中還動(dòng)的節(jié)奏,舞蹈在相對(duì)自由但又有規(guī)律可循的“彈性”節(jié)奏中進(jìn)行。中國(guó)古典舞在身韻方面強(qiáng)調(diào)培養(yǎng)舞蹈者在舞動(dòng)時(shí)對(duì)力度的掌握尺度,要求力度的運(yùn)用應(yīng)做到有輕重、緩急、長(zhǎng)短等的對(duì)比與區(qū)別,不能趨于平均。“勁”不只是貫穿于動(dòng)作的過(guò)程中,在動(dòng)作快結(jié)束時(shí)更為重要。
4、律
“律”,包含動(dòng)作中自身的律動(dòng)性和運(yùn)動(dòng)中依循的規(guī)律兩層含義。一般來(lái)講,動(dòng)作與動(dòng)作間的連接必須要“順”,而這“順”便是“律”中之“正律”。舞蹈中,演員的動(dòng)作若“順”,則有行云流水、一氣呵成之感。但“反律”也是古典舞律動(dòng)中十分重要的因素,這些“不順則順”的“反律”,在舞蹈中可以產(chǎn)生奇峰迭起、出其不意的效果。再?gòu)墓诺湮璧膭?dòng)作來(lái)看,“一切由相反之面做起”也是其重要特征之一,主要表現(xiàn)為“欲左先右、欲前先后、欲上先下、逢開(kāi)必合、逢沖必靠”的運(yùn)動(dòng)規(guī)律。通過(guò)這些我們可以看出,無(wú)論是一氣呵成、順?biāo)浦鄣捻槃?shì),還是相反的逆向運(yùn)勢(shì),或是從“相反之面做起”,都體現(xiàn)出中國(guó)古典舞“圓、游、變、幻”之美,這正是中國(guó)“舞律”之精奧所在。
由此可見(jiàn),中國(guó)古典舞蹈具有脫俗驚艷、讓人沉醉的美感。而這種美感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根植于中華民族悠遠(yuǎn)廣博的文化底蘊(yùn)之中,幾千年歷史滄桑的推演和燦爛文化的滋養(yǎng)陶冶,注入中國(guó)古典舞以中華民族特有的審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