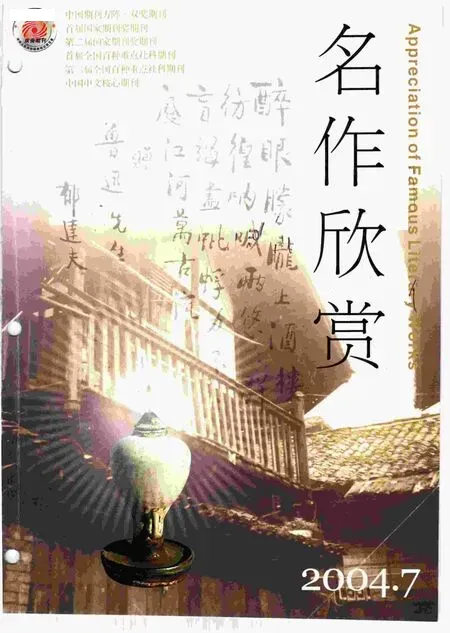讀者來函
2012-08-15 00:42:44朱小如
名作欣賞 2012年7期
第一期拜讀了。“語文講堂”一塊,有意思!“語文”比之“文學”可算是重要的多得多的“經國之千秋大業”,容不得“糊涂”。姜文看著貌似有理,卻是大不妥。忘了語文接受和文學接受的差別,幼兒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區分。葉老的功績在語文教育,而非文學成就,葉老的《文心》是語文教師的必讀書。葉老的由“教到不用教”的“理性工具”教育思想,是我當年教書的指南。當年我之放棄教書一職,是因為現實教學生活中,每天面對著天真無邪的學生卻又不得不說“謊話”的痛苦和恐懼。如果,換成另一種現實,我愿意一生從教,而非當什么記者、編輯、評論家。如今的老師、博導們也許就因為對自己說“謊話”從未產生過我那樣的“痛苦和恐懼”,所以他們覺得有資格做老師、博導。我是沒有這份自信,所以連個高一點的“職稱”都評不上。回到“語文”的話題,教學改革提了幾十年,就是越“改”越“繁瑣”,越抓不住重點。其實,在我看來,教學改革的重點,也就一個字就包含了,那就是改“教”為“學”,長期以來,“教”意味的是“教化”,這和我們的民族文化智慧有密切關聯。中國人管理國家、人民、孩子是一回事,除了我們習慣的“管、卡、壓”并沒有太多的智慧。如何改被動的“教”為主動的“學”,這才是人類學會運用“理性工具”,懂得如何選擇正確的、民主的、自由的語文教育的唯一方向。讀讀同期中李潔非所說的話:“說到底,讀書無非是求知,無非是去弄懂各種道理。讀書的意愿,來自希望了解和接受古往今來以為善的、正確的觀念、尊重這些觀念、按照這些觀念行事做人。”我以為這也就“語文教育”的最高目的。去年我曾寫過一篇有關語文的文章,意思是如今的“語文教育”教會了我們如何說空話、套話和假話,就是沒教會我們說自己的話,更別提說實話、說真話了。
猜你喜歡
華人時刊(2022年13期)2022-10-27 08:55:52
當代陜西(2022年4期)2022-04-19 12:08:52
快樂語文(2021年35期)2022-01-18 06:05:52
福建基礎教育研究(2019年9期)2019-05-28 01:34:27
北京教育·普教版(2018年1期)2018-01-29 20:45:18
小天使·一年級語數英綜合(2014年6期)2014-07-22 23:32:38
智慧與創想(2013年7期)2013-11-18 08:06:04
網球俱樂部(2009年9期)2009-07-16 09:3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