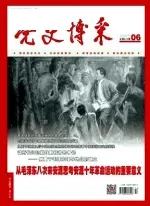毛澤東平津決戰謀篇布局之特色
任淑艷
(天津市委黨校 中國天津 300191)
毛澤東平津決戰謀篇布局之特色
任淑艷
(天津市委黨校 中國天津 300191)
平津戰役系解放戰爭時期三大戰役的最后一次敵我大交鋒,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通向勝利之路,無一例外地取決于謀劃與運作,或言決策與用兵,即事與謀。決戰性的戰役尤當如此。平津決戰謀篇布局之特色,決策用兵之精到,無處不在的《孫子兵法》,又遠非不朽的軍事經典《孫子兵法》之連珠妙語盡能概括的。
平津決戰;決策;用兵;孫子兵法
平津戰役系三大戰役的最后一次敵我大交鋒,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它的勝利是人民的勝利,人民的勝利乃不變之定理。然而通向勝利之路,并非天然之坦途,或漫長,或短暫,或崎嶇,或平直,皆無一例外地取決于謀劃與運作,或言決策與用兵,即事與謀。決戰性的戰役尤其如此。用以解決國民黨軍事力量的所謂北平、天津、綏遠方式的創造,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對平津戰役決策與指揮的出神入化,堪稱中外戰史經典之作。平津決戰謀篇布局之特色,決策用兵之精到,無處不在的《孫子兵法》,又遠非《孫子兵法》之連珠妙語盡能概括的。
一、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是毛澤東決戰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平津戰役中得到成功的運用。
戰爭被稱作流血的政治,論及戰爭,總要聯想到血腥與傷亡,這幾乎成了戰爭的同義語,并作為戰爭的常規被認同。戰役是消滅敵人有生力量,迫使敵人屈服最終實現戰略目標的手段。既然是手段,就需加以權衡。在屈人之兵上,戰與不戰有殊途同歸,異曲同工之效。選擇戰與不戰要因人因事因時而定,在多種制約因素中,不可或缺的是英明的戰略指導和超凡的軍事指揮。鑒于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只是善用兵,而且是戰爭的最高境界。
“屈人之兵而非戰者”,可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實力懸殊,敵強我弱,戰則于己不利,通過政策策略瓦解敵人,可贏得武力打擊意想不到的效果。北平的和平解放則為第二種情形,我軍實力已今非昔比,士氣高昂,所向披靡。之所以采用和平方式解決敵軍,實乃鐵肩擔道義,不僅能使極具政治、經濟、文化價值的名城北平,免遭戰火洗劫,而且可以保護城市工商業,減少人員傷亡,有助于擴大我軍建制,并能夠加快勝利的進程,還可以保證中共中央及政府首腦機構順利遷入北平,這是出發點之一;之二是對傅作義的一貫作為和兩難處境有深入了解,傅系地方實力派,非蔣嫡系,與蔣積怨日深,在抗戰中深明大義,態度積極。在北平問題上,因顧慮重重,苦苦徘徊于顧全民族大義與徹底淪為民族罪人之間,心情極為復雜矛盾,適度的外力無疑可助其抉擇。由此可見,人民解放軍不是無力攻取北平,而是不宜武力輕取。既然不戰可屈人之兵,何樂而不為。況且選擇何種方式解決傅部還關系到平津的穩定。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用軍事手段鋪就通往和平道路的方針,攻心與攻城相結合,對傅進行政治爭取,通過其親朋故交進行游說滲透,曉以利害,使其拋棄幻想,打消顧慮。同時輔以強大的軍事實力做后盾,即使一旦和平解決的道路受阻,也不會貽誤和喪失戰機。傅面對華野和東野百萬解放軍的破竹之勢,無法消受,已如驚弓之鳥,加之解放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武力解決了天津守敵,這一并成為傅作義決意投誠,接受和平改編的軍事前提。所以,北平之敵的和平解決可以說是以柔克剛,以剛舉柔,剛柔并濟,迫敵就范。北平的和平解放,對新中國的重建,功不可沒。
二、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戰爭有慣常之規律和基本之要素。若言謀略,充其量不過三十六計,但卻可以有幻化無窮的戰術組合。出奇不意,既在情理之中,又在常規之外,即可謂之奇勝。平津戰役從高層決策到實際操作,無不充滿智慧。最高決策者毛澤東在決策和指揮過程中既非力排眾議,也非簡單地博采眾長,其用兵與決策可用兩個字概括,即“定”和“變”。戰役以決戰形式出現,徹底解決平津守敵的戰略已定。戰術上求變,沖破思維定勢,既著眼于目前戰局,又不僵滯于眼前;高瞻遠矚,既無處不到,又非面面俱到;不僅對戰勢了如指掌,更能充分利用戰術的靈活營造有利的戰略態勢;辯證靈活地處理目的和手段的關系,因勢利導,促其互動和轉化。定與變相得益彰。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從圍而不打,隔而不圍,到打掉兩頭,孤立中間,奇正結合,環環相接,絲絲入扣,促成了最終吃掉天津敵人,和平接管北平的結局。打破常規,靈活多變,屢出奇兵以奇制勝是毛澤東軍事思想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是屢試不爽的制勝之寶。傅作義曾盤算,在東北戰局結束后,東北野戰軍入關至少需要三個月,他可借機將華北國民黨軍從60萬急擴至100萬,一來可加強軍事實力,二來可為自已增加政治籌碼。幻想以一字長蛇陣來確保萬無一失。然而毛澤東卻出其不意地在東北戰事結束之前,就命令東野秘密入關,并用包圍張家口吸引傅部的注意等手段迷惑敵人,以掩護東野入關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同時達到了一舉消滅敵35軍等主力的目的。手段與目的巧妙結合,戰術運用爐火純青。當平津戰幕拉開時,東野已入關并部署完畢,實現了對傅集團的戰略包圍和分割,腰斬敵“一”字長蛇為五截。一招奇兵使傅痛失或談或打的籌碼和本錢,開始試探性地謀求和談。對于其頗欠明朗的態度,中共中央并未以固定的模式非打即拉,而是采用又打又拉、恩威并施的策略,把傅列入戰犯名單,從而一舉多得,既讓傅認識到自己負有不可逃脫的戰爭罪責,又通過此舉加強了傅的合法地位,有可能借此大做文章,更重要的是使蔣系親信從幕后迫不及待地跳到臺前,充分表演,使傅對蔣利用他的真實面目一覽無余,下定倒戈之決心,談判得以越過最為艱難的臺階,最終踏上和平之旅。
三、上下同欲者勝。夫上下同欲,即萬眾一心,為贏得人民的解放,打敗反動派這一共同目標,軍民團結作戰支前,將帥協同決策用兵,這是平津戰役取得勝利的關鍵。
平津決戰的勝利,首先離不開華北及東北地區廣大人民群眾人力物力的大力支援,民眾以極高的熱情擁護和支持解放軍,傾其所有,盡其所能。為配合東野入關作戰,15萬民工利用民間的大車、小車、手推車或人背馬馱,隨大軍遠征,以保障百萬大軍的糧草供給,鋪路架橋,運送傷員,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民戰爭。戰役期間,周恩來、李富春、薄一波等親自主抓支前工作。冀中、冀東、北岳區等均成立了支前委員會或指揮部。后勤保障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決戰戰役規模大,持續時間長,參戰人員眾多,就地取給不能滿足需求,所以物資運輸成為重中之重,民工支前是后勤保障的重要組成。不僅如此,大量物資的募集也離不開人民群眾的積極支持。“據不完全統計,平津戰役共動員民工2154萬人,共修路7000余公里,架橋372座,出動擔架2萬余副,小車2萬輛,大車38萬輛,牲畜100萬頭,運糧3.1億斤”。[1]總之,依靠軍民兩條線保障了巨大的后勤供應,單靠任何一方都難以完成,正可謂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以其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嚴明的紀律,勇敢的戰斗作風,贏得了人民的擁戴,在一定意義上說,天津戰役是軍事勝利更是政策的勝利。
加強政策宣傳使之深入人心,是我黨的工作作風也是平津戰役之特點,使全軍上下,皆了解黨中央的戰略意圖,主動配合瓦解敵人的攻心戰。北平群眾在我黨的領導下,舉行示威游行,反對堅持武力頑抗的倒行逆施,產生了巨大影響。
決策層將帥協同一心,是戰役勝利的有力保證,有史以來,正反兩方面的教訓為數不少。蔣邦集團高層勾心斗角,內訌頻發,朝令夕改,莫衷一是,最終成為導致兵敗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反證,高級決策層的團結協同,的確至關重要。與之迥然不同的是中共中央領導層緊密團結,步調一致。這種團結絕不是抹煞是非的一團和氣,而是目標一致、人民至上、志同道合。以集體的智慧,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在用兵與決策上皆有不同的貢獻,中共黨和人民群眾上下齊心,同仇敵愾,銳不可當。
四、夫兵形象水。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用兵無常勢,水無常形概括中國人民解放軍打與走相結合的運動戰,可謂恰如其分。為掩護東野秘密入關,華野楊成武等部,造成包圍張家口之勢,傅不知是計,調35軍回撤馳援,并暗中竊喜,自以為正中下懷,郭景云更是自鳴得意,忘形至甚,殊不知35軍已鉆進了華野19兵團的包圍圈,令其做夢也想不到的是,東野如神兵天降,出現在面前,配合華野作戰。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被蔣介石視為狡猾過人的宿將傅某栽了跟頭。解放軍的戰略運動,貴在無定勢和常形,高深莫測,質在有備而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
中央軍委原決定東野主力入關后,首先殲滅塘沽之敵,以斷敵東逃之路。在兵力配置上,對敵人有可能借我軍力克塘沽之時兵力向東集中的可能性做了充分的估計,也做了周密的準備。而在實地勘察時,發現塘沽地貌不利構筑工事,難以嚴防敵軍東逃,而且根據形勢判斷,傅部很有可能會借我軍攻打塘沽之機突圍,于是中央軍委斷然將矛頭指向天津,一面向天津守軍發出和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一面完成了軍事攻堅部署。天津市區地形南北向狹長,且守敵系南弱而北強。守軍司令陳長捷錯誤地判斷擅長攻堅的解放軍,會打北部攻堅或以南部為突破點,然而,東野的最高指揮電請中央,決定以中部為主攻點,主攻縱隊如鋒利尖刀,東西對進,攔腰斬斷,其余縱隊乘勢鋪開,先南后北,如水淹七軍,如風卷殘云,先吃肉、后啃骨頭,僅用29小時即解決了天津守敵。出神入化的兵力調配已令敵軍眼花繚亂,加之此次戰役中投入的大量新式兵種,坦克兵、炮兵、工兵、步兵多兵種全方位交叉協作,如百變金剛,使敵人既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天津戰役既不排除爭取守敵和平放下武器的可能,又不放棄武力解決,根據敵軍布防和意圖及時調整戰術部署,因敵而制勝。解放軍所到之處,猶如洪流蕩滌著污泥濁水。
五、勝兵先勝而后求戰。孫子日:道、天、地、將、法“凡此五者,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主熟有道?將熟有能?天地熟得?法令熟行?兵眾熟強?士卒熟練?賞罰熟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國民黨反動派背離民意,大失民心,草菅人命,頻起內訌,蔣、傅矛盾,高層弄權,法令不通。與之截然相反,人民解放軍是正義之師,順乎民心,合乎民意,紀律嚴明,官兵一致,上通下達,將帥協謀,決策英明。解放戰爭最初兩年的對壘及遼沈、準海兩大戰役,已基本改變了敵我力量對比,而且東野提早入關,與華野總兵力達百萬,占絕對優勢。本著執行有利決戰,避免不利決戰的原則,在戰役開始前,中共中央及中央軍委在組織戰略上積極而慎重,做了充分而周密的部署,在戰略決策上已成竹在胸,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絕非一賭勝負。對敵兵力數量、配置、軍事指揮的特點,集團內部矛盾乃至細膩的心理揣摩,無不了如指掌,正所謂知已知彼,百戰不殆,其攻勢必定是直奔要害的致命一擊。所以平津戰役不是毫無準備的順水推舟之作,而是經過充分運籌的杰作。不戰已知勝負了。正如毛澤東在總結北平、天津、綏遠三種方式時,精彩而準確地提出“解決”國民黨軍事力量,“解決”二字道出了決戰的真諦,展示出胸中自有百萬兵,九天五洋縛蒼龍并且穩操勝券的雄渾氣魄。
平津戰役的勝利,基本肅清了華北國民黨軍的軍事力量,奠定了全國勝利的基礎。該戰役主要經驗特點是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相結合,武力解決與不流血的斗爭方式相結合,暫時讓步與集中力量消滅首要相結合,其謀篇布局之精進,遣將用兵之老道,分寸之間,拿捏自如,彪炳中外戰爭史冊。
[1]李新、陳鐵健主編《最后的決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577頁。
任淑艷,工作單位:天津市委黨校黨史部,職務職稱: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共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