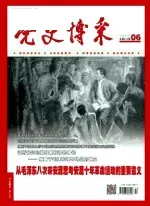對現時代輿論的有效引導與合理調控
褚亞玲 李強強
(石家莊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00)
對現時代輿論的有效引導與合理調控
褚亞玲 李強強
(石家莊學院 河北石家莊 050000)
輿論是公眾關于現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但這并不能說明輿論總是科學的和合理的,輿論不可避免地帶有較強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此外,公眾總體認識水平的局限、外在客觀條件的制約等也在影響著輿論的科學性,有時還會出現極端的情緒性輿論。正如黑格爾所言,“公共輿論中真理和無窮錯誤直接混雜在一起”。面對混雜著理性和非理性的成分的輿論,不能對之簡單地予以全面肯定或全盤否定,要能夠發現和扶持輿論中積極健康、科學合理的成分,抑制和剔除負面的甚至反動的成分,才能使輿論真正發揮促進社會發展的進步作用。
一、對輿論進行合理的調控、引導
我國政府和媒體一直都強調必須對輿論進行正確引導,并將新聞工作列為宣傳輿論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全局高度對事物的運行和發展予以總體上的指導和調節。因此,我們的輿論引導,是指執政黨和政府為確保輿論健康有序發展,使其對思想、對社會、對政權產生有益的穩定和促進作用,運用直接和間接手段相結合的方法,從系統、綜合和全局的角度,對一定范圍內的輿論的總體運行進行引導和調節的過程。
中宣部干部局編寫的《新時期宣傳思想工作》一書指出“新聞輿論工作的宏觀管理,就是從黨、國家的工作大局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遵循黨的方針政策,依據國家的法律法規,對新聞宣傳工作實行組織、指導、協調和監管,積極支持和發展正確健康的輿論,堅決抵制和克服消極有害的輿論,保證正確輿論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地位。”我們的輿論引導,是在充分尊重新聞規律和輿論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進行的一種彈性控制、柔性控制,不是強迫實現輿論的一律。
毛澤東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提出了“輿論既一律又不一律”的命題。雖然現在歷史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該命題對今天的輿論調控仍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在事關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則的問題上,一定要旗幟鮮明、毫不含糊,此外則提倡輿論的多樣化,以營造一個主旋律一致下的多元表達世界,讓全面反映客觀事物的真實情況、反映客觀規律、維護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社會輿論在多元化的輿論生態中形成強勢,形成主流。
我國輿論引導的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要做到輿論的平穩、有序,避免輿論的大起大落、起伏不定和輿論中心忽東忽西、飄搖不定。要在保持輿論常態中確定輿論主旋律,最終實現“變中之靜”“動中之穩”,推動社會良性、有序、理性發展。
二、政府對輿論的調控
政府對輿論有強大的調控功能,例如政府對輿論傳播媒介的控制、對傳播人員的控制和對傳播內容的調控。對傳播內容的調控主要指國家和政黨或政治集團利用法律、行政、物資以及新聞宣傳紀律、新聞宣傳的效果預測等手段,對新聞的信息傳播的流向與流量進行強制性和希望性相結合的管理與約束。
(一)政府調控輿論原則
社會生活中的輿論調控應遵循一些主觀原則和客觀規律,這些原則和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所以,有必要研究輿論調控的原則性。
1.國家利益原則。任何國家的任何政治經濟文化行為,都把維護國家利益作為最高的利益。作為國家管理的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新聞媒體更是不能例外,更要處處時時事事以國家利益為重。
2.黨性原則。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輿論是有黨性的。它為哪個階級服務,就要具有哪個階級的黨性。毛澤東曾強調“務使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克服宣傳人員中鬧獨立性的傾向。”毛澤東還強調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西方國家執政黨在輿論調控的過程中,同樣遵循這一原則。
3.符合輿論規律。輿論調控也好,輿論引導也好,必須遵循輿論規律,從事實出發做出判斷。輿論是一種社會意識,它一經產生就具有不依賴于意識主體的相對獨立性,有著內在的發展規律,這種客觀的規律,誰掌握就將為誰服務。馬克思對輿論的內在規律有個著名論斷:它“具有連植物也具有的那種為我們所承認的東西,即承認它具有自己的內在規律,這種規律它不能而且也不應該由于專橫暴戾而喪失掉”。
(二)政府調控輿論手段
考察目前國內外對輿論進行調控的形式,有以下幾種:
加強施工過程控制以及技術人員、管理人員的質量意識,每次開工前開展質量意識重申,開展獎懲機制,一旦發生違規操作,立即嚴厲制止并進行處罰。
1.輿論立國
即利用各種媒介形式對內宣傳本國利益的正當性和立場的正義性,統一思想和意志,動員并爭取物力、財力、人力和科技等方面的支持;對外力爭法理和道義上的主動,以期國際社會的支持。
2.輿論引導
“輿論調控方”主導新聞輿論、影響民意歸屬,用典型引導等方式宣揚己方的立場和政策,把國家意志轉化為群眾意志。一方面對對方輿論的擴散實行嚴格控制,以確保不受對方輿論影響;另一方面對己方的輿論進行檢查監督,確保輿論符合國家意志和戰略目標。
3.反輿論封鎖
控制信息權較弱的一方利用新媒體打破信息壟斷,在國際社會發出自己的聲音,爭取輿論空間。
(三)政府利用法律法規進行調控
國家、政府、政黨、社會集團、行業組織出于各自的利益、目地和需要,利用法律政策、規章等手段,進行新聞檢查、新聞審讀,對其流向、流量進行強制性的約束和管理。正如對社會生活的管理離不開法律法規的強制執行,對輿論的調控也離不開相應的法律法規。例如,對網絡輿論場的調控,網絡輿論場有自由、民主,可以讓網民在論壇、空間中自由發帖,表達自己的觀點與看法。與此相對應的,網絡也要有相應的法治,用以維護網絡文明。
除此之外,還有政黨調控,包括政策、紀律、指示和審讀等,政府還可以進行行政調控。
(四)政府采用更加高明的軟性控制手段
輿論調控不能簡單粗暴,理應采用更加“智慧”的手段。
陳力丹先生指出“政治、經濟的權力組織針對因特網實行的控制方式,正從硬性轉向軟性的對話、對策關系,如同我們說話有語法的無形控制,但大多沒有感覺到。”這正是政府對輿論進行調控的一種“潤物細無聲”的高明手法。
比爾·蓋茨在《未來之路》一書中對西方國家社會對輿論進行調控的手段進行了披露:“通過各種被稱為‘信息推拿’的宣傳手法、通過軟件對信息的不同剪裁和歸納、通過管理者階層間接控制局域網等等,使得因特網的新聞和言論不會經常溢出被允許的限度。由于強大的信息源網站比普通個人用戶具有的優勢,用戶的選擇權實際上只是一種操作權。供應商(ISP)有權切斷用戶線路,關閉他們的帳戶,軟件平臺公司可以完全控制住信息的顯示方式……。”
看來美國對網絡輿論的調控是“毫不手軟”兼具“不動聲色”,正如托夫勒寫道:“任何國家都在力保權力。無論給我們造成的損失有多大,國家都將想方設法阻止最新的通信革命達到目的,并將對信息的自由流動加以限制。”
三、社會對輿論的調控
對于新聞傳播及通過媒體進行的社會輿論的控制,從社會功能和實施渠道來說,是一種社會調控,來自政府以外的社會力量對輿論的調控。互聯網等新媒體推動了“數字化文藝復興”,也產生了“數字鴻溝”,新媒體所形成的輿論場是一個反映現實生活的虛擬空間,現實社會中有各種法律法規、道德規范、自律公約等發揮作用以維持社會的穩定,輿論空間同樣需要各種規則來進行約束與調控。正如哈貝馬斯所言:“科學技術的合理性本身也就是控制的合理性,即統治的合理性。”
1.社會集團等通過媒介影響輿論,表達、實現其利益
社會控制的一個目標就是界定正當行為的時間、地點和方式,通過對形象、秩序和失序的申明、強制和道德譴責等方式顯示出來。最典型的是集團調控,各種權勢集團和壓力集團對輿論進行調控;
2.行業管理遵循行業規范
即行業調控,通過行業組織的自律來實現。如互聯網管理組織等,互聯網行業形成本行業的行業規范,借之來進行自我調控。如民間的掃黃打非協議等,集團、組織憑借社會力量和政府進行博弈,使政府做出對之有益的決議。如通過對“把關人”的重點監控,提高其新聞倫理水準,制定新聞倫理規范,督促其自覺執行貫徹新聞職業道德準則;促進互聯網加強行業自律,遵守行業規范,增加社會責任感,都是社會對輿論進行調控的手段。
此外還有資源調控,如對新聞生產資料、新聞信息、廣告、資金的配置及商標與主辦者信譽等無形資產的管理;稅收調控,通過保證金、營業稅、印花稅等進行調控;市場調控,指對國內外書報刊及電子傳媒市場的準入與否以及各種優惠政策的調控等等。同時,以媒介素養教育提升大眾傳媒素養,亦是社會調控的手段之一。
本課題為2011年度石家莊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研究課題“新媒體及其輿論引導力研究”(編號WH1105)。
褚亞玲 (1972年—),女,石家莊學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新媒體。李強強,石家莊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